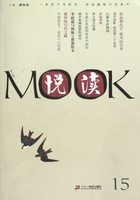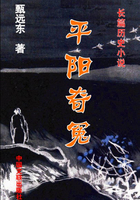窗无月,人无泪,无泪何故反相思?
人无聊,酒无情,无情何须折愁肠?
一人斜倚着窗儿,挽着酒坛子,对着黑夜痛饮。他的头发蓬乱,双目半闭,目光却如刀芒;胡子浓密,像针一样插在脸上,差点儿连嘴巴都找不到了;脖子颀长而坚韧,还有一条巨大的伤疤斜躺在那里,就像一条蜈蚣似的。
他仰着头,将半坛酒倒了进去,酒从嘴角流出,淌过那条伤疤,湿透了胸膛。
“一个人喝酒,寂寞不寂寞了一点?”
一个粉衣少女走了进来。她身材高窕,脸颊尖长而稚气未脱,眼睛如竹叶一般细长。她是大名鼎鼎的剑客宋礼之千金宋尚燕。
他冷笑道:“堂堂一个石头山庄的千金,三更半夜跑到一个醉汉的家里,到底想做什么?”
宋尚燕道:“当然是做女人想做的事,而且很耗费体力和时间呢。”
“女人晚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知你指的是哪一种。”
“喝酒,当然是喝酒。”
“哦?”他冷笑道,“酒我已喝完了,却不知姑娘的话说完了没有?天黑了,我想我该睡觉了。”
“死归野,坏归野。”宋尚燕跺着脚道,“为什么每次都赶我走?难道喜欢一个人有罪么?”
“喜欢一个人没有罪的。”归野道,“但喜欢我那就比犯了罪还可怕哩。”
宋尚燕气得满脸通红,狠狠地道:
“好。那我每天晚上都来吵你,让你睡不了一个好觉!”
“那没办法了,我只好再到山上小住一年半载的,好好享受一下安宁的生活。”
宋尚燕又跺着脚道:
“让那些野蚊子狠狠教训你一顿吧。”
说着转身就走,又回过头来,抛下一句话:
“我爹叫你去一趟山庄,听说要和我哥打一下架。”
归野吹灭了灯,躺在床上,朝着门外道:
“记住把门关上!”
次日。风清。鸟鸣。
石头山庄内,一片草坪上,两人对望而立,一个叫宋尚义,一个叫归野。站在不远处的有宋礼、石头村六将和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他们将见证石头村三小将的最后一名幸运者的诞生。因此,他们交头接耳兴致勃勃地发表他们独特的见解。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比武者不用武器,单比武功之高下,点到即止。
宋尚义盯着归野,身形闪动,围着归野高速运转,可以同时看到十几个影子,而且每个影子的动作都是形状各异,就像十几个野鬼在飘荡。奇怪的是,虽然宋尚义闪动的速度极快,却听不到任何风声,可见他的轻功之高深。而归野还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微闭着眼,嘴角浮现出一丝嘲笑的意味,神情并没有多大变化。微风吹动着他的头发,发端在双眼间来回摆动,仿佛要扫掉上面的悲哀或尘埃似的。
宋尚义一直寻求着机会出手,但他发现眼前的对手是多么的可怕:对手处于自己的阴影围攻之下,居然泰然自若,而自己却找不到他的任何破绽。在如此之情况之下,自己的弱点很容易,因为自己处于运动之中而对手处于静止之中,运动使体力不断消耗,如此下去,自己将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危险。
于是,宋尚义使出了“龙烈掌”,风声萧萧,如龙长嘶,气势人,如剑如虹,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直扑归野!
归野忽然抬起一只手,眼睛还是微闭着,冷冷地道:
“不玩了。”
“不玩了?”宋尚义急急收住掌势,呆呆地瞪着归野。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下,归野迈着坚定的步子,朝着山庄的大门走去,直到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归野走出山庄的大门的时候,他的脸色已变成了铁青色,一滴滴豆大的汗水从额头滚了下来。他捂着肚子,心里装满了难言的苦水。
一间建在竹林深处的茅厕出现在归野的眼帘,他长舒了一口气:
“得救了。”
恶人寨、五虎寨和野猫寨三寨联军,将石头村围的像一朵向日葵似的,漫山遍野都是帐篷,就像一座座坟墓似的。
在这漫山遍野的白色帐篷之中,有一个青色的帐篷,比其他都要大好几倍,而且这个帐篷门前立着三面不同图案的旗帜,守卫也极其森严。在帐篷之内,三条大汉相对而坐,他们分别是恶人寨主吴夏仁、五虎寨寨主欧霸天和野猫寨寨主朱威。吴夏仁满脸横肉,浓密的络腮胡子,鼻子扁塌,像被牛踩扁似的,嘴巴呈拱形,仿佛对任何事都不满或者瞧不起似的。欧霸天则长得鼠头鼠脑,嘴尖哨牙,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手不停地捋着髭须,仿佛在计算一道算术题似的。朱威面目则显得狰狞,一道大刀疤从额头上一直爬到腮边,脸形严重扭曲,就像一个熟石榴似的。他总是皱起鼻子,重重地喷着气,仿佛很生气的样子。
铺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石头村的地形图,上面满是标记,连茅厕也标出来了,编者的周密之心可见一斑。另一张是邀月台的平面结构图,上面标记了哨台及士兵之数量,连如何破解邀月台的机关都有说明。
吴夏仁指点着地图,对着另外两人解说着,另外两人频频点头。
吴夏仁咳嗽了一声,唤来了一个士兵道:
“叫他进来。”
一个人低着头,跟着卫兵进了来。
这人瑟瑟缩缩,身穿华服,满脸的麻子,就像一块蛋糕上撒满了葡萄干。
吴夏仁道:“在‘青楼梦’玩得还开心么?”
麻子王道:“开心,开心。”
欧霸天开启哨牙大门道:“当当当然啦,那那那里的姑姑姑娘可可可是全城最最最好的。”
一个人长了丑陋的哨牙,老天还让他口吃,真是祸不单行啊。
吴夏仁道:“那人准备得如何?”
麻子王道:“一切按计划进行,到时候他会在山庄里放一把火的,这便是信号。到时候,大王就可以”
今天天气异常闷热,太阳烤炙着大地,就像身处于蒸炉的面包。热气在腾升,火气在膨胀。
陶小志很早便起床了,是被热醒的,否则不到中午的时候,他是不会停止打鼻鼾的,到那时他是被饿醒的。
今天不是打猎的好天气,陶小志想,却是游泳的最佳时日,不知道阿木他们死到哪里去了。
陶小志呆呆地望着小黑,小黑吐了吐舌头,又“嘘嘘”地嗅着地上莫名的气味。
小黑呀小黑,陶小志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的另一半呢。
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远处的树林打得“莎莎”直响,感觉真的像下起了雨。风来无影,去无踪,转眼之间就听不到任何风声了,一切又归于宁静和燥热。
阳光忽然间暗淡了起来。陶小志以为是云朵在岛乱,但天空里根本无甚云朵,太阳却缺了一块!
太阳上的阴影在扩大,光线越来越暗淡,陶小志的惊呀程度越来越大。
太阳难道没有柴薪了么?没有太阳的日子世界将会怎样?植物是不是会全部枯萎?气候是不是永远冬天?我们是不是不用说早上好了?我们是不是只有挨肚子和睡大觉就别无他事可干了?人类会不会随之灭亡?
陶小志的脑海里的疑问一个一个地跳出来,排着对等待着大脑的回应。
一瞬间,天地没有了阳光,太阳变成了一个黑球,天空甚至出现了几颗闪亮的星星!
陶小志凝望着,连呼吸都屏住了。小黑“汪汪”叫声也停止了,仿佛在等待一场噩梦的降临。天地间一片阴沉,万籁俱寂,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迷惑中逃出来。
这是日食,是一种奇异的天文现象。当月球运转到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连成一线,月球挡住了太阳的直射,处于月球阴影中的地球上的人们,便会看到日全食,其他附近的地方可看到的是日偏食。
陶小志正好处在地球上的这块阴影区域里。但他并不知道这叫“日食”,他只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传说,名曰“天狗叼月”,却不知道“天狗”为什么“叼月”,谁敢将这么一个大火球吞下肚子?既然这样,天狗如果哪天不开心,说不定也会把地球一口吞噬呢。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四五分钟,才发生变化。黑色的太阳忽然间亮了一块,也在不断扩大,太阳一块一块地补上了。天地间的光线便又明亮了起来。这种状况正是之前的逆过程。
很快,太阳的整个脸都露了出来,还是刚才的样子,热火四射,并没有任何损伤。
陶小志长长吁了一口气,将满心的不安都吐了出来,但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还是无法平静。
过了许久,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敲着脑袋,跑进了屋子。
出来后,他手里多了一根骨头,骨头里的骨髓吸掉了,就像一根管子似的。他写了一张纸条,卷了起来,塞进骨头里,抛了出去。小黑“汪汪”地跳了起来,接住了骨头,叼着。
“快去,去找小花!”
恶人寨、五虎寨和野猫寨联军到达的第二天,便派人前来搦战。来军大概五六百人,领头的是恶人寨二寨主赵图刚、五虎寨二寨主张英和野猫寨二寨主杨岳。他们叫士兵在石头村的村墙门前骂战。宋礼的两个弟弟宋强、宋忠带几百人出来迎战。
石头村的碉堡之上,有一个小亭,亭中摆着一张圆桌,桌子上铺着一碟花生、一碟香菇炒鸡肉、一碟牛肉和两瓶叶竹青。一个青衣中年男人坐在桌旁,举杯慢慢细呷。这个人的姿态优美,动作文雅,神情安闲,他是石头山庄的庄主宋礼。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面对何种情况,他的举止永远都是那么高雅,神情永远是那么安逸谦和,因为他是宋礼,天底下最潇洒的名剑客!这些年来,他想的东西越来越多,头发却越来越少,而头上的光环却越来越耀眼,简直比如来佛祖的光环还强烈,使人看了眼睛刺痛,所以别人在他面前总是低着头,怕强光伤害了眼睛。即便如此,他待人总是谦和礼貌,就像他欠了别人一债似的。他脸上永远戴着一张扯不掉的宽和仁慈的面具。
他一边喝着酒品尝着佳肴,一边用眼角瞟着城墙下的情况,仿佛在欣赏一场无聊的戏似的。这戏虽然无聊得让人作呕,但他又想知道到底有多作呕,否则他是无法安心的,就像明知道抠伤痂会发炎,还是忍不住要抠。
村墙之下,两军对垒,双方的首领说着脏话。
张英是个性急之人,哪有空和他们吵架,所以他第一个挺枪冲进对方的阵地。宋忠也不甘示弱,怒喝一声,挥舞着偃月刀,拍马迎了过去。
两人交手未及十招,张英的人头便落地。赵图刚和杨岳带领着部队冲杀过来。宋强也长剑一挥,石头村的几百士兵也厮杀过来。
混战之间,一支箭“嗖”的一声,从宋忠的背横穿胸口,他从马上翻落下来。宋强看见弟弟受伤,想前来营救,但摆脱不了赵图刚和杨岳的纠缠,只好调转马头,指挥军队撤退。
石头村村门大开,赵图刚和杨岳赶至村墙之下,城墙上箭矢如雨般射下来。两人只好却步不前,叫士兵破口大骂,还用马拖着宋忠的尸体在墙下转来转去,好好地炫耀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