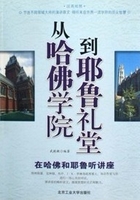直到逃出去了,曼曼还是觉得心跳失常,额头上一层冷汗。真见鬼了,她怕陈云正一个小屁孩儿做什么?
可是,他竟然把当初的戏谈当了真,也实在是够惊悚的了。
也或许,他当初根本就没当戏谈,而是暗里给自己挖的一个大陷阱。可笑自己枉比他年长许多,又自认经历过世故人情,却不想还是幼稚短练的很,竟然稀里糊涂的上了他的当。
一日为师,终身为夫……
呃!曼曼捂住胸口,说不出来的郁闷和窒息。
在当代世界,老夫少妻是经常的现象,但老妻少夫也还不算悖世离俗,从古到今都有,相差十几岁的更常见,但曼曼没法接受自己会嫁一个比自己小上五岁以上的丈夫。
还是一个自己亲手服侍,亲眼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丈夫。
还不是她一个人的丈夫。
况且,根本不是丈夫。
那只是主子而已。
只希望,他只是一时的新鲜,不会执着。
一定是自己多虑了,他只不过是孩子的独占性在作祟。一定是。
曼曼正在自欺欺人呢,就见陈云正满面怒气的瞪着自己:“你这个出尔反尔的骗子,你平时都是怎么说的,什么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什么说话算数,什么守信重诺,原来你都是骗我的?你这个骗子,骗子。”
“不是的。”曼曼看到陈云正脸上真实的痛楚和被骗的愤怒,忙解释道:“奴婢没有说话不算数。”
“哼。”陈云正道:“谅你也不敢。”
他虽是这么说,心底却是不信的,曼曼真个与众不同,明明她是被冤枉的,她却不辩解,宁愿忍着这一身脏水,只能说她根本不在意这府里的人对她是如何看法,更不在意自己对她的看法。
不过,他不会跟她逞一时意气。
曼曼心乱如麻,见他无意追究,也就茫然的点了点头。陈云正端详着一下子寂静下来的院落,脸上是少有的沉静。曼曼不敢走,只得陪站在一旁。
陈云正只盯着桂树出神,竟不知神思飘到了哪儿。
曼曼几欲张口,又觉得自己身份实在尴尬,为了免去以后的烦扰,还是少开口为妙。
陈云正却开口了:“我知道,是徐妈妈跟太太告的秘,也知道你是冤枉的……”
曼曼沉默。这些她也知道,她还知道,若不是他的庇护,只怕这会自己已经死了,或者受了很重的惩罚,不定被贬到哪儿去了。
但,这情份,不足以让她用一辈子的愚忠来抵偿。也或许,应该早些跟他把话挑明?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啊孩子啊,是花骨朵啊,自己真的能下得去手摧毁这娇嫩的花骨朵吗?
正愣神呢,听陈云正道:“……都是暂时的,你也别嫌闷的慌,等到风平浪静,我带你出去逛。”
明知不妥,曼曼还是掠过欣喜:“真的?”
见陈云正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莫名其妙的有些脸红。不是自己贪玩,可实在是来到这个世界几个月,都没怎么去外面瞧过。
平时不觉得,但偶然一想起来,还是觉得在这院子里跟住在囚笼一样。从前还能去园子里转转,这回把园子门一锁,就这么个小院儿,人又都叫陈云正给撵走了,她非得疯了不可。
陈云正见曼曼高兴,也不由的暗自欢喜,面上却不显,眉头一蹙,道:“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你喜欢去哪儿?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曼曼下意识的就想拒绝,随即又想,横竖与陈夫人撕了脸,现在能倚靠的,只剩下了陈云正,何必呛着他的意思?
或者再恶毒些的想,陈云正的将来与她何干?他爱不爱读书,有没有前程,那是陈老爷、陈夫人该着急发愁的事,她费尽心力也落不到好,还不如替自己想想。
因此曼曼道:“去哪儿都好,也不要做什么准备,若闹的人尽皆知,只怕老爷、太太又要责怪了。”
陈云正很是得意和自豪。
能够让曼曼顺着他的意思行事,他很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因此背着手,点点头,思忖了一会,道:“你这话对也不对。不当兴师动众是对的,否则老爷和太太只会说你勾着小爷不思进学,只知贪玩,免不得又要找借口责罚你。”
曼曼无耐的叹了口气。她算是和陈云正绑到一起了,他若好了呢,自己未必有功,可他若是出丁点点事,就是自己的错。
还真不能脑子一热,意气用事,真要传到老爷、太太耳朵里,可不是自己受罚么。
因有了顾忌,曼曼便存了疑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便瞪大眼睛问陈云正:“依六爷的意思,该如何呢?”
陈云正呵呵一笑,点头曼曼道:“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儿你得承认你也有不如我的时候了吧?”
不如他的地方多了,谁让他是男,她是女,他是主,她是仆呢?世俗规矩,都是给她定的,于他来说束缚却少,她不问计于他,光指着自己能有什么办法?
曼曼陪笑道:“夫子所言,自然正确无比,况且奴婢从来不敢妄称强过六爷啊。”
被曼曼拍的浑身通泰,陈云正收了洋洋之色,正正经经的道:“所以么,你刚才所说不必有所准备是错的。我们要出门,得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做好准备才是。这样——我去学堂,你在家里做准备。”
说不轻视他,那是曼曼撒谎,她就想着,他一个小屁孩儿,就算看过猪跑,可他又没真正往外边胡天胡地,风花雪月过,再早熟,也是个孩子,他能知道什么?他还能安排个什么来?可谁想他竟安排的头头是道。
他要出门,毕竟是富家少爷,带的人是少不了的,除了白术、白莪,还有府里的家丁,就为了防着万一出了什么事没人照应。
带丫头的也不是没有,但对于陈云正来说,带谁都不合适。带个年岁大的,会被人笑话,带年岁小的,比他还小,那就别指望着出去做什么了,一路上就带孩子吧,带曼曼这么大的丫头,更显得不伦不类,可若他换了身份,那就不一样了。
陈云方安耽的享受着夏娆等人的服侍。
有给他捶腿的,有替他按肩的,还有专门替他剥葡萄皮的,夏娆则偎在他的身侧,蜷缩了做猫状,任他抚触,同时絮絮的讲着秋蕴居里的热闹:“……太太动了怒,可是拗不过六爷,只得将院子里一干人都带走了。现在秋蕴居已经锁了通往园子里的院门,也只留了两个粗使婆子,院外是老爷派的四个家丁轮班巡守。”
陈云方懒洋洋的道:“小六儿什么时候这么有心计了?我这当哥哥的都要自愧不如了。”
夏娆听着陈云方并没有着恼的意思,便乍着胆子道:“要说也是咏芳妹妹太急切了些,没能达成爷的心愿,倒让六爷起了护短的心思,人都撵走了,偏把苏曼曼更严密的保护了起来……”
陈云方睁开眼,瞄了一眼夏娆,笑道:“小六护着自己的人有什么不对?难道爷没护着你们不成?”
夏娆虽是妒嫉咏芳后来者居上,得了陈云方的格外看重,但毕竟陈云方对她们几个也并没多冷落,并且因为近水楼台,自然要多得一些爱宠,更兼她冷眼瞧着,陈云方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在曼曼身上,因此嫉妒是有,但唇亡齿寒也是真的。若这次咏芳得不了好下场,估计她们日后也就有了比照。
因此不敢实话实话,只略略顿了顿,便道:“都说患难见真情,爷也应该让咏芳妹妹吃颗定心丸了。”
陈云方不免笑道:“素知你是个机灵的,难得还有这份体贴,罢了,替我拿衣服,我去娘那边瞧瞧。”
陈夫人十分的闷闷不乐。
一朝疼宠在怀的儿子,忽然腾升了羽翼,不由自己掌控,不听自己的话,不愿意偎依在自己身边,甚至露出小爪牙要表现自己的力量了,凭谁心里也不舒服。
陈云端和陈云方此时都聚在这里,无声的劝慰着。
说是劝慰,其实是各怀心思。知子莫若母,陈夫人又长他们这么多,一打眼就能知道陈云端是什么心思,他来,定然是李氏让她来的,嫌自己手伸得太长,把徐妈妈打发过去了。
李氏就是个心胸狭窄,眼皮子浅的,这才哪儿到哪儿,又坐不住了?亏得她也是大家闺秀出身,怎么就这么上不得台面,一点忍性都没有,将来这偌大陈府又该如何交到她的手里?
这大儿子也是个耳软心活的,媳妇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还有没有一点出息?
这老三,跟他湿没关系干没关系,他杵在这又是为了哪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