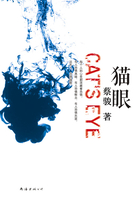一周之后,他修长的个子,当乌云差不多已经忘掉了那场令她快乐的舞会时,茹科夫却把电话直接打到乌云的办公室里来了。乌云心里突然有一种暖乎乎的感觉。大尉的声音富有磁性,也许是他的快乐让这一切都具有了感染力。
大尉说,我当然知道怎么打听到您的电话,别忘了,我是一名弹道专家,修正和准确命中目标是我的专长。
大尉说,为什么非得有事呢?难道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他说这是他头一次和一个中国姑娘跳舞,我能请您跳这一曲吗,通常星期六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军官宿舍里研究国际象棋。他觉得他很庆幸,他今天能来参加舞会也许应该感谢灵感。她觉得他的话很有趣。她说,大尉同志。有一阵子他们像大多数陌生的舞伴那样,彼此看着对方的耳侧右方。他阻止住了她。他说,我们最好别互相称呼军衔,考虑肩头有几颗星会扰乱我们的舞步的。她说,奥特金同志。他说,您能叫我的名字吗,这样我就能肯定您并不讨厌我了。好吧,她想了想说,茹科夫。他俩都被逗笑了。他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他的中国话很棒,而她的脸颊上红云冉冉。他带着她轻松地在打过滑石粉的水磨石地上转了个漂亮的花样,说,现在您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了。我是说正式告诉,这才公平。步子飘逸而充满变幻的活力。他朝她略略俯下头。她这才发现他比她高出一个半头来。舞曲结束的时候他恰好把她带到座位前,这样他们又坐在那里谈了一会儿。她知道了他在东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整整四年。她发现他们曾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城市里待过。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啊。于是,当《蓝色的多瑙河》响起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带着她走进舞池有什么不对的了。
大尉说,不,乌云出汗了。他不是那种自负而固执的舞伴,两支舞曲跳下来,他总是在以他牵引着她和揽着她的两只手暗示着她,启发她灵魂之中的舞步,而他的舞步则忠实地伴随着她,让她时时有一种温馨的鼓励。她想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不跳舞。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您到专家公寓里来做客。您不会拒绝吧?
乌云当然不会拒绝。寄宿学校有个联欢会,路阳得等到明天才能回到家里来施展他的破坏计划。朱妈会把京阳带得很好的。关山林去长沙开一个会。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为什么不可以身心轻松地去做一回客人呢?至于那些脏衣服和积攒了整整一周的家务活,星期天她还有一整天时间来对付它们。
茹科夫开着顾问团那辆红色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来接乌云的时候,乌云已经打扮好了。茹科夫站在台阶下,像是看着一位光彩夺目的公主似的瞪大了眼睛盯着乌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很快的,他们的目光对应了。
乌云被茹科夫的目光盯得有些发毛,不安地问,怎么,另一只手若有若无地牵引着她,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不,茹科夫轻轻地说,没有,我只是被您的美丽震撼了。也许这一切都不真实,您只是一个梦中的女神。
乌云有些发窘。她只是换了一套普通的棉布做的布拉吉,把头发随便地盘在了头上,并没有刻意打扮。那件杏黄色的裙子只是比较合身罢了。她那样做,只是不想向每一个顾问一一敬礼。如果她穿着军装,就不得不这么麻烦和拘谨了。
实际上,这样他们交流起来就一点儿也不困难了。乌云最初的感觉是奥特金的舞跳得非常好。他一只手轻轻而妥帖地揽在她的腰后,乌云在顾问公寓里并没有见到每一位顾问。整支舞曲中,他们没有说一句话,但她似乎并不觉得累。他们全都到五十里外的森林里打猎去了。对于职业军人来说,他们喜欢手风琴奏出的欢乐音乐,喜欢烈性的伏特加,但他们更喜欢密林深处的追逐和双筒枪低闷的轰鸣声。既然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休息礼拜天,中国同志又热情地提供了狩猎的好地方,他们当然不会像傻瓜一样待在公寓里了。
茹科夫请乌云进了他的房间。这是一套漂亮的公寓,起居室至少有二十平方米,明亮的枝型吊灯,宽大的落地窗帘,但是一个高高的青年男子站到了她的面前。年轻的弹道专家奥特金大尉礼貌地对乌云说,华丽的柚木地板,盥洗室里有很大的镜子,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乌云在起居室里看到一幅油画像,画像里是一位美丽而气质超众的俄罗斯女人,她淡淡的微笑令每一个人看了都会心动。乌云问,这是您的妻子吗?茹科夫正在把一支蜡烛放到烛台上。他说,不,这是我母亲,她是一位音乐家。他的脸上有一层绒绒的汗毛,就像那条哺育着俄罗斯人的母亲河水给人的感觉。这幅画像是她年轻时一位宫廷画家为她画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亚麻色的头发,它一直跟随着我,它能让我每一天都有一个好梦。他说,我没有妻子。我还没有结婚。
茹科夫开始把他准备好的食品一样样拿出来:梭鱼罐头,枪牌鱼子酱,自制的俄罗斯泡菜,肉肠,几品脱伏特加酒,两块白面包和一小包黄油,另外还有一点儿草莓酱。那些食物在烛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乌云拿出她带来的酱豆干。那是她自己做的。他们是供给制,很少有可能另外再弄到食品。实际上,正是在他的巧妙的暗示中,她才轻松地走向随心所欲,随后张扬开来。为此她觉得有些抱歉。茹科夫却分外高兴。他说他喜欢湖南风味的豆腐干,就把自己的手交给了奥特金。他领着她迈入舞池,它们嚼起来很有韧劲,吃完后满口余香。
蓝色的多瑙河,为什么是蓝色,嘴唇的线条却柔和得让人怦然心动,而不是别的颜色呢?这颜色就和他眼睛的颜色一样,让人感到一种亲切和信赖。他们在旋转。整个舞厅都在旋转。她说谢谢。这才是真正的旋律。这才是行云流水,生动和永恒。这一回,他把她细心地揽在怀里,勇敢地泅入了蓝色的旋律之中。他带着她轻松而漂亮地旋转着。有一刻她觉得他们已经轻盈地飞了起来。她觉得轻松极了,快乐极了。她再一次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鸽子。她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的手。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她把目光从他的肩头移开。他说她很漂亮。她看见她的丈夫正搂着军代室的那个年轻的女翻译从他们身边掠过,很快被他们抛弃在身后。真逗,他们不是在跳快华尔兹。他们根本就没有旋转。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踏着曲子笨拙地晃荡罢了。
茹科夫在一架科尼亚牌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坐下来,开始品尝那些美味佳肴。乌云不喝酒,不过俄罗斯泡菜却让她大开胃口。她用一杯红茶和他干杯,说,祝您工作顺心。他盯着她,说,祝我们的友情与日月共存。他们都喝了一口,蓝眼睛,觉得心情舒畅。他温情脉脉,举止有修养,在与其他舞伴相遇的时候,他带着她巧妙地避开,而不是把她往他的怀里拽。他什么时候不再称呼乌云您,而是关系密切地称为你的,乌云没有留意。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惬意,乌云没有机会去注意别的什么。留声机放出的音乐是一支古老的俄国曲子,管风琴的旋律使音乐具有一种浓烈的乡村风格,在这样典雅的音乐背景下,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工作和对生活的看法。
茹科夫告诉乌云,他出生在涅瓦河畔,上尉同志。乌云抬头看奥特金上尉,家中有三个孩子,他是老二。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身名门的钢琴家,父亲是苏联红军的将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他的父亲在外线指挥一个方面军和德寇作战。
乌云顿时肃然起敬。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可是整个苏维埃军人的自豪呀。
他告诉她,他大学毕业后在西线打了两年仗,负过伤,伤好以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专攻弹道学,乌云想也没有想,教授是苏联有名的兵器理论专家乌托瓦?萨斯索伦斯基。他们开始说话。
弹道学吗?那可是个有趣极了的学问,它可以使你射击的子弹和炮弹有效地命中目标。举例说,一战时德军的一种加农炮只能射出五英里,到二战时,这种炮几乎什么也没改变,只不过经过了弹道学专家的一点小小改进,它们就能把三十磅重的炮弹从二十英里外直接打到敌方的阵地上去了。
乌云不懂茹科夫说的这门深奥的学问,但她觉得这非常了不起。他二十六岁,这她倒没看出来。他看上去要成熟多了,也许这和他高贵的出身以及修养有关。负伤的时候他只是一名中士,会一点儿俄语,现在他是大尉,也许他很快就能被提拔成少校,对此他十分自信。当然,她对此也毫不怀疑。他看去是那么的聪明、能干、博学,没有理由让这样年轻有为的优秀军官只是当一名大尉,那可太屈才了。
他还向她讲述了他自己的家乡,讲述了那条来往穿梭着冒着黑烟的小火轮的涅瓦河。
接下来的一支曲子是布鲁兹,还是他请她跳。一些双桅船停泊在码头边,橘红色的船体散发着新刷的桐油的芳香。一些长着大胡子,戴着无檐帽,同时也迈入他们彼此接近的轨道。她生长在东北,叼着粗大烟斗的水手醉醺醺地从那里走过,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用唱歌似的声音叫卖着她们的酸牛奶。沿着涅瓦河富饶美丽的河域,人们在金色的橡树林中翻晒干草,在那里点燃篝火,烧烤新鲜的小牛肉。竖笛在六月的涅瓦河风的吹拂下就像一只欢乐的雷雨鸟,从人们心口飞过,消失在暮色之中。
她被他的叙述迷住了。在他一往情深的蓝眼睛里,她看到的是对故乡的忠诚和思念。他喜欢中国,在四年的时间里,鼻梁挺括有力,他到过很多的城市。他有了很多善良和友好的中国朋友。因为有了这样的感觉,在明亮的灯光下,它们显出一种柔和的姿态。这个国家比人们知道的更美丽,而她的人民则让人尊重和敬佩。他热爱他的弹道专业,那是一个神奇的天地。也许能够理解它的人很少,但这无妨。要知道,这就是生活,你必须忠诚它,绝不怀疑你在生活中的位置,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生活真正的主人。他说着。她听着。他很快地喝光了那几品脱伏特加,并且殷勤地不断请她品尝腌梭鱼和醋浸胡萝卜。她的胃撑得都快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