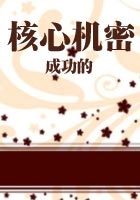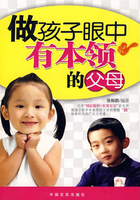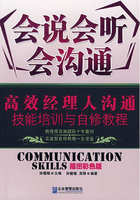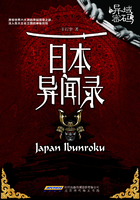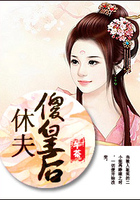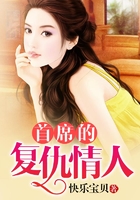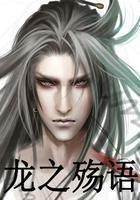手边的这本《我和端端》,我在十多年前读过。如今再读,感觉依然亲近、真实,于无声处,心弦被拨动。
现在想来,我认识于老师一家也快二十年了吧。记得很清楚,初见于老师的时候,正值初秋,他着一件风衣,说话声音不大,手里拿着几本书,还有一些稿纸,唯一显现出他是东北男人的,是他的大胡子。其实让我更加真切地记住于老师的是她的爱人——那天早上,一个像小燕子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的女人——确切地说,她跑到于老师的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快给我点钱,我在早市看好一块花布,我忘了带钱了。”连声音带样貌,都是小女生的样子。可是于老师说,那是她的爱人。一个小鸟一样的女人!我记住了她,也记住了这个让“小鸟”依靠的作家男人。
见到他们的儿子时,已是初冬了。那天好早啊,一个还没有桌面高的小男孩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手里举着一张大卷子,尖声尖气地和我说:“阿姨,我是于德北的儿子,我来印张卷子,然后记在我爸的账上。”哈!看到他小模小样的神情,听到他一板一眼说话,我一下子就笑了起来。我把印好的卷子放到他的手里,问他:“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你会过马路吗?”他使劲地点头:“能!”小家伙可爱的样子让人心疼极了。我让弟弟尾随他身后,护送他到家……而端端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已经参加工作了。前两天,当我把这一幕说给他听时,我竟发现,他微笑的神情,还是当年那个小端端的样子。
翻看着《我和端端》,心也跟着书里的故事游走。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他踮着小脚前进的样子像一头小小的梅花鹿……”细柔的父爱溢满纸面,我想于老师写到这里时,一定是怕喘息的声音大了都会惊吓了孩子吧?
现在的端端,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男孩儿了——近一米八的大个子,浑身是结实的肌肉,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副眼镜,不仅透出文气,还有一股子英气、阳光之气、帅气!
端端好学。
这个孩子不同于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喜欢什么都三分钟热度。他是要么不喜欢,要么就喜欢到骨子里的那种。大概是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吧,这个孩子喜欢上了篮球。可是没有老师指点,就自己拿着一个大篮球,拍来拍去。拍着上楼,拍着下楼,拍着走路,拍着跑步,学习累了,他最大的享受是拍一会儿篮球。如果妈妈能放他半天假,让他尽情地玩一玩篮球,他就会喜悦得眼睛里放光。这孩子把篮球从初中拍进了高中,拍进了大学,拍得一身的结实肌肉,拍得活脱脱一个棒小伙子。
可能是大了的缘故吧,就在大学临毕业的时候,端端迷上了吉他。他学吉他的劲儿,和喜欢篮球的劲儿一样。当他刚刚可以把音符串在一起拨响一曲时,就迫不及待地弹给我听。看他专注的样子,让人欣慰和喜悦。一年过去了,现在从他手里流淌出的旋律,已能深深地打动身边的听者了。
端端感性。
这孩子喜欢结交朋友,对朋友全情投入。记得在他高一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春天花会开》,就是写他和同学之间的友情的。他在和我讲这篇作文的时候,说:这是真的。我看到他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我躲开了这让人心疼的眼神。
看着这只长大的小鹿,心里的感慨真是太多了。说心里话,现在的许多家庭为了培养孩子,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但收效却并不尽如人意。要培育一个健康孩子,不单单是多上几个课外班、再挤进重点高中就可以吧?许多家长不知道,他们的努力有时真是南辕北辙!一些脱离孩子天性的拔苗助长的培养,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怎样的接班人呢?
健康的孩子,是社会的财富;健康的孩子,更是父母辛劳的成果。
端端大了。这只小小的梅花鹿也健壮了,可以健步地奔跑了。
《我和端端》里的故事我熟悉,《我和端端》外的故事我也知道。
东北的冬天很冷,而且雪大。几年前的冬天,于老师下班回家,雪已经半尺厚了,他正走着的时候,脚踢到了一个硬东西,弯腰去摸,拾起一个黑包,包很重,因为天寒而变得又凉又硬。当时雪像帘幕一样不断地垂下。于老师抱着包,一动也不敢动地在原地站着,一站一个多小时。于老师的爱人阿瑞在家等急了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他已经在雪地里站了那么长时间——原来他是怕主人发现包丢了,回来寻的时候寻不见,所以他就“守株待兔”,希望失主快快出现。因为这个包,他和爱人忙了半宿找主人;也因为这个包,他认识了包的主人,两家人竟成了朋友。
就像于老师在《我和端端》里说的那样,夫妻两人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相像,总是早早地把“底牌”亮给别人,总是让自己处在吃亏的位置,而且吃过亏以后还会常常觉得很值得安慰似的。
就说前几天,我们这里做“暖房子”工程,需要把每家的窗外户栏拆掉。于老师家一共有三个窗户,也就有三个护栏,南面两个,北面一个。和来拆卸的工人讲好,拆三个护栏,工钱一百五十元外加拆下来的护栏一并送给他们。可拆完北面的护栏后发现如果南面的都拆了,就再也没有地方放花盆了,于是阿瑞就决定把南面的护栏锯下去上半截,把下半截留下来,这样在夏天的时候,窗台就可以养一些花了。可是拆卸的工人听了却一百个不依,说这样他们就吃亏了。阿瑞一听人家吃亏了,连忙说:我把你亏的地方补上。对方见阿瑞好说话,就喊:再加二百!这放在哪个家庭主妇身上都知道,剩下的两个半截护栏,再值钱也值不上二百啊!可阿瑞硬是觉得对方不容易,满口应承下来。结果是拆了一个护栏外加两个半截护栏,硬生生地花了三百五十元。拆卸的人心满意足地走了,我想这阿瑞可能也会觉得亏吧?可是一问,她却说:他们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活不太好干,心里想只要平安干完了,再多花点也行啊!
这是一对常吃亏却常觉富足的夫妻。说富足,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富足的。《我和端端》里有一段是写当年他们生活的窘状的,可那样的日子,他们却过得有声有色:在漏雨的屋子里,一个男子汉在“顶天立地”,日子清贫,郊外有他们三口之家的欢声。
在他们家的窗檐处,有一个小小的燕子窝儿。那燕子每年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家就多了一些成员,走的时候,便带走了他们的全家惦记。我常想:燕子是不会在乖戾的地方停留的。这是一户安宁祥和的家庭……
书中的叙述和缓、亲切,当你读它的时候,就像和自己的邻居在一起聊天。更多的时候,就像是在面对自己,面对内心深处的那个干干净净的自己。
这是一个善良、平凡、有爱的家庭。中国这样的家庭有很多,他们真挚、淳朴、热爱生活,他们不吝把爱和关怀给别人,而温暖的爱就在他们的心窝里涌流得越来越多。我喜欢读这样的故事,我喜欢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陪伴我,缓解孤独,伴我安睡,给我温暖,慰我忧伤。
认识这样的一家人,就如与一片湖水为邻,舒心,美丽。你看窗外的秋阳,你看那蓝色的天空,你不感到生活很美吗?暖洋洋、甜丝丝的美。
生命中很多人都是在眼前一闪而过,闪过去后就再没什么可记住的了。而于老师这一家人却在不经意间轻轻地走进我的视线,然后就深深地留在我的生命里了。
王 玫
201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