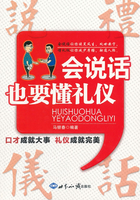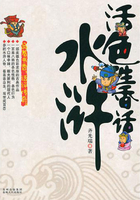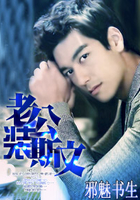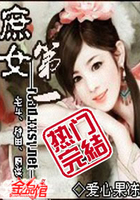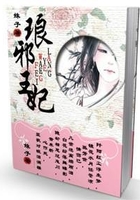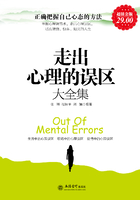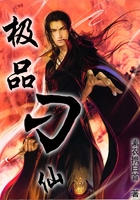《少年文艺》主编沈飚从南京打电话来,他们全家要来长春,然后取道通化,去二道白河,上长白山。我们早就说好,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全家一同陪他们上去。
日子被计划了,就过得飞快。7月26日,沈飚一家抵达长春,第二天,我们一行五人直奔那个北方的旅游胜地。
我第一次去长白山时才19岁,当时《文艺时报》举办笔会,我的一篇小说获奖,所以,我是以工作人员和获奖者的双重身份去的。我登长白山的时候,天上下着雨,上山的路极其难走,我单衫薄履,怀揣一瓶白酒,去和天池对饮,而我的下酒菜就是天池水。
我在天池边留了一张照,头发飞扬,张开双臂,拥抱神山圣水。我醉了。
端端懂事后,我常和他提起长白山,常和他讲我“年轻”时的故事。
我读过许多关于天池怪兽的资料,我答应端端,有一天,带他去看长白山。沈飚要来,正好也帮我圆了一个梦。
我和端端的行囊很简单,内衣裤、袜子和两件长衫。我们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跋涉,终于到了二道白河。原来此行也应该有端端的妈妈,可是因为家里要装修房子,她只好放弃这一次家庭旅游的机会。
我们找了一家非常便宜的旅店住下,沈飚一家住一个房间,我和端端住一个房间。想一想,这一次旅行,是我和端端第一次离家独处,我们像两个真正的男子汉,干净利落地处理一应事务。晚上,我写日记,端端看《辛巴达历险记》,有精彩的镜头,我们用寥寥数语交流。
第二天去长白山。也许是对我们长途奔波的照顾,一连几日不开晴的长白山在我们驱车登山的那个早晨,有了片刻的“阵雨初散”。我们一抵达主峰,就有人兴奋地告诉我们:“快上去吧,天池开了。”
我拉着端端的手,快步向顶峰冲去。熟悉长白山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阴霾天气,见到天池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见到天池了!端端的表情有点儿严肃。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懂得感受的孩子,天池的冷峻和宁静一样可以抓住他的心。
我问他:“漂亮吗?”
他点点头:“漂亮。”
也许,在一瞬间,他也想到了天池怪兽。有人说,天池是和尼斯湖相通的,两个地方的怪兽可以互相来往。我乐于把这样的话想象成童话。
从长白山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们选择归程。沈飚和夫人、孩子取道延边,然后去镜泊湖、哈尔滨,之后回长春,再从长春返回南京。我则选了一条经大蒲柴河、夹皮沟、桦甸、吉林回长春的路线。
我们有去集安的打算,怕时间不够用,所以,选择这个“半圆”回家。选这条路线的原因还有一个,我想让端端在领略自然风光(这条路线三分之二在山区)的同时,学会看地图。来长白山之前,我特意买了一张新版吉林省地图,以便在上边寻找以前不知道的途径。看来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真就选择了一条以前从未听说的公路返程。也许这条公路早就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我和端端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展开地图,一程一程地校对我们所经之地。车子每到一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小圆圈,我们知道,计划的地方都画上圆圈之后,我们就该到家了。
早晨下了一点儿雨,空气异常清新。公路两边时常可见斑斓的大鸟,嘎嘎嘎嘎地飞起或落下。还有山花,烂漫了一程又一程。我尽我所知,给端端讲述长白山的典故、传说和人物,我相信这种“实地教学法”胜于空洞的“填鸭”。大蒲柴河的林蛙,夹皮沟的金矿,红石林业局曾经有过的几个诗人……
可以说,我和端端的旅途一点儿也不寂寞。
车至桦甸,我思虑再三,决定在这里换乘,我想简单地休整一下,吃点儿东西,和家里通个电话,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两点,我们已经在车上颠簸了八个多小时。
在桦甸汽车站,我给端端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们在桦甸呢!”妈妈愣了。也是,在她的概念里,我们是不该在这里的。
我解释说:“我们找到一条路,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妈妈问:“安全吗?”
我说:“不安全的路都走完了,剩下的路基本都是平川了。”
妈妈放心了。
我和端端坐在桦甸车站的候车室里,他双手抱着自己的背包,我们转乘的车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出站,我借这个机会和端端聊聊天。我说:“回去可以写一篇作文。”
端端说:“还可以画点儿画。”
我说:“还可以和小朋友讲一讲见闻。”
端端说:“把地图拿给他们看看。”
我笑了,心里非常温暖。
从地图上看,我们从长春出发,至通化,取道二道白河。之后,从二道白河经大蒲柴河,过夹皮沟、桦甸、吉林回到长春,正好是绕了一个大圈。
圈也可以理解为句号,也就是说,我和端端陪沈飚一家去长白山的行程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端端有很多收获:进一步了解了我和沈飚的友情,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学了一点儿地理知识,在离家的日子懂得照顾自己……
如果每绕一个大圈就让孩子有所收获,我希望和端端一同再绕几个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