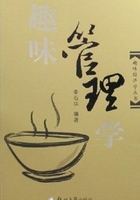虽然我也曾经是个很干练的人,但却被出现在眼前的这个文弱却又强悍的女人给镇住了,一时间心里堵得说不出话来。我愣了一会儿,说:“靠左第一间房,全是些换穿的衣服,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说着,便借着话题跟何涛一起往饭馆里走去。
看来何涛是个很热情的人,他搭着我的肩,嘻嘻哈哈地说:“哥们儿,以前在部队里怕洗衣服不?告诉你,到了这儿,可以一年不洗衣服,外面脏了调个面儿再穿,里面脏了再换外面,嘿嘿。”他提起我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包,掂了掂,又说,“哟,挺沉的,你小子还真打算在这儿长住啊?准备安家落户不?回头我好帮你联系联系!”
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我就没有放在心上。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出饭馆,周青重新检查卡车后面的物资是否绑扎牢固,因为上面盖了一层防水布,我也瞧不出他们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她检查完了,坐在驾驶室里等我们。
我发现何涛是个话痨,嘴巴像是被冻得合不拢了,所以就只好不停地说,借着运动产生的热能来温暖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他也始终不嫌累,不倦地和我唠叨着,即使是在开车的时候,两片嘴皮子也像嗑瓜子似的,吧嗒吧嗒地响。
周青看我有些沉默,不好意思地扭头冲我笑了一下,说:“他是个话痨,别怨他,在这个地方待上几年,像他这样算是正常的了。”
何涛又开始和我找话说,一边开车一边问:“肖兵,你咋想到要来可可西里?”
透过挡风玻璃看过去,外面没有阳光,天空也是灰蒙蒙的,车子在颠簸中沿着昨天他们开过来的车轮印前进,我没有回答何涛的话,只是向远方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望去。何涛看了我一眼,又问:“咋不说话?你还没待几年呢,刚来可可西里就犯毛病了?你该不会和马帅一样吧?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来,那多没意思!”
驾驶室很小,三个人穿得都很臃肿,我被夹在中间。我裹了裹身上的棉大衣,把双手往袖筒子里拢了拢,说:“来这儿之前,我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待了半年多,那儿的人生活很苦,碰上个天灾人祸的,衣食就没有着落。”何涛说:“别担心,咱们这儿虽然苦,但饭总是吃得饱的,虽然不咋好吃,总比没吃的强多啦!”
我知道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没理他,接着说:“我在那儿认识了一只獒,她的名字叫大黑……”
何涛插嘴,问:“獒?狗?很大的那种?听说獒可猛了,以前我战友邻居家养了一只。听我战友说,有一次他去邻居家玩,那獒可凶地站起来要咬他,要不是隔着个铁笼子,那命可就保不住了。哎哟,真他妈厉害,顶着脸地往铁栏杆上撞,要把笼子给拆了似的……”
话还没说完,周青瞪了何涛一眼:“别插嘴。”
何涛闭了嘴,我继续说:“那是一只有灵性的獒,全黑的,很威猛,我刚到那儿的时候……”
何涛忍不住又插嘴,说:“全黑的?纯种吗?那得值多少钱啊?”
我只好说:“有一次,有人专门找到那个地方买獒,就那只黑獒,对方开价就是三十万美元……”
何涛惊叹地咋舌,说:“我的个天哟!我以后回家了也要养只獒……乖乖,真值钱,一辈子不愁吃穿咯!”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如果何涛是个贪财的人,他也不会把全部的退伍金都捐出来,到可可西里这个地方了。
我说:“以前,我不了解那只獒的时候也曾想过,为什么她的主人不肯卖,都出那么高的价钱了!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是那只獒教会我该怎样去做一个人。你说,人活一辈子,要是临死了还搞不清楚自己为啥活了一辈子,那该活得多冤啊!是不?”
何涛听明白了我的话,没有直接回应我,反而开玩笑地说:“哟,周青,咱们这儿又来了个哲学家,五花八门的,可都凑齐了。你说,咱们回去是不是该搞个活动庆祝一下?这下子可就好咯,小乐、杨钦他们可就不寂寞咯!”
他正啰唆着,车身突然猛地一晃,何涛的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他刚把身子稳住,车身又猛地一歪,就听车轮子“哧哧”地空响了几下,车子就不动了。
像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周青很老练地说:“陷住了。何涛,你去把车厢里的板子抽出来,肖兵,下去搭把手。”
我打开车门,和何涛跳下车。一下车,就感觉到脚在缓缓地往下陷,原本看起来什么也没有的路面,竟然是片沼泽地。何涛把车厢里一早准备好的厚木板抽出来,说:“现在这天气比起冬天来算是暖和些的了,白天的时候,气温稍高一些,表层的土壤就会解冻。你放心,这片沼泽地没有多深的,最深也就一米,一米以下就是永久冻土,来,把车头往上抬。”
我把车头使劲地往上抬,何涛一边帮着抬,一边把厚木板往车轮底下垫。这片沼泽区没有多大,可能这里曾经是一小片水湾,后来水干了,便成了沼泽地,刚才车子拐了个弯,不知怎么就给陷进去了。周涛说,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海拔高,气候特殊而且寒冷,这儿的沼泽地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可怕,车子在沼泽里陷上三天也不会沉,不用担心人和车子会被沼泽没了顶。铺好木板后,周青发动了车子,我们便走到车屁股后面去推车。
因为车上载满了物资,车身重量加大,所以一旦被陷住,再想开出去就很麻烦。周青说:“必须得把车子开出去,不然天黑以后气温骤降,没准车轮子会被冻住,到时就麻烦了。”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车子还是没能开出去,实在没办法了,何涛说:“要不把车上的东西扔一点下去?”正说着话,我们就看到,从昆仑山口方向开过来两辆草原吉普,还有一辆牵引车。那些人看我们被陷住了,主动停车问要不要帮忙。
我认出他们曾和我在同一家小饭馆住过,他们也认出了我。原来他们是科考队的,来这儿搞地质研究,刚才路上也出了点小状况。他们听何涛说我们是反盗猎志愿者后,就有几个年轻力壮的赶紧过来帮忙。车子总算是开出了那片沼泽地,为了赶时间,打过招呼后,便各自开车上路。
一路上,周青有些沉默,我问她在想什么,她没有直接回答我,有些漫不经心地自语:“或许,有些地区保持它的原始特征会更适合它的发展,人类的过度侵入反而是最大的危害因素,入侵、占领,然后灭亡,这就是一个又一个物种相继灭绝的原因之一。”
我猜,大概是刚才那一队科考人员的出现引发她如此大的感慨。人类的入侵和开发,将会导致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我在很早之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那还是和大黑在一起的时候。只是没想到,在可可西里这块被称为“无人区”的荒地上,人类活动的足迹也已涉入,所谓的“中国第一大无人区”,已经是名不副实。
天色越来越暗,车子一路颠簸,驾驶室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何涛继续开着车。天色擦黑的时候,气温骤降,驾驶室里突然冷得像冰窖。天色终于完全暗了下来,就算打亮了车前灯也无法完全看清前面的路况,我们只好停了车,准备在荒滩上过夜。
周青从随身的小旅行包里掏出面饼、方面便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盒牛肉罐头、一瓶水。三个人挤在驾驶室里吃着面饼、啃着方便面,所有的食物都是又干又硬。驾驶室里太冷,因为要半开着窗透气,所以就更冷,我们不可能在驾驶室里冻一夜,只能在荒滩上支帐篷。
帐篷是军用的,厚实而且透气性好,不过,在可可西里这种高寒地带,再保温的帐篷也顶不了多大用。我拉紧帐篷帘子,铺上厚厚的地垫,再把棉大衣盖在上面,还是觉得冷,从头到脚没有一丝温暖的地方。
听外面的风在呼呼地吼,不知道半夜会不会下雪。我睡不着,小声和身边的何涛说话:“装备都还挺全的,就是不管什么用。”
何涛与白天的话痨一反常态,没吭声,沉默了一会儿,向着帐篷边上的周青那边努了努嘴,小声说:“回去以后你才知道装备更全呢!不说了,睡觉,不然明早起来头痛……咦?你刚来咋没有高原反应呢?我刚来那会儿,整天吃不下饭,心里堵得慌,整天就像猪一样的死睡。”
我小声喘了口气,说:“我也觉得心里堵得慌,不过以前在高原地区也待过半年,所以适应得要快一些。”
何涛点点头,不再说话,蒙头大睡。我还是睡不着,觉得两个耳朵边像是有无数只苍蝇在飞一样,嗡嗡作响,胸口闷,手脚冰凉,听着帐篷外呼啸的风声,心里的失望向无边的黑暗中一层层漫延。我想:不知道到了驻地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睡袋口呼出的热气结成了冰花。伸手一摸脸,脸上竟然结着一层冰霜,鼻子被冻得通红,一钻出帐篷,就立即感觉鼻梁骨里面被冷空气冻得刺痛,像是有人在你鼻子里面插进了一根锥子。我开始收拾帐篷,周青在准备早餐。一旁的何涛开始发动车子,给发动机预热的时候,他也顺便跟着取取暖。
车子上路了,开出许久,终于驶出了戈壁滩和零零星星的积雪区,前面路上慢慢地现出一些稀疏的草甸,我问何涛:“地上那些小坑是什么东西留下的?”
何涛说:“是鼠洞。”
我数了一下,大概一平方米的地方就有十来个鼠洞,我很是吃惊,就问何涛:“你们平时吃肉吗?鲜肉?”
何涛笑了一下,说:“吃,不过大多是罐头,在可可西里这块地方吃鲜肉,那可是‘犯法’的,不过老鼠肉除外,就是周青觉得有点儿恶心。”他说着看了周青一眼,周青没搭理我们,拿着望远镜看车窗外两边半青不黄的草甸。我知道何涛说的吃鲜肉犯法指的是捕食草原上的野生动物,的确,在可可西里,几乎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是珍稀物种,只有老鼠除外,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按物以稀为贵的标准,老鼠们还挤不上排行榜。
我又小声地问何涛:“经常吃?”
何涛说:“嘴馋了就吃,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也去抓鱼,就是水太冷,没人愿意动手。对了,跟你说个故事,”何涛脸上促狭地一笑,把嘴凑到我耳边,想了想,又说,“算了,还是不跟你说了。”
被他这样一逗,本来对听故事没什么兴趣的我反倒被勾起了兴趣,不知道在可可西里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新奇的故事,于是追着问:“到底什么故事?快说!”
何涛哈哈地笑,然后板起脸来,说:“没啥。”
周青说:“肖兵,你别理何涛,他拿你开心呢。”她说话的时候头也没回,继续拿着望远镜瞄着远处的草甸。
可可西里的草甸子长得很稀疏,较近些的地方,可以看到草与草之间露出的黄土,不像藏北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的绿。这儿的草让人觉得发育不良,像是个在虐待中残喘的旧社会儿童,病恹恹的,让人瞧着就觉得心酸。按理说,在这片中国最大的无人区,草甸应该长得十分茂盛。本来我还想着可可西里这块地方会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是“青色的山梁”“美丽的少女”,也会像藏北大草原一样绿得让人心醉,但现在看起来却只能令人心酸。
“这儿的草长得真慢。”我自言自语着,仿佛心灵的草原也渐渐失去了给养,正在慢慢地荒芜,最后变得就像可可西里的荒滩一样苍凉。
周青举着望远镜继续瞄着远处,随口回答我说:“是啊!本来长得就慢,再一糟践,还没长出头就死掉了,一死就是一大片。这里环境恶劣,一年两年都恢复不了。”
“糟践?谁?”我反问道。
周青放下望远镜,回头看了我一眼,反问道:“你说除了人还能有谁?你、我、他。”
“盗猎的?他们只是捕杀野生动物……”
何涛插嘴说:“你刚来,还不了解可可西里,我刚来那会儿也有这个疑问,慢慢你就知道了。”
据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是车子开了那么久,我却一只野生动物都没有看到。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什么原因,眼前除了荒漠就是半黄的草甸,一望无际的荒凉,除了车身在晃动,看不到半缕人烟。周青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一声不吭地把望远镜递给我。
我接过望远镜,迫不及待地向远处望去,镜头里出现远处半青半黄的山梁,看起来光秃秃的,草甸与荒滩间杂交错,远处似乎有几个黑点在驻足凝望。
周青知道我在看什么东西,就说:“那是几只野牦牛,运气好的话或许能看到几只藏羚羊,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看到,它们也是远远地就逃跑了。现在这儿的野生动物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看到人和车子就飞快地逃开,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和人类亲近了。”我沉默,没说什么,继续瞄着远处,周青似乎有很多的感慨要发泄出来,她叹了口气,又说,“人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逼着动物与自己疏远,再逼着它们灭亡,或许当所有的野生动物都灭绝了,接下来死亡的就是人类自己。”
周青脸色忧郁,她把胳膊支在车窗上,手托着腮,脸色很凝重。看得出来,她是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或自己打动。而我的心头却渐渐起了一层疑惑:这样的人能做好“暴风”的领导者吗?那可是真枪实弹地与盗猎者对抗啊!
没来可可西里之前,我一直对可可西里这片神秘的地方充满着好奇和憧憬,一遍遍在脑海中幻想着它的美丽。但到了这儿之后,一切都令我觉得无比的伤感,最初在小饭馆里留下的那么一点儿好心情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阴暗。我们都不再说话,车子晃晃荡荡地开着。路上,我终于看到了一群野驴,离得远,看得不太清楚,它们一看到车子,就飞快地逃,但是又摸不清方向,反而与车子越跑越近,倒像是在和我们飙速。
何涛开玩笑地说:“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弱点,就像野驴,它也知道见了人要赶快逃,偏又摸不清方向,结果反而与人越跑越近;再比如藏羚羊吧,一到了晚上,胆子就特别小,哪儿有光就往哪儿挤。肖兵,你的弱点是啥?”我一愣,马上明白过来,反问道:“你说我是动物?”
何涛说:“哪儿跟哪儿呢?两条腿的难道不算是动物?你知道啥叫动物吗?动物动物,就是可以不依靠外力自己移动的物体。”我刚想反驳,就听哗啦啦一声响,一只灰黑色的猎隼从车前头飞过,打断了我的思路。
已经过了中午,远远望去,我们似乎已经进入可可西里的腹地边缘—最接近中心地带的边缘区。从望远镜里望去,那座山脚下似乎有一条小河,河边上一排营房在镜头里凝成一排黑点。
我放下望远镜,心头一阵悲凉。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反盗猎组织都居住在有人烟的地方或是小镇上,只是在巡山的时候才会驱车进入可可西里,而“暴风”却驻扎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山脚下。这里没有人烟,也没有小镇,不管是气候条件,还是地理条件,所有的一切都恶劣到了极点。更令我惊奇的是,这样的一排营房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材料设备是如何运到这里的?为什么要把驻扎点选在这个地方?我怀着满腹的疑问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镜头越拉越近,营房也越来越近。我看见灰色的砖墙,房顶上架着天线,一根一根的电线也不知从哪间房里拉出来。电线?这片荒滩上哪儿来的电?
镜头再一次拉近,我的眼前出现了几张大脸,一张张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红,更显得牙齿的雪白。其中有一张脸令我印象深刻,因为眼睛特别细小,一笑起来,就更显得只见牙不见眼。那张脸越拉越近,仿佛就贴在望远镜的两块玻璃片上,最后放大成一对挤得瞧不清眼珠的大眼皮。
“喂,兄弟,瞄啥呢?都是大老爷们儿的,哥们儿可不好这一口啊!”那对眼睛的主人猛地拍了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