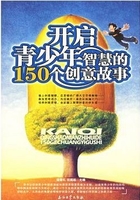马义从殡仪馆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五点。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张厚重而密不透风的裹尸布一样笼罩着这个城市。目力所及范围内的一切都显得发黄发暗,以一种模糊、放大的姿势悄无声息地病恹恹地萎缩在那里,似乎和他一样不堪重负,陪同他等待着黑夜的真正来临。夜代表着沉默与休息。马义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几天来,笑意就像一个迷途知返的孩子第一次从他的心里爬出来,但刚到嘴角就被他无情地吞了回去。他拼命连续咽了几次口水,觉得喉咙发干。身体里的水分都化作唾沫,在几天里被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榨干了。
他朝前方街道看去,几个模糊的影子闪来闪去,似乎还有个人转过身来朝他大喊了什么,看他站在原地不动就跑开了去追前面的人群。马义等他们全部消失不见,才抬脚试着走几步,他感到右边小腿发木,刚一落地整个身子就不由自主地朝前倾覆,他赶紧蹲下来,像个先天畸形的残废人一样,双手按着脚面朝左侧的一棵刺槐树移动。二十三步,他左手开始摸向树干,却始终按不到实处而使整个人侧翻在地。眼镜已经丢了三天了,所有的东西都被自己瞳孔恶作剧般地放大。就像刚才,例行公事地掀开红毛毯看唐雨最后一面,所有人都虚情假意地阻挡他,但他明白,即使自己是一个演员,哪怕再嫌恶,在自己这一环也不能出茬子。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唐雨硕大的脸庞。都怪他自己,先紧闭着眼睛,等完全掀开后才突然睁开,以期像从前一样与唐雨来个四目对视,当然这已不可能。那一刻,他又掉进四年来一直驱逐不散的梦魇里。
梦里,他睁开双眼,突然遭遇的是唐雨硕大的脸庞,近在咫尺,他甚至感受到了眼睫毛互相擦过时刻保持的湿润,精心雕琢的皮肤的颤动感,然后这一切仍然在更加逼近,唐雨似乎想把脸从他眼睛里塞进来。而后,脸开始向上攀移,与他眼睛相视的变成嘴,他的眼珠由原先感受到的窒息开始变为向外奔突的愿望。吸力非常巨大,在那张大嘴的呼吸之间,他的眼珠仿佛艰难跳动在无边的沙漠上,任狂风掠起的黄沙蹂躏、鞭打。有一刻,他真想放弃抵抗,像做爱时经不住唐雨继续坚持的要求而举手投降最终一泻千里一样。
马义承认,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几乎从未有过,他从未与自己的本能进行对抗,已企图延长与唐雨交欢的时间,更为准确地说,他从来都无动于衷。时间的长短他似乎从未留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交欢时他想的都是其他问题,房屋的装修,明天的报告,什么时候回乡下等。这一刻倒反成了他最佳的休息时间,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想,干瞪着眼像个骷髅一样大脑一片空白。据说,这是审美疲劳。但马义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所有流行的、众人普遍接受的说法总是幼稚乏味的,总是游离于事实与真相之外的。他没有任何理由,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非要理由。何况,他从未对第二个女人产生过任何冲动,刻薄点说,从结婚那天开始,女人这种东西的性别特征就从他心里永远消失了,一切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就像上交期末总结和职称报告一般,唯一的区别只不过需要两个人来完成。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件事争吵过。
马义突然想起来,自己从未问过唐雨的感受,他为这个念头有点心酸,苦涩的感觉像一根锥子扎进满是厚茧的老手,慢慢才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对于一直没有遏制自己延长交欢时间的做法,此刻马义由衷地感到内疚,当然,对一个已死的女人因为交欢而产生的内疚会让人觉得可笑。而且,这有必要吗?马义忘不了梦魇的最后,自己分明看见,有无数黑色的小虫子,不断从唐雨的喉咙里爬出来,从她的舌头上一跃钻进他的眼睛里。马义觉得这是有象征意味的,预示了什么他一直想不明白,现在也无须追究了。
马义此后一再要求唐雨背对背睡觉,他惧怕突然睁眼醒来,塞入整个眼帘的那张硕大的脸庞。唐雨不理解,追问为什么,马义解释不清,何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幸好唐雨是那种如果你一再坚持最后她绝不反对的女人。
那么,唐雨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呢?秋天的黄昏,坐在树下的马义这样问自己。一个相处四年的妻子,马义却觉得自己了解得很少,他所掌握的仅仅是她的休息时间、阅读爱好、经常吃的菜以及喜欢的化妆品的牌子。就这些马义还经常与单位一个喜欢炫耀的女同事搞混。马义拒绝娇弱、温柔、善解人意、忠诚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些和现在的天色一样模糊。人永远是无法真正了解并无法言说的动物,特别是女人。有时候,了解比理解更困难。那些字眼和化妆品一样,只能反映出一个女人最表层的东西,至多是性格偏好,而和这个女人无关。马义觉得头疼欲裂,他用劲拍打着树干,但没有效果,又反手过来拍打自己的脑袋。回忆像成群的蜗牛拥挤在通路里,把血管严严密密地堵塞了。
很长时间以来,马义觉得自己的头部在不停地胀大,他曾经看到《少林足球》里赵薇的光头时,就想象着如果把自己的头拧下来像足球一样踢远,也许,世界在那一刻才能清明下来。同样是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那个无风无月密封在罐子里一样的晚上,唐雨情意绵绵又不无恶意地偎在枕边对他说,她也想钻到马义的肚子里,看看他是否爱她。精灵古怪又可恶的周星驰。那么,我是否爱她呢?马义在深秋的傍晚像个花季少年般问自己。一股劲风沿着街面从西北角吹过来,把马义推得朝后仰了仰。后面一棵树上叫不出名字的黑鸟从马义头上呼啸着逃窜走了。风里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仿佛在泄露答案。爱,有时很简单,是或不是,无论真诚与否,无论是否在内心经过百回千转煎熬般的反复考虑,答上一声即可。有时却很复杂。想复杂了——马义喃喃自语,惊得路边踯躅独行的疯子朝这黑暗的角落里瞄了一下,然后被人追杀似地奔逃而去。世界有时候很简单,爱情更简单,人们只不过在自我折磨自作自受罢了,马义接着说。但这一切并不重要,至少从现在开始,它已经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