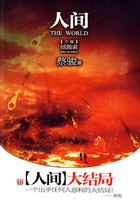人们最初都是心疼冬子,说你看着了吧,这才几年,冬子就成了“小白菜”了;说小翠娘也真是的,偏着自个的,苛对前窝的,这叫啥人啊!等有些人说够了,回过头来一琢磨,又觉着不对路子。小翠娘这两年渐渐地吃闲粮不管闲事了,这个家完全是鬼子一手遮天,这就不能再去怪人家小翠娘了。大伙便开始骂鬼子坏了良心,像陈世美,喜新厌旧,向着后窝的。骂来骂去,又有人想明白了,小翠前窝后窝都不是,小翠和鬼子没有啥血脉上的关系。于是,人们终于感觉到了,凭鬼子的为人,他这样疼小翠是不合情理的。
你千万别小看合庄的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民,他们的眼睛有时可是雪亮的。尽管他们可以拿一年的辛苦和小商贩子换一沓假钞,回来后还因买了个好价而津津乐道。但他们对于庄上的大事小事,尤其是男男女女的事,却出奇地敏感。他们能从蛛丝马迹中得到一些领悟,同时他们总是很急切地把所领悟到的东西,巧妙地传递给别人。看起来他们好像是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并带有一种使命感的。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或者坏事,但只要这事是发生在他们耳闻目睹的范围内,他们就有心思或责任去管。他们从心里没拿小翠当合庄人,但这事发生在这里,他们就有参与的理由。鬼子是合庄人,在他们看来,合庄人做了有背这里规则的事,丢的是整个合庄的脸面。他们没人肯或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又不愿意这公道被人践踏。说白了,他们是一群自己不愿意打架,又十分愿意看别人打架的人。
鬼子和小翠关系不正常这档子事,没几天的工夫,在合庄的绝大部分人中,早已是心知肚明了。剩下的那一小部分人,可能是韩奎一家和一群十几岁以下的孩子们了。
到了第二年的开春,小翠娘的精神头就更不足兴了。用鬼子的话说叫睡时睡得着,醒时睡不醒。找庄上的沈大夫,就是原来的“赤脚医生”看过几次,说是小脑开始萎缩了。吃了几付中药也不见好转,非但不见好,越治小脑越蔫巴得加速起来。
为了不影响小翠娘和冬子休息,鬼子提出把电视搬到西屋,也就是小翠住的那间房子里,这也算合情合理且两全其美的事。
消息刚刚从冬子嘴里吐出来,就像一般浓烟,立即弥漫整个合庄。这次传播,与上次传播明显不同。现在的这件事不是他们脑力劳动的结果,这就像领导讲话与传达领导讲话一样。领导讲话要讲求含蓄,传达领导讲话要讲求简洁。对于是事实的事,他们在叙述时开门见山,见面不用打招呼,也没有任何的铺垫,到最后扒皮去骨就剩下一句话了。那就是:你还不知道吧?鬼子搬到西屋去了。
这之后的一些议论,多半都是在庄西头大榆树下进行的。白天女人们凑在一起,她们认为,鬼子是通过小恩小惠的物质投资和旷日持久的感情渗透达到目的的;晚上男人们聚在一块,则不同意女人们的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鬼子是通过突然袭击完成后,才开始物质投资和感情渗透的。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没多大的区别,但合庄人硬是把它分析得关系到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从法律的角度讲,这涉及到通奸与强奸的性质界定;二是从道德角度上讲,小翠要是主动的,女儿抢母亲的饭碗,那小翠是不道德的。小翠要是被鬼子强迫的,鬼子一枪两鸟,放着碗里的不吃去祸害盆里的,那鬼子就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是缺德了;三是从时间角度讲,按女人们的说法,他俩住在一起只是今年的事情。按男人的说法,他俩住在一起那就是去年或更早的事情了。
就在合庄人背地里喳喳咕咕,议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鬼子放出风来,说冬子和小翠好上了;说冬子天天懒在小翠的屋里不出来;说他们之间或许都有啥事了;说他准备成全这两个孩子,想征求一下老邻旧居的意见。
大伙一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虽然他们不忍心看着狼吃小羊,但对于不是自己家的小羊,他们又不敢上前和狼博一场。他们只好点着头说,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娶媳妇打发闺女一事办,属于双喜临门。这回你可得好好地操办一下,到时候我们都来喝喜酒。鬼子听了,当然也兴奋。他给每位点上一支香烟,当即立断就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
冬子结婚那天,是农历的六月十五,天热,早上九点多钟,天就跟下了火似的。十点刚到,请来的厨师才生火,鬼子就站在门口等待宾客了。他还让韩奎的儿子准备一个喜礼薄和一个装钱用的匣子,摆放在门口一个显眼的地方。
这天的合庄,出奇的宁静。五十多户人家,除了韩奎一家四口忙里忙外,就是一群十岁以下的孩子在奔走相告。其余的人家,都掩起大门。
十一点,鬼子就开始站在当街放双响,叮叮当当地一圈双响下去了,他又开始放鞭炮,一会儿一挂,一会儿又一挂,断断续续地嘣到十二点多,也不见个人影。鬼子气得站在门口大骂一通,吓得连等着要糖的小孩子也跑光了。鬼子回屋一头扎到西屋炕上,连饭也没吃。准备的七八桌子酒席,两天之后,全部倒进泔水缸,心痛得冬子见人就说,把猪肉都喂猪了。
冬子的喜事就这样办了。合庄的人对于不能制止的事情,他们只能以特有的形式,表明他们的态度。
现在的小翠娘已经不比冬子强啥了。她一个人在家看家,从早上吃完饭,就拿个小板凳到杏树下坐着。看着老鹰在院子上空盘旋,她就抬头瞅着老鹰笑;老鹰俯冲下来了,她吓得用手捂上眼睛。等老鹰把小鸡叼走了,她又抬起头来瞅着天空笑。
鬼子白天领着冬子和小翠上山干活,晚上仍就在西屋炕上看电视。鬼子见了谁都不肯说话,昂着头走路。合庄的人倒像欠了他什么似的,只好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小翠每次走出院门,即便是大热天,头上也裹着一条方巾,银灰色的方巾掩去她的大半张脸。鬼子这个家,现在和外界唯一有交往的,就冬子一个人了。
冬子是不管这个那个的。他在家里呆不住,就往外跑,他爹越是不让他出来,他就越想出来,出来还就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凑合。
有一天晚上,大伙坐在大榆树下闲聊,冬子也晃晃悠悠地凑了过来。坚强和冬子同岁,他见冬子来了,就问他,说你昨晚上在哪屋住的?冬子低着头,说我不告诉你。坚强逗他,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从你媳妇屋住的呗。冬子听了就认真起来,说才不是呢,我和我娘在东屋来着。坚强又说,你爹也住东屋,你也住东屋,那东屋多挤呀?冬子抬起头,冲着坚强气冲冲地说,才不挤呢,我爹昨晚没住东屋。坚强追问道,说那不能吧?冬子听坚强不信他的话,就急了,他冲着坚强大声地嚷起来,说我起来尿尿,看我爹就没在东屋嘛。
大伙哈哈大笑,便七嘴八舌头地问冬子,说小翠是你媳妇,你咋不上你媳妇屋去住?冬子见大伙都在笑,他像捡着了多大的相应似的,也跟着高兴起来,边比划着边说,我媳妇不让我上西屋,我上西屋去拿糖,她拧我……
大家伙只管取笑了,竟没人注意鬼子的到来。鬼子上前就给手舞足蹈的冬子一个大耳光,那耳光打得像劈雷似的,大伙都吓了一跳。冬子一看是他爹,都没顾得哭,一只手捂着脸跑了。
冬子跑了,可鬼子没动。他站在那里破口大骂,骂冬子,顺稍也把在座的骂了。他还走到坚强跟前,指着坚强的鼻子发狠,说赶明个哪个王八犊子再敢瞎说八道,咱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大伙听着,谁都没敢搭茬,一个一个借着夜色偷摸地溜了。
从这天起,鬼子不再从家里看电视了。到了晚上,就出来溜达,哪里聚的人多,他就猫一样地凑过来,在人群的外围找个地方蹲下,听人们说话。
几天之后,人们再聚到大榆树下闲聊,坚强就不说话了。他在听别人说话时,眼睛盯着东头,见鬼子披着衣服过来了,他就小声地提示,说鬼子来了。
说话的人听说鬼子来了,不管正在说什么,都自然地停顿下来,抬头瞅一眼,等鬼子走到跟前,正赶上大伙都傻呼呼地坐着。
鬼子仍旧认为刚才大伙正在议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