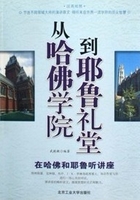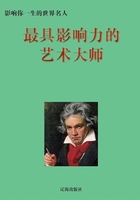房子的外观和别人家一样了,可里边还是做不了假,土坯墙上边无论如何抹不上水泥和白灰,只能抹黄泥。屋顶也没法吊棚,裸露着被炊烟薰得乌黑的檀木。
王勤家现在的新房子,虽说不是给王守金盖的,确实是因为李翠花才盖的。王勤家刚刚改装完房子,家里就上媒人了,给王守金介绍的这个对象就是李翠花。王守金订婚的第二年春天,王家张罗着结婚。媒人去说和几次,李翠花家不同意,问题就出在这房子上。李家说王家的砖瓦房是假冒违劣产品,说他们相门户那天上王勤的当了。这话是李翠花的父亲说的,他的原话是让王勤这个老鬼给唬弄了。
王守金的这桩婚事,是托媒人介绍的。按照这里婚姻的程序,媒人选定好男女双方人选后,第一步就是相人,即把男女双方叫到一起见个面。王守金和李翠花是在媒人家相看的,参加相人的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异议后,第二步就是相门户,也就是女方到男方家参观一下。相门户是在相人的当天进行的,李翠花一家从媒人家直接去王勤家。当时王勤说房门的钥匙让王守银带走了,王守银上山干活去了,一会就回来,让他们在当院等一会。李翠花一家只站在当院瞅一眼就走了,没上屋,他们认为房子的外观不错,屋里也指定错不了。等进行到第三步,也就是订婚时,李翠花一行人进屋后才发现端倪,但好像是晚了半拍,此刻这桩婚姻已进行到实质性操作阶段,王勤家的所有致近亲属都来了,老邻旧居也都到了,家里准备七八桌酒席,女方这时再提出疑议来,有些说不过去了。但这件事在李翠花全家人心里终究是个疙瘩,这个疙瘩一直结到现在。最后李翠花的父亲给个死话,说王家不盖新房,他们不嫁新娘。
媒人回来把话学说了一遍,王勤听后就翻脸了。他说我这也算是砖瓦房啊,墙上有砖,房上有瓦,他们还想咋地?他们也不看看自己家的闺女啥身份,我给她盖个金銮殿,她敢住吗?他们想拿结婚来要挟我,没门,不结就不结,不干拉倒。
王勤说这话时,媒人在场,王守金也在场。王守金瞅他爹一眼,啥也没说,转身走了。他到当院拿个尿桶放到西屋,盖上大被子睡起来,一直睡了两天两宿,叫他吃饭也不起来,问他咋地也不吱声,来尿了,他就下地撒尿,来屎了,他就蹲在尿桶上拉屎,整得屋里比厕所味还大。王守银和他睡在一个屋里,天天起早贪黑地给他倒尿桶。两天后,王勤一看实在是没治了,就咬咬牙,瞪瞪眼,摔了一个茶杯,挥了挥手说,马上盖房子。
王勤家现在的这三间正房,是在老房子地基上翻盖的,纯正的砖瓦结构,铝合金门窗。房门开在中间的屋子上,东西两屋的前面是窗户。进门之后,左右各有一个通往东西屋的门,是用上好的红松打做的,只刷两遍亮油,保留着木头的本色。迎面是一个铝合金隔断,上面镶着花玻璃。打开隔断上的推拉门,里面是厨房。东西两屋的格局和布置几乎一模一样,沿着后墙各搭一埔两米宽的大炕。东西两个锅台的烟道,穿墙而过,在大炕里七扭八拐之后,再从东西墙的烟筒里排出房顶。室内的装修在合庄这一带也算考究,房顶吊得是石膏板的棚,地上镶着乳白色地板砖,顶棚和墙壁都刮着仿瓷,炕上铺的是安舒地板革,屋里还安装着吊扇,管灯和土暖气。
新房峻工,李翠花跟着就过门了。西屋做王守金他们的洞房,王守银自然跟着父母住在东屋了。这样,东屋老俩口子,西屋小俩口子,晚上睡觉时,难免会搞出一些让王守银听得兴奋的动静。每次王守银听完这种声音后,他都起来,到外屋过道上的尿桶里撒尿。王守银个子高,有一米七八左右,撒尿时比别人落差大,撒尿的声音就相对响亮,好像要把那个塑料尿桶戳穿一样。王守银撒完尿后,躺在炕稍翻身打滚地叹气,半宿半夜地不睡觉。王勤觉察到了,他认为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又找来瓦工,在东屋的三分之一处竖起一道墙,这样原来的东屋就变成了一大一小的两间小屋。那间小屋的门开到厨房里,王守银有他自己的单间。
去年年底,王守银也要结婚了。王勤是这样打算的,还是用西屋做王守银的洞房,王守金一家三口搬到东屋去住,他们老两口子住原来王守银住的那间小屋。
方案确定后,李翠花一听就恼了,当天就抱着儿子胖胖回了娘家。不过两天就托人捎来话,说如果王勤不能给她一个满意的说法,她就不跟王守金过了。
自从媳妇回了娘家,王守金也在家里积极配合。他不去砖厂上班了,整天就躺在西屋炕上看电视。娘把饭做好后,他不起来吃,王守银招呼他起来吃饭,他瞪王守银。王勤两口子招呼他起来吃饭,他假装睡着了。没办法,王守银只好把饭盛好,送到西屋。王守金趴在被窝里吃饭,吃完后,把碗筷往炕稍一推,接着睡。只是这次他不在屋里拉屎和撒尿了。
几天之后,王勤再次缴械,他打发王守金去接媳妇,并送去他的承诺,说这只是暂时的,等王守银结婚后,缓个一年半载的,家里攒了钱,再批一处房基地,再盖三间新房子,让他们两口子搬出去住。这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王守银的这个媳妇,是他老姑托媒人给介绍的,是离合庄5里外的东官村的,原来在省城的一家酒店打工。这姑娘,论模样,论说话办事,比王守金的媳妇强得多。人家对房子没有过份的要求,说有个能住的地方就行。这让王勤感觉很是欣慰,好像是捡多大便宜似的。因此,在给二儿媳妇买衣服上,也显得比王守金结婚那会儿大方很多。
王守银结婚后,乐得王勤老婆天天上当街去站着,看见有人过来,就过去主动跟人家搭话。人家问她忙吗?她说家里的那点活计,两房媳妇背着手就能干完,连一根草刺都不用她捡。人家问她二儿媳妇咋样?她不答,只是说娶二儿媳妇比娶大儿媳妇多花一千多块。于是,听的人就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小儿媳妇要比那个大儿媳妇强一千倍啊。
王守银是腊月中旬结的婚,刚过正月十五,他媳妇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回了娘家。第二天便让媒人捎来口信,提出离婚,所持的理由是王守银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媒人先把消息送到王守银老姑的耳朵里。王守银的老姑听后,当时就从炕上跳到了地下。她说我侄子五大三粗的,要说挣钱没多大能耐,这我信;要说这方面不行,那不可能。我侄子小的时候,小鸡子就比别人的大,一有了尿,就硬梆梆的,原来我还担心他们闺女消受不了呢?
当天,王守银的老姑就跑去女方家里去质问,说这可是关系到一个男人尊严的事,没有根据可不能瞎说。女方的母亲说,这事你不用来问我们,你回去问你的侄子不就得了,你们孩子啥样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孩子可跟他遭不起这份洋罪了。
王守银的老姑一想也是这么个理,这事除了当事人之外,别人谁也说不清楚。她立即掉头跑回娘家,到家时都是掌灯时分了。
吃过晚饭,全家人坐在西屋炕上开会。王勤坐在炕头上,依次是王勤老婆,老姑和王守金。李翠花抱着孩子在地下站了一会,被王守金撵回东屋睡觉去了。王守银坐在地下的折叠椅上,那阵式,跟戏台上三堂会审似的。
王勤问儿子身体倒底能不能行?王守银说他能行。王守金说你搁进去过吗?王守银说搁进去过。王勤老婆问儿子能挺多长时间?王守银说不一定,有时候能挺一会,有时候一动弹就出来了。老姑问侄子从结婚后一直这样吗?王守银说是,但一宿要玩两回时,第二回时间就长点。
事情问清楚之后,第二天早上,王守银的老姑便返回到东官村去劝合。她说王守银那玩艺也能站起来,也能搁进去,时间短点这不算毛病,这种事情国家也没有规定多长时间算是合适。女方的母亲说,那也总不能每次都和放爆竹似的,砰的一下就完事吧。王守银的老姑说,那你还想要多长时间?女方的母亲急了,说没有你这样说话的,还问我想要多长时间,我想要多长时间那是我老头的活计,关你们个屁事、就冲你这句话,我家闺女就不跟你侄子过了。
事情搁置半个月,王守银媳妇又回省城那个酒店打工去了。王守银的老姑找乡里的司法助理咨询,司法助理说,这种情况,只要是女方提出来了,离婚就是合理的。王守银的老姑问司法助理,男的插多长时间合适?司法助理笑了,他说女方认为多长时间合适就合适了。王守银的老姑说,那她要是总认为不合适呢?司法助理摊了一下手,说她要那么说也没办法。
后来媒人出面调停,双方答成共识,王勤家做了让步,同意离婚,让女方把男方给她置买的衣物等项带走,但女方必须在对外说法上,不提离婚的真正原因,为王守银保持这个密秘。女方家也表示同意,尽管毛病不出在他们闺女身上,但真正说出去离婚的原因,他们也觉得好说不好听。最后双方定下攻守同盟,一口咬定两人离婚是因为性格不适合。
王守银离婚后,这个家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王守金一家三口人又搬回西屋,王勤两口子也住回到东屋,王守银搬着他的那套新行李,又住回后小屋去了。可以说,王守银结一回婚,除了落下两套新衣服外,就是换了一套新行李。他结婚时的家俱啥的,也都归王守金使用着。王守金原来的家俱,王勤两口子用着。
王守金搬回西屋那天,李翠花的脸上喜气洋洋的,跟又结了一次婚似的,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吃过晚饭,两口子连电视都没看,早早地就关灯睡觉了。
早上起来,王守银洗过脸后,他仍旧去了西屋,站在那面原来属于他的穿衣镜前,用她媳妇留下的那把桃木梳子,没完没了地笼着头皮。相对比身材,王守银脑袋显得很小,又呈枣核形状,不合适留长发。王守银每个月都要到镇上去剪头,把头发剪得紧贴着头皮,跟秋后田野里割过的庄稼茬子似的,梳子从头皮上滑过,就像秋风横扫秋后的大地,畅通无阻。
李翠花洗完脸,站在王守银的身后,一边擦着脸,一边很不耐烦地说,去去去,一个大老爷们,没事上镜子跟前瞎照啥,再照,能把媳妇照回来是咋地?
王守银听了嫂子的话,他把梳子放下,但人并没离开。他用手来回地扑打着头上的皮屑,不紧不慢地说,离了更好,离了咱再说个新的,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说完他转过身来,冲着李翠花笑了一下,说嫂子,这屋子和这屋里的东西,可都是我的。你可得给我照看好了,以后我再结婚时,还用呢?
李翠花听完王守银的话,很气愤,脸胀得通红,但又不好说啥。因为王守银的话不无道理。她白愣王守银一眼,拿起梳子,啪地一下扔在脸盆里,又从抽屉里找出个刷子来,开始刷王守银用过的梳子。
从这天开始,王守银有事没事都好去西屋转转,有时候进屋打个照就走了,有时候依靠在西屋炕梢被垛上看会儿电视。他还用原来属于他的脸盆洗脸洗头,甚至把他不穿的脏衣服,还放到他原来的大衣柜里。
王守银每天在西屋出出进进的,让李翠花觉得心里很憋闷。王守金也觉得很不自在。两口子没地方出气,就轮班着打孩子,虽然不是真打,但胖胖每天总是哭咧咧的。王守银看得出哥哥嫂子的意思,但他们越是这样,王守银出入得越发频繁了。
一段时间后,李翠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她每次给孩子喂奶时,王守银就赶紧出去了。这一发现,李翠花就像掌握了原子弹似的,她看到王守银进屋,就拽过胖胖来喂奶。胖胖不吃,她也撩开衣襟,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吓得王守银低着头就退出来了。李翠花这一举动,虽然缩短王守银在西屋逗留的时间,并没能减少王守银去西屋的次数,赶上李翠花不在屋时,或者胖胖不在屋时,王守银还是要在西屋坐一会。
到了秋天,家里卖完粮食,王守金也从砖厂把工资开出来,王守银也从建筑工地上把工钱算回来了。这样,王勤的手里又有三万多块钱了。他开始四处托媒人给王守银说媳妇。
这天,庄子东头老刘家的驴下驹时憋死了,大伙都买驴肉,王勤也买回几斤来,晚饭吃的是驴肉馅的饺子。王勤和他老婆并座在炕头上,王守金和王守银坐在桌子的对面,炕里是王守金三岁的儿子胖胖,自己占去方桌的一面,李翠花站在炕沿边上,自己也占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