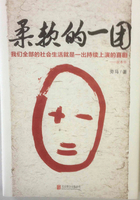虽然土改没受到打击,但秧子安逸的生活被破坏了。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参加到合作社的劳作之中。他打小没干过农活,甚至连锄头犁杖都不会用。合庄人虽然看不起不会种地的庄稼人,动辄就拿他说事,把他当成好吃懒做的反面教材。但他们并不歧视他,不欺负他。人们认为秧子所以这样,错不在他,也不在于他爹,而在于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人们坐下来研究一番,决定让秧子当饲养员兼看青的,也就是每天上山放牲口时,顺便看护着地里的庄稼。这时秧子的二儿子已经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个吃饭的,他感觉到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工作起来还是挺卖力气的。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秧子已经是老饲养员了。他每天住在生产队里,喂养那些骡马并负责看护着队上的仓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是生产队的核心人物了。生产队班子开会,他都能列席参加了。
在秧子得三儿子那年冬天的一个后半夜,他起来给牲口填草,刚来到当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后边嗖嗖地冒凉气,身上的汗毛孔都张开了。他以往晚上起来,都提着一盏灯笼,这天是大月亮地,便空着手出来了。他蹲在屋檐下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便感觉到粮仓后面有动静。他摄手摄脚地走过去,看见两个人影在粮仓后面。
秧子躲在暗处看着,见两个小偷在土墙上打了个碗口粗细的洞,把一根铁烟筒斜着插进去,这样粮食就顺着烟筒自然地流出来了,流进下边放着的口袋里。看明白这一切后,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两个小偷。可佩服归佩服,他是看粮仓的,他不能坐视不管。明天保管发现粮食少了,第一个摊责任的是他。
秧子眼看着两个小偷的口袋要接满了,他在心里着急,但又不敢轻易地出手。他知道凭他的体格,一个小偷都对付不了,别说是两个了。他在围前左右寻找了一下,地上连块石头都没有,他又摸摸身上,除了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和一个烟口袋,再也没啥可手的家伙了。眼看着两个小偷要走了,他恨不得自己手里有一颗枪。他想着想着,手自然地向腰里够去,把烟袋摸出来了。
秧子的这个烟袋是他爷爷留下来的,他爹不抽烟,自然就归他了。烟口袋是他结婚那会儿他老婆给他做的。原本是白茬皮的,因为用得时间长了,磨得黑不溜秋的了。烟口袋的在开口处,用一条丝绳穿着,绳子上面系着蛋黄大小的一个玉石,据说这块玉是他老婆家传下来的。合庄人管这这东西叫烟荷包挡头,不用烟口袋的时候,就把那块玉石掖在裤腰带上,有它挡着,烟口袋不置于掉下来。玉石的下边飘散着一绺红缨子,也是用丝线做成的,跟烟口袋的长度差不多。秧子每天把烟口袋挂在烟袋上,只要是穿上裤子,这套家伙式就一直地在他身上。
秧子摸到“枪”后,胆量自然大了些,他摄手摄脚地走到两个小偷身后,用烟袋顶在其中一个小偷的腰眼上,他突然大喊一声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那小偷觉得身后硬梆梆的,也就真不敢动了,并学着电影里坏人的样子,把两只手自动地举起来。另一个小偷听到喊声,回头扫了一眼,他看不到秧子手里拿着啥,只看到下边飘荡的红缨。那时很多有手枪的人,都爱在枪把上拴上红布一类的装饰物。这个小偷也以为是手枪,当时吓得不行,也赶紧举起手来。秧子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个听我的口令,谁敢乱动一下,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睛。听到了吗?秧子这一诈唬,吓得两个小偷连连求绕,说听到了,我们不乱动,你可千万别开枪啊,我们犯的不是死罪,就偷点粮食,这也是饿得没法子。
秧子押着两个小偷来到生产队当院的大钟下,这期间,他的烟袋始终没离开 过那个矮个子小偷的腰眼。他让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小偷敲钟,高个子有些犹豫,他就用烟袋使劲地碓这个矮个子,他对高个子说,你不敲,我就打死他。吓得矮个子带着哭腔对高个子说,姐夫,你就敲吧,他让你咋着你就咋着吧,不然我们俩都没命了。秧子从矮个子的话里听出来了,原来他们是姐夫和小舅子关系,他心里更有底了,这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只要看住眼前这个不跑,那个就跑不了。那个高个子拿起插在钟上的一根铁棍,当当地敲起来。雄浑的钟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显得有些突兀刺耳。
几分钟后,各家的灯光便渐次地亮起来,之后便是开大门的声音和奔跑的脚步声,人们都以为是来了啥最高指示。生产队长王俭披着棉袄跑在最前头,他边跑边系扣子。他棉袄上钉的是那种用布条自己打制的纽扣,就是我们看过的唐装上的那种。他从村东头跑到生产队部,只扣上4个,其中有三个还扣错位置了,衣服的下襟变得一长一短的,前胸鼓起个大包,和女人的奶子似的。
大伙来到生产队的院里,见当院的大柳树下,一溜地站着三个人,前边的高个子拿着铁棍,还在不停地敲打着,只是手抖得厉害,半天一下,有气无力的样子。高个子后边的矮个子,双手抱着脑袋,一副俘虏模样。秧子站在最后,抬着胳膊,还在用烟袋顶着矮个子。人们不知道情况,纷纷地围上来,把三个人围在当中。王俭围着三个人转了一圈,他问秧子咋回事?秧子说抓住两个小偷。王俭让大伙把小偷按住,找来绳子捆上,秧子才把顶在那人腰上的烟袋拿下来。
秧子来到两个小偷的正面,他抬眼看了看他们,并把手里的烟袋举了举,嘿嘿地笑了几声,说看见了吧,这是烟枪。说着就赶紧往人群外挤,边挤边脱裤子,他刚挤出人圈,就哗哗地尿起来。他边尿边嚷,说你们再不来,我就尿裤子了。等他尿完后,总感觉不对,刚才觉得憋得难受,咋就这点尿啊?他用手往棉裤里摸了摸,里边已经有一片地方湿了。他没敢嚷嚷,转身回到人圈里,他朝那个高上子小偷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说你他妈的,竟给老子找麻烦。
秧子智擒两个小偷的事,第二天便经生产队传到大队和公社,并受到了极大重视。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专程来到合庄,给秧子开现场表彰大会,公社书记亲自给秧子披红戴花,号召全体社员向他学习。可大会刚开到一半,就听人群里有人呜呜地哭起来,大伙一看,却是秧子的老婆。公书记很不解,说你男人为人民立了大功,你应该高兴才是,这咋还哭上了呢?秧子老婆来到书记跟前,她说秧子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惹了麻烦,那两个小偷就偷点粮食,肯定判不了死刑,过几天就得放出来,这样我们家孩子大人都不安全了,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咋过啊?她说着竟然坐到地上了,拍着大腿放声地嚎起来,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
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一听,觉得秧子老婆说得有道理。怎么能让英雄和家属天天心里不安呢?他们经过简单的商议,决定让秧子去大队当民兵连长,发给他一支真枪,允许他晚上背到家里来。公社书记对秧子老婆说,他拿着烟袋都不怕那两个小偷,这回有了真枪,你应该放心了吧?秧子老婆破啼为笑,说这回放心了。大伙也为这事高兴,纷纷过来祝贺,说秧子是鸟枪换炮了。
秧子的民兵连长一直当到分田到户,大队改成村委会后,不设专职的民兵连长了,秧子又回家重新当了农民。这期间秧子家发生些变故,马玉柱两口子前后脚去逝了;秧子的大儿子结婚了,没用服药,很顺利地生个儿子,秧子愉快地当上爷爷了。
由于秧子打小就没干过农活,再加上当这么多年的民兵连长,更加不会干活了。他每天就背着手在当街闲逛,顶多是抱着孙子闲逛。这样他大儿媳妇就有意见了,天天跟她男人生气。秧子看不过眼,想把大儿子分出去。可儿子分家得有地方住啊,秧子便给大儿子盖了三间房子。
大儿子的事算是摆平了,家里攒的几个钱也花光了。眼前还有二儿子该说媳妇,还有小儿子在高中念书。他的小儿子非常用功,不但学校的功课及时完成,还利用课余时间,把秧子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也都学完了。他比秧子学得还好,有时候秧子看不懂的地方,还得去问他。老师说这个县要是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秧子感觉到生活上的压力,天天吃不好睡不着的。有一天,邻居家儿子结婚,他给人家写完礼帐,多喝了几杯酒。回来后,他站在当院里大喊,让他老婆摆上香案,他从柜里把他爹当年得到的两个方子拿出,放到香案上,他率领着全家老少跪在案前,冲着香案磕过三个头后,他大声地宣布,说不知姓名的干爷爷,孙子对不住你了。我打算用你的这两个方子,去改变我家的生活,虽然这有背你老人家的愿望,可也算是济世救人的事,希望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
秧子包下原来村上的卫生所。把名字改成马氏诊所。在牌匾的下边,特意写上一行小字:祖传秘方,包治男女不孕不育症。因为合庄的人都听说过马玉柱当年的事,对他家有秘方的说法毫不怀疑。谁家亲戚朋友有这种毛病,他们都在义务地给秧子宣传着。这样,没用几个月,秧子的诊所就远近闻名了。
秧子不看病,他只卖药。来了病人,他让病人自己去镇上的医院做化验,确定好是男人有病还是女人有病,第二天让人家来取药。他把熬好的中药放在瓶子里,把剩下的药碴子倒进猪圈。抓药的话他亲自去做,熬药的活让他二儿子去做。他的药价很高,每人收费三千元,不过有一点还算公平合理,半年后不怀孕的,退还二千五,那五百块钱算是药的成本。从打开业后,只有一个人来找他退款,那人的媳妇吃了他的药,还没等怀孕就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秧子听完那个人的遭遇,竟然全额退还了人家,这在当时当地也成为一个美谈,人们都说他到底是个读过书的人,为人做事就是仁义,所以来找他看病的人,都一个百放心,他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起来。
几年之后,马氏诊所根据发展的需要,搬到黑龙镇上去了,还自己添置了化验设备。不过自打搬到镇上后,诊所就由他二儿子打理了。秧子只需要戴上老花镜,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本有关医药方面的书,坐在那里充个样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