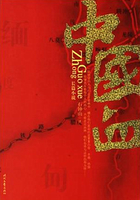爷爷和父亲面朝院子坐着。大雨一直在下,似乎天刚好在我们头顶漏了,雨点直奔而下,雨点落在屋后的枇杷树上,落在屋顶的成千上万瓦片上,落在院子的草地上,不同的声响混杂在一起,交织成无边无际灰蒙蒙的大网。渐渐的,院中露出了闪耀着淡淡光彩的杏树梢头,满院浑浊的雨水打着旋儿,急急朝出水口涌去。又白又大的雨点从黑暗中剥离出来,砸进水面,发出噗噗的声音。沉默像雨声一样把爷爷和父亲之间的距离填充得严严实实。父亲抽出一根春城牌香烟,递给爷爷,爷爷挡开了,父亲尴尬地咳了一声,自己点了烟。爷爷仔细往烟斗里压了一锅烟丝,父亲慌忙掏出火柴。爷爷咬着烟斗,让父亲替自己点燃了。爷爷和父亲各自抽着烟,还是不说话,雨水持续着,两个红红的烟头静静地一亮一暗,好似时间的正面和反面。我等不及了,刚张开嘴,父亲就狠狠瞪了我一眼,刚到喉咙的话又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这雨下了一夜,山上怕滑坡了。”父亲清清喉咙说。
爷爷不说话,眼睛眨了眨,望着雨水,又好像什么也没看。
雨似乎小了,但更持久。雨珠砸在水面,溅起一朵朵小水花,水花漂一段才破,溅开细小的水珠,使水面浮着淡淡的雾气。屋后的竹林里传来一声声翠绿的鸟啼,天色不早了。我急得心头起火,又不敢声张,只不断去看爷爷。爷爷紧紧抿着嘴巴,双目炯炯,脸色铁青,从没这么严肃过。
“爹,你瞧瞧院里那么多草,等雨晴了,太阳一晒……”父亲小心翼翼说。
爷爷脸色越发难看了,嘴巴也抿得越发紧。
“爹,做儿子的本不该说,只是……”父亲犹豫着,深吸一口烟,长长地吐出来,浓白的烟迟滞地扩散开,遮住了他的脸,“还是直说吧。马死了多少年了,你年纪也大了,还和以前一样,天天到山里头割草,割回草扔给猪猪不吃,放在院子里,又是雨又是晴,外面来个人,哪个不是捏着鼻子……”
父亲声调渐高,脸红成一只大虾。我可怜巴巴地望着爷爷,爷爷脸绷得紧紧的,光秃秃的额头布满皱纹,头顶却异常光滑,泛着淡淡的雨水的光芒,抿得紧紧的嘴巴下面,翘着几根灰白干枯的胡须,胡须微微颤抖着。
父亲忽然闭了嘴,紧张地凝视着爷爷。爷爷纹丝不动,仿佛一座大理石雕塑。我轻轻地摇了摇爷爷的手,感到那只大手软弱无力,如一只抽了丝褪了壳的丝瓜瓤,我心里酸溜溜的,低低喊了一声。
“爷爷!”
“嗯?”
爷爷猛然醒过来,迷惘地望着我,顺手拿起烟斗,塞进嘴里,吧吧抽了两口,一点火星儿不见,烟斗早哑巴了。
大雨接连下了半个来月。每天早上,爷爷坐在房门前,曲着腰,似一只衰老的猫或者狗,一动不动地瞅着漫天雨水。雨过天晴后,院子里的茅草彻底腐烂,沤成了粪,发出热烘烘的臭气,紫黑的污水流了一地,污水一落,草根噌噌噌往上抽芽,不几天,院子铺了厚厚一层绿色。爷爷眼见铁锈似的绿色占领了院子的一个个角落,石头一般缄口不言。
爷爷还是每天一大早起,在门前枯坐。有一天,听到他走出家门,以为他又上山割草了,快吃早饭时,他回来了,手里捏了一把干草。
天晴后那一个来月,爷爷过得极其痛苦,就如解了鞍鞯、离了沙场的战马,在逼仄的马棚里待不安生。
一天傍晚,太阳还未落到大山背面,瓦楞上的热气还未消散,爷爷匆匆从外面走回来,红光满面,脚步轻悄,手里没有草。爷爷直奔柴楼,蹬蹬蹬爬上去,在柴草堆里翻出一把斧子,三两下抹掉木柄的灰尘,扛红旗一样扛下来。
面对手握斧子的爷爷,父亲半天说不上话。
“你们说我割草没用,我上山挖松根!回来晒干了,能当柴烧吧?”爷爷赌气似的说。太阳落着,夕光照得他脸色辉煌,如镀了金的铁板。
我如今记不清和爷爷一起走过多少山林,涉过多少河流,挖回过多少松根了。现在村里的老人见到我,有时还会说,这才一晃眼,昨天还让你爷爷担你,今天就成大人了。爷爷很快回复了上山割草的生活节奏,一部老朽的机器歇了几天工,重新上油后,运转得更欢更快。
走得最远的一次,到了老鹰山的背面。
那天我们起身很早,出了家门,拐上村外的滚石河,一个人没碰到。滚石河两边堤岸很高,很窄,是灰白的砂石路。路边立着两排羊草果树,笔直细高的树干顶着一大蓬叶子,投下大团大团模糊的影子,蹲伏着的野兽一般。我走了没几步,脚一翘一翘的,又连连打了几个小呵欠。我感到爷爷无声地笑了笑。
“小光,上来!”
爷爷放下扁担,把扁担上的绳子顺开。我揉揉惺忪的眼睛,手背沾了泪水,咧开嘴笑了。我走进竹筐,盘腿坐下,两只手分别抓住两根麻绳。爷爷把斧子搁在另一边的竹筐里,站在两个竹筐当中靠我这边,我听到爷爷轻轻哼了一声,扁担发出轻微的嘎吱声,麻绳猛然绷紧了,我的屁股悠悠地离了地面。爷爷挪了挪扁担的位置,好让挑子保持平衡,然后,扁担唱歌似的嘎吱嘎吱着,我稳稳当当坐在竹筐里往前走了。
“重不重?”我扭过头望着爷爷。
“不重。”
爷爷一只手搭在扁担上,一只手拽住我这边的麻绳,均匀地迈着大步,鞋底擦擦擦摩擦着路面的鹅卵石,裤管碰撞着路边的野草,噼啪噼啪响。我身子底下即是河边的慢坡,坡上野草蓬勃生长,顶端的花穗不时扦进竹筐缝隙里,被竹筐碰断,散发微涩微苦的清香。我不时伸出手去,拽一两朵野花,举得高高的让爷爷看,爷爷乜一眼,嘴里含含糊糊地唔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