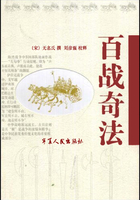约莫十多年前,从我家门口往西,拐过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过了岔路口,再顺河岸往南走两公里不到,就是天和镇的街市了。临街的河面,一溜木板房还未拆除。几根发黑的圆木插入河水,矮墩墩的房子蹲在上面。人走进去,整座房子趔趄着,地板嘎吱嘎吱响,透过木板间宽大的罅隙可以看见黄褐色的河水慢吞吞地流过。河面漂浮着各种垃圾,暗绿色的腥臭气味一蓬一蓬浮上来。夏天的时候,热烘烘的臭气熏得人简直睁不开眼。车云飞却格外喜欢木板房里的夏天。母亲和“外方人”跑后,父亲又到外地打工了,他只好暂住舅舅家的小店。他想钓鱼,舅舅又不允许他到河边,舅舅到店前应对客人时,他便紧紧缠住钓鱼线,将钓钩小心翼翼穿过地板的缝隙,一直探到水里,然后,脸贴地板,全神贯注盯着漂杆,呼呼喘着气。
木板上细微的灰尘腾起,搅进一道道金色光柱。不一会儿,靠近他脑袋的地板纤尘不染,还带着一点儿潮气。只要前面有什么异常响动,他立刻扬起脑袋,支起耳朵,瞅着将木板房隔成前后两部分的那道门。暗沉沉的门纹丝不动。舅舅从没发现他这小小的快乐。不过,他也从没钓到过什么活着的猎物。他钓到过一只黄胶鞋,他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扔回水里了。第二次,他又吊起一只小铁桶,桶里灌了半桶沙子,他费尽周折,也没能让铁桶穿过地板的缝隙。再后来,他又钓到一样古怪的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皱着眉,将它拉上来。泥水淋淋漓漓落向河面,激起轻微的水声。他偷偷把那东西洗干净——两个暗红色的圆形垫子连着几条暗红色的带子。他仍然不明白那是什么。因此,他感到几分兴奋。一天中午,他忍不住把他的猎物带到店铺外面玩。
“小云飞,你过来!”他忽然听到一个低低的怒气冲冲的声音。
他看到舅舅站在柜台后面,阴着一张脸,目光从粗黑的眉毛下射向他。他心里咯噔一下,茫然地望着舅舅。舅舅盯着他,目光凝聚着。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猎物藏在身后,忐忑不安地朝舅舅走过去。
“你手里拿着什么?”
“没有……”
“手伸出来!”舅舅的目光冷冷的,手术刀一样切进他的身体。
他扭着身子,手里揉搓着自己的猎物。马路上传来赶集的人纷乱的讨价还价声。汽车拼命按响喇叭,催赶挡路的人。他怯怯地伸出手。舅舅扫了一眼,脸上黑压压浮了一片乌云。
“杨贵芳!出来瞧瞧你的好侄子!”舅舅冲着隔门吼了一声。
车云飞吓得心惊肉跳。姑妈推开隔门走出来,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问舅舅怎么回事,舅舅气呼呼地朝他手上睇了一眼,姑妈一看,脸刷地红到了耳根。
“你也不放放好!”
姑妈又看了看他手上的东西。
“不是我的。”姑妈说,脸红得像一张透明的红纸。
“不是你的是哪个的?难不成是我的?”舅舅没好气地说。
“你这个人才怪了!”姑妈也没好气地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有这样颜色的?”姑妈的脸变成了猪肝色,一扭头回里屋了。门在她身后发出巨大的声响。
舅舅瞪着隔门骂了一句粗话。
舅舅问不出那东西从哪来的,把它扔进河里了。车云飞坐在小凳子上,脸对着人来人往的街道,目光偷偷向下撇,注视着河里那刚还在他手里的猎物。那东西掉进水里,并不落下,而是浮在水面,随着水流缓缓飘动,遇到阻碍,又停下来,迟迟不动,待阻拦的东西给水流带下去了,又继续往前漂浮。一团暗红色在暗褐色的木头地板之间闪现。车云飞看得眼睛发酸。不多时,那东西消失在屋脚的木板处,仿佛给一刀切断了。那片红色在他的眼帘里,又存在了一会儿,也消失了。他呆呆坐着,回味着那一点儿温热的红色。
“出了什么事?”柜台后面,舅舅的声音吓了车云飞一跳,他刚刚苏醒过来似的,迷迷瞪瞪地望向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