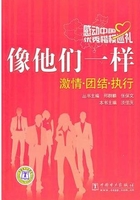致韩菁清
昨天睡得时间不久,但是很甜。我从来没戴过指环(注:指环。即戒指。 韩菁清把祖传的戒指送给他),现在觉得手指上添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一个大负担,是一种束缚,但是使得我安全地睡了一大觉。小儿睡在母亲的怀里, 是一幅纯洁而幸福的图画,我昨晚有类似的感觉。“像是真的一样”(注: 这是韩菁清常爱说的话)。手表夜里可以发光(注:这是韩菁清送他的表), 实在是好,我特别珍视它。因为你告诉我曾经戴过它。我也特别羡慕它,嫉 妒它,因为它曾亲近过你的肤泽。我昨天太兴奋,所以在国宾(注:饭店的名称)饮咖啡就突然头昏;这是我没有过的经验,我无法形容我的感受。凤凰引火自焚,然后有一个新生。我也是自己捡起柴木,煽动火焰,开始焚烧我自己,但愿我能把以往烧成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即是你所谓的“自讨苦吃”。我看“苦”是吃定了。
你给我煮的水饺、鸡汤,乃是我在你的房里第一次的享受,尤其是那一瓶 ROYALSALUTE(注:据韩菁清说,那是苏格兰的一种名贵威士忌),若不是有第三者在场(注:指佣人,每天来韩寓服务一、两小时),我将不准你使那两只漂亮的酒杯——一只就足够了。你喝酒之后脸上有一点红,我脸上 虽然没有红,心里像火烧一样。以后我们在单独的时候,或在众多人群中, 我们绝不饮酒,亲亲,记住我的话。只有在我们两人相对的时候,可以共饮 一杯。这是我的恳求,务必答应我。我暂时离开的期间,我要在那酒瓶上加 一封条。
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注:指一个月后他要离开台北),上天不仁,残酷乃尔! 我今天提早睡午觉,以便及时飞到你的身边,同时不因牺牲午觉而受你的呵斥(注:恋爱期间梁实秋常常不睡午觉在韩菁清楼前“仰望”、等候,因而韩菁清“呵斥”他要保重身体)。
亲亲,我可爱的孩子!
梁实秋
63.12.早晨 6 时
(注:“63”,即 1974 年。)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1903—1987),散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名人婚恋
梁实秋与韩菁清
1974年12月27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聚会上,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梁实秋与韩菁清相遇了。对于美丽大方的韩菁清,梁实秋一见倾心。
在以后的几天里,梁实秋每天上午都到台北忠孝东路韩菁清的公寓下守候,等到韩菁清一起床,他就登楼入室。晚上,他们或者一同应邀参加各种应酬。韩菁清很快觉察到“梁教授”爱上了自己。然而韩此时仅43岁,梁韩相差近30岁,这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在一次闲谈中,韩若无其事地向梁表示,她愿替他做红娘,不料梁实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喜欢的就是红娘。
梁实秋之所以在晚年爱上韩菁清,不仅仅是因为老伴去世后晚景凄凉,也不仅仅因为韩菁清年轻俏丽,而是在于跟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韩菁清家境良好,早年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她熟谙古文,懂英文,善书法绘画。
在天天见面的情况下,仅仅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梁实秋就给韩菁清写了三十多封情书。梁实秋身体不好,多年来习惯于早睡早起,而韩菁清晚上的应酬很多,常常和朋友们在外边吃宵夜。梁实秋告诉韩菁清,他将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以把他们两人的作息时间慢慢地拉近。此后,如有可能,他就坚持陪着韩菁清一起吃宵夜,陪她去上课。恋爱使梁实秋焕发了青春,他脱下了长年穿惯了的灰色西服和深色领带,换上新西装,系上新领带。爱情使他充满了快乐。
转眼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梁实秋为处理前妻程季淑的非正常死亡,必须回美国去打官司。1975年1月10日,梁实秋飞离台北,为了保密,韩菁清没有去机场送行。
梁实秋和韩菁清在台北出双入对,进出饭店,早已为朋友圈中所瞩目,也引起了一些记者的注意。韩菁清曾送给梁实秋一枚碧玉戒指,梁实秋十分喜爱地戴在手上。这天,朋友们正在候机大厅围着梁实秋告别的时候,一位朋友忽然发现了他手指上的戒指,便问:“谁送的呀?”大约是太高兴了,梁实秋说走了嘴:“韩小姐送的!”
梁韩相恋的消息,从二人的朋友圈中逐步地传播开去,终于让记者在报纸上捅了出去。一时间,梁韩之恋成了“倾城之恋”,在台岛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这一“非常时期”里,梁韩二人书信频频,往返数十封,相互安慰着,共同迎接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这场战斗。
梁实秋在一封信中表示:“你在我的心中占据最崇高的地位……。如今有人侵犯你,那即是侵犯我。”最后,他又一再叮咛:“海枯石烂,你是我的爱人,我是你的爱人,我们两颗心永久永久凝结在一起。别人挑拨,别人诬蔑,没有用。”
就在梁韩相恋的风波历久不息之际,梁实秋终于处理好在美国的事务,于3月29日悄然飞回台北。在一片夜色中,韩菁清在台北松山机场迎来了自己心爱的“教授”。5月9日,是台湾的“母亲节”,成了梁韩结合的日子。台湾三家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都插播了梁实秋韩菁清婚礼实况,台、港数十家报纸刊登了新闻报导,有好几家报纸以整版篇幅刊登婚礼照片,又一次引起轰动。
出乎人们的预料,梁实秋所有的朋友都承认,他再婚以后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刘绍唐说梁实秋在婚后“半天写作,半天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1984年10月,梁实秋趁韩菁清去香港小住、他独自在家之机,写下了遗嘱。在预备专给韩菁清留下的遗言里,他说:“我首先告诉你,自从十年前在华美一晤我就爱你,到如今进入第十个年头,我依然爱你……”
1987年10月,梁实秋译完了平生最后一部译著——《生死边缘》。11月1日下午,还接待了两对来访的夫妇的梁实秋,晚上11时突然感到心脏不适,住进了台北中心诊所。11月3日清晨,梁实秋感到心闷不适,要求换大氧气罩。就在换罩停止供氧的几分钟里,梁实秋停止了呼吸。11月18日,梁实秋安葬于淡水北海墓园,正可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名人故事
梁实秋在抗战期间
抗战爆发,平津沦陷,梁实秋避往华中,于1938年春在武汉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不久武汉亦失守,梁实秋又辗转来重庆,应教育部之约,编写中小学教科书。
其后,教科书编写组与国立编译馆合并,迁往北碚,梁实秋亦随迁,于1939年在那里与龚业雅合伙购置平房一幢,取名为“雅舍”。自此,他但凡写文章,都以“雅舍”为名,终生未改。
躲离了喧嚣的闹市区,梁实秋的心境不由得松弛下来,仿佛找到一处泊船的良港,心平气和去做他的学问。他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下篇)、长篇小说《呼啸山庄》、中篇小说《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极受青年读者的喜爱。
其妻程季淑病居北平,未能来大后方,因而梁实秋的生活极其简单,粗茶淡饭则知足。他把钱花在购书上,几年中,“雅舍”内处处皆书,随处摊放,偶有客来,一时竟找不到落座之处。
粱实秋既为参政员,自然要轮到出公差。
1940年1月,他奉派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向前线进发,两个月中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
此行,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敌占区民众的困苦生活。联系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社会现象,对于未来的局面,他也开始产生隐隐的担忧。
抗战方殷,国事正多艰难,他不敢颓唐,自认应以所学之长,报效国家。回到重庆后,他自动加码,除了继续翻译外国作品外,还以“子佳”为笔名,在《星期评论》及《世纪评论》两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开辟的栏目命名为《雅舍小品》。
梁实秋的文章大多一气呵成,底稿极少涂改,但他在动笔前总是反复推敲,斟酌再三,务去繁缛枝节。这严于律己的文风,直到他的晚年仍未稍弃。
梁实秋的作品极少与政治沾边,多为直抒人生的胸臆,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故乡、朋友、往事的回忆。但这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怀旧,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战乱年代的焦虑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他写文章很投入,因而交际不广,惟有三五知己却时相过从,丝毫不吝惜时间。
他的朋友中有冰心夫妇、老舍、朱光潜、王云五等人,都是宽袍大袖、浑身书卷气之辈。只要这些文友来访,他必定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喜滋滋地参与高谈阔论,偷得半日清闲。有的时候,他还给远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吴晗写封信,他们也是老朋友。
其时大后方物资匮乏,生活清苦,各公教单位都奉命设立消费合作社,也就是要搞点“创收”。不知国立编译馆的同仁是怎么想的,竟然公推梁实秋为消费合作社的理事会主席,委托他为全馆员工谋福利。梁实秋虽然学富五车,做生意却是大大的外行,没办法,他只好另请一位经纪人代劳,自己在旁监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