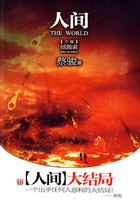汤姆显然不放心黛熙一个人出来玩,因为接下来那个星期六晚上,他陪黛熙来参加盖茨比的宴会。也许他的出席使那天晚上的气氛变得特别压抑——那年夏天我在盖茨比家参加了不少宴会,这次印象尤其深刻。人还是那些人,至少还是那类人,香槟还是源源不断地漫溢着,还是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喧闹,但我觉得现场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充盈着一种沉闷的氛围。或许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合,渐渐认为西卵自成天地,有其自身的风俗和独特的人物,是独一无二的好地方,但现在我却通过黛熙的眼睛来重新认识它。如果你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费了很大劲才适应的事物,感到难受总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来时已是黄昏。我们在数百位耀眼的客人中漫步,黛熙的喉咙不断弹奏出婉转动听的呢喃。
“这种场合让我很兴奋,”她低声说,“如果你今晚想要亲我,尼克,请随时跟我说,我会很乐意替你安排的。你只要喊我的名字。或者出示一张绿卡片。我正在散发绿……”
“请四处看看,”盖茨比提议说。
“我一直在看呀。我觉得真是太……”
“你肯定看到许多闻名已久的人物。”
汤姆傲慢的眼睛扫视着人群。
“我们很少出来玩,”他说,“其实我刚才还觉得这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也许你认识那位女士。”盖茨比指着一个明艳照人、美若兰花的女人,她雍容地坐在一株白梅树下。汤姆和黛熙望过去,认出那是某个向来只在大银幕上见到的电影明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好美啊,”黛熙说。
“在她面前弯着腰那人是她的导演。”
他郑重其事地带他们认识一群又一群的宾客。
“这位是布坎南太太……这位是布坎南先生……”略微犹豫之后,他立即补充说,“马球高手。”
“谬赞啦,”汤姆赶紧谦让,“我算不上。”
但盖茨比显然很喜欢这个称号,因为那天晚上他逢人便说汤姆是“马球高手”。
“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名人,”黛熙惊喜地说,“我喜欢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鼻子有点发青那个。”
盖茨比说出那人的名字,又说他只是个小制片人。
“嗯,反正我喜欢他。”
“我宁愿自己不是马球高手,”汤姆高兴地说,“我宁愿当一个景仰这些著名人物的……无名小卒。”
黛熙和盖茨比跳舞了。我记得当时很吃惊,因为他的狐步舞跳得既优雅又合拍——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见他跳过舞。然后他们漫步到我家,在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而我则应黛熙的要求,在花园里望风。“以防走火或者发洪水,”她解释说,“或者有什么天灾。”
我们一起坐下来吃晚餐时,汤姆这位无名小卒出现了。“你介意我去陪那些人吃饭吗?”他说,“那边有个家伙说话很风趣。”
“去呀,”黛熙善解人意地说,“把我这支小金笔拿去,你想记下地址的时候可以用。”……过了片刻,她望望四周,告诉我那个女孩“粗俗但很漂亮”,我知道除了和盖茨比独处那半个小时,她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我们这桌人喝得特别醉。这都怪我——盖茨比被叫去听电话,而两个星期前刚认识那些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挺有趣的。但原本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
“你还好吧,贝德克小姐?”
我问候的那女孩正要向我的肩膀靠过来,但还没靠到。听到这句话,她立刻坐直了,睁开了眼睛。
“什么啊?”
有个昏昏欲睡的大块头女人刚才一直在敦促黛熙明天陪她到本地的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这时她替贝德克小姐打圆场说:“哎呀,她没事的啦。她要是喝上五六杯鸡尾酒,就会像这样大喊大叫。我早就跟她说过不能多喝酒的。”
“我确实没多喝呀,”受指责的那位茫然地说。
“那次我们听见你在大叫,所以我对这里的西维特医生说:‘有个人需要你的帮助,医生。’”
“她很领你的情,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位朋友毫不感激地说,“可是当时你把她的头按到游泳池里,把她的裙子都弄湿了。”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别人把我的头按到游泳池里,”贝德克小姐口齿不清地说,“有一次在新泽西他们差点把我淹死。”
“那么你应该戒酒,”西维特医生反驳说。
“说说你自己吧!”贝德克小姐激动地喊道,“你的手抖个不停。我就算要做手术也不找你开刀!”
情形大概就是这样。我记得到最后我和黛熙站在一起看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明星。他们仍在白梅树下,两张脸凑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道淡淡的月光。我怀疑那导演整晚都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朝女明星弯下腰去,到现在终于靠得这么近了。然后我看见他弯下最后一度,亲上了她的脸颊。
“我喜欢她,”黛熙说,“我觉得她很漂亮。”
但别的一切都让她反感——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她的反感并不针对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整体的感觉。她厌恶西卵,几个百老汇名流的光临就让这个长岛渔村硬生生地变成前所未有的“胜地”。她厌恶那种与老派社交礼仪龃龉不合的粗俗习气,厌恶西卵居民那种原本家徒四壁而后富可敌国的过于突兀的命运。她无法理解这种简单的现象,所以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陪他们坐在前门的台阶上等车。这里很暗,只有明亮的前门发出十平方英尺的光线,击破了黎明前的幽黑。楼上更衣室的百叶窗上不时有人影闪过,这些络绎不绝的人影大概是在对着一面看不见的镜子涂脂抹粉吧。
“这个盖茨比到底是什么人?”汤姆突然气势汹汹地问,“一个大私酒贩子?”
“你在哪里听来的?”我问。
“这不是我听来的。是我想到的。许多这种暴发户其实都是大私酒贩子,你也知道的。”
“盖茨比不是这种人,”我懒得多说。
他沉默了片刻。车道的碎石被他踩得吱嘎响。
“他肯定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九流三教的人请到一起。”
微风吹得黛熙的灰皮领上的细毛像薄雾般轻轻晃动。
“这些人至少比我们认识那些有趣多了,”她不自然地说。
“刚才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谁说的,我很高兴。”
汤姆哈哈大笑,扭头看着我。
“你刚才注意到黛熙的脸色吗?就是那个喝醉的女孩请黛熙替她冲冷水澡那会儿。”
黛熙开始跟着音乐轻轻地歌唱,她的歌喉婉转而动听,把每个字都唱得具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的意义。她曼妙的歌声随着曲调的高低而变化,其音色之纯美足以媲美女低音歌唱家,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地将她温馨的魅力挥洒给夜空。
“这里有许多人是不请自来的,”她突然说,“那女孩就没受到邀请。他们直接闯上门来,他又不好意思拒绝。”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汤姆旧话重提,“我想我会搞清楚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她回答说,“他是开药房的,有很多家大药房。那些都是他亲手创办的。”
那辆姗姗来迟的豪华轿车缓缓地驶过来。
“晚安,尼克,”黛熙说。
她的目光离开我,直奔光线明亮的台阶上端而去,那年流行的伤感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82]正从前门飘扬而出。终归到底,盖茨比的宴会虽然不讲繁文缛节,却有着罗曼蒂克的可能性,而这在她的世界里是完全没有的。这首动听的乐曲不就引得她忍不住想要回到里面吗?在随后几个小时,那昏暗的大厅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会有一位不可思议的宾客,一个倾城倾国的佳人,一个明艳动人的少女,向盖茨比投去倾慕的眼神,然后刹那间的神奇邂逅就会把五年的坚贞不渝一笔勾销。
那晚我待了很久。盖茨比让我等到他有空再聊几句,于是我在花园里流连,直到那些下海游泳的客人浑身哆嗦、嘻嘻哈哈地从黝黑的沙滩跑上来,直到楼上那些客房的灯光都熄灭了。然后他终于从台阶上走下来,他那晒得发黄的皮肤在脸上绷得异乎寻常的紧,眼睛还是很亮,但有点倦意。
“她不喜欢这场宴会,”他迫不及待地说。
“她当然喜欢啦。”
“她不喜欢的,”他固执地说,“她今晚玩得不是很高兴。”
他沉默了半晌,我猜他心里大概有什么说不出的苦恼。
“我感觉和她离得很远,”他说,“很难让她明白我的想法。”
“你是说跳舞的事情吗?”
“跳舞?”他打个响指,把他开过的所有舞会都取消了,“老兄,跳舞并不重要。”
他对黛熙没别的要求,只希望她走到汤姆面前并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在她用这句话抹杀过去四年之后,他们就能决定要采取哪些更为实际的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等她恢复自由,他们将会重返路易斯维尔,在她家举办婚礼——仿佛一切回到了五年前。
“她不理解,”他说,“她以前很善解人意的。我们常常坐上几个小时……”
他说到这里就停了,开始凄凉地在满地果皮、客人收下又丢弃的礼物和被踩烂的花朵之间走来走去。
“还是别要求她太多吧,”我斗胆提议,“人是无法回到从前的。”
“无法回到从前?”他不以为然地喊道,“当然是可以回去的!”
他神经兮兮地东张西望,仿佛从前就躲在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只要伸出手就能抓到。
“我会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像从前那样,”他坚决地点着头说,“她会明白的。”
他说了许多从前的事,我觉得他是想找回某种他和黛熙恋爱时丢失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自己的某些看法。他的生活在那以后变得混乱不堪,但如果他能回到某个起点,慢慢地重新再来,他就能找到丢失的到底是什么……
……五年前的某个秋夜,他们在街上走啊走,落叶纷纷飘下,他们走到一个没有树的地方,人行道上洒满了皎洁的月光。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转身彼此对视。夜凉如水,空气中弥漫着每年夏秋之交特有的神秘而兴奋的气息。安静的灯光从几处屋宇中透射出来,打破了黑暗的夜色,天上的星星也不肯安宁,片刻不停地闪烁着。借眼角的余光望去,盖茨比看见一段一段的人行道变成了梯子,直通到树梢上方某个秘密的地方——只要他独自往上爬,他就能爬上去;爬到顶部之后,他就能吮吸生活的乳头,大口大口地喝下那无与伦比的神奇奶汁。
眼看黛熙白皙的面庞向他的脸凑过来,他的心越跳越快。他深深地知道,只要他亲吻这个女孩,让他那些无法言喻的梦想和她容易消失的呼吸永远地结合起来,他的精神就再也不能像上帝那样自由自在、毫无羁绊了。所以他等待着,再次静静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他亲吻了她。在他的嘴唇的触碰之下,黛熙像花朵般为他盛放,而他从此也就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听完他伤感的回忆,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某段飘忽不定的乐曲,几句早已遗忘的歌词,也许是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听过的歌。刹那间,有句话试图通过我的嘴跑出来,而我的双唇像哑巴那样张开,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还有什么在它们之上挣扎。但它们终于没有发出声音,而我几乎就要想起来的东西,也变得永远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