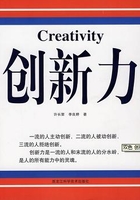作为一位公务员,一位做了十年办公室主任的公务员,近期,亚东是悲伤的。
亚东悲伤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人给他投毒。
当医生告诉亚东,他中的是一种罕见的毒时,他大感意外。医生说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毒,相当少见,生活中,不大可能中这样的毒,除非有人故意投毒。
三天前,亚东感觉头晕,手脚显得很笨重,他以为是近期操劳过度而且睡眠不够造成的,就请假回家休息。
闭上眼睛躺在床上,感觉像腾云驾雾般飘在半空中。家中的药箱有不少药,但亚东不知自己这算不算病,没敢乱吃。正当亚东在半睡半醒间思考着要不要到医院去的时候,下属打电话来说省里领导去某处考察,顺道经过本市,问亚东能不能出面招待。对于招待领导这项工作,亚东驾轻就熟,他也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亚东一听到领导要来了,心里突然涌起了无限的厌恶,就交待下属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让下属自己去张罗。
打发了下属,亚东起来喝了一大杯水。自从头脑开始晕眩以后,他就不停地感觉到口渴,一天喝十几大杯水还觉得喉咙不舒服。夜里也要起来喝两三次水。喝水太多的后果是频繁地上厕所。
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马丽芳。她在电话里追问亚东是不是为了躲避她而绕路去上下班了。
亚东没好气地说病了,躺床上快要死了。马丽芳哪里肯信?昨天亚东还神气活现地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今天怎么可能快要死了呢。亚东不理她,掐断电话闷头睡。过了大约半小时,马丽芳又打电话来,咋咋呼呼地对亚东嘘寒问暖起来。亚东心中疑惑,以为马丽芳这是在跟自己作此生最后的道别。亚东心中烦躁不安,想找个理由快些结束通话的时候,脑里突然灵光一闪,猜到了马丽芳打电话到单位去向他的同事证实自己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想到马丽芳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不禁有些担心,马丽芳是冲动型的女人,亚东无法想象她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会说些什么样的话。
“你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去了是不是?”
“人家担心你。”
“现在你知道我真的生病了,你安心了吧?”
亚东本想就此结束通话,他有些累,但马丽芳不让他消停,非要等亚东把症状详细描述一番才肯掐断电话。亚东的病情也没什么出奇之处,无非是食欲不振、浑身无力、口干舌燥、虚火上升,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像醒着,醒着的时候像在睡觉……说了半天,亚东自己也有些奇怪: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听起来像是肾亏。”马丽芳说。
“哈,”亚东忍不住大笑,“发神经呀你?”
亚东把手机调成无声,扔在客厅里,又回到房间睡觉。虽然知道自己八成还是无法入睡,但他还是执著地回到床上去。身体很沉,床很轻,头很沉,脚很轻,身体往下坠,床在天上飘,头像是别人的,脚像没了血似的凉……脚板底有一块硬硬的东西,似乎脚底中间有块皮肉坏死了,变成了木头一样……人不舒服的时候大多会躺到床上去,虽然坐在客厅不会比躺在床上更难受,但一旦有病,床就是最好的选择。
亚东对马丽芳说没什么事,躺一会,好好睡一觉,明天又可以跟她一起骑自行车了。
在床上躺到傍晚时分,亚东想起来去买菜做饭,但刚一起床,脚就发软,一头撞到门上去,“砰”的一声巨响。在床上半梦半醒地躺了几个小时后,病情反倒加重了。
亚东跌坐在沙发上,养了半天神,才存够了给老婆泡一杯灵芝茶的力气。亚东坐在餐桌旁边,用筷子搅着气味难闻的灵芝茶。
儿子开门进屋,闻到灵芝味道,又像往常那样皱眉。
亚东告诉儿子他不舒服,让儿子把冰箱里的鸡肉拿出来解冻,等妈妈回家后做饭。
“你不舒服就不要做了。”儿子说完,拿起电话就打给某个快餐厅。
望着自作主张的儿子,亚东既甜蜜又酸涩。他想告诉儿子自己没胃口吃晚饭,但当他回过神来后,儿子已经完成了叫餐事项掐断电话进房间去了。
亚东把自己摊开斜靠在餐椅上,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风筝。亚东睡着了,像只断线的风筝那样瘫在椅子上睡着了。在舒服的床上挣扎了一整天都无法入睡,没想到在这张用了十余年的旧椅子上一靠就睡着了。
亚东觉得自己睡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虽然他只是睡了一刻钟。他被下班回家的老婆何融叫醒了。
天说黑就黑了。屋里已经黑得看不清五官的时候,何融回到家中,开了玄关的灯,猛地看到亚东张大了嘴巴仰瘫在椅子上,脸冲着大门的方面,吓得双脚发麻——她以为亚东死掉了。何融壮胆伸手在亚东的颈动脉上把了把,感觉还有脉象,才松了口气。望着柔和灯光下的丈夫,何融难得地温柔了一会。她端起丈夫为她泡的灵芝茶,掐着鼻子把还温温的茶喝下去,然后在丈夫面前蹲下,拉着丈夫的双手。然而,亚东冰冻的手,又把何融吓了一跳。女人的直觉是敏感的,她意识到事态有些严重。早上上班前,她听到亚东说不舒服,要请假在家休息,以为亚东只是感冒,现在看来,事情严重得多。
何融到厨房里转了转,看到炉灶是凉的,担心又加重了些。
快餐厅的饭菜送到,周琪昌出来跟妈妈说他订了餐,让妈妈付款。
打发了送餐员后,何融打开客厅的大吊灯。
何融和周琪昌一左一右站在亚东旁边。他们在观察亚东。
儿子拉起亚东的手问:“妈你看,我爸的手怎么这么黑?”
亚东十个手指头都是黑色的,像涂了酱油。何融以为亚东死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以为亚东死了。她使劲推了一下亚东的肩膀,差点把亚东连人带椅子推翻在地,还好被儿子扶住了。
亚东醒了,揉搓着眼睛奇怪地看着母子俩。亚东忽然觉得自己的手有些不对劲。他的手麻了,关节像长了锈一样不灵活。
何融松了口气,招呼亚东和儿子吃饭。
“我的脚麻了。”亚东说。说完,他站了起来。他刚站起来,脚底下传来一阵钻心的痛。脚底痛,臀部麻,头晕,胸闷……亚东刚一站起来,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两眼一黑,摔倒在地。
母子两个,好一阵手忙脚乱才把亚东搬到床上去。他们本来要打120求救,被亚东阻止了。亚东的晕眩只是暂时的,他的神智很快就恢复清醒了。
在灯光下,亚东查看自己的脚板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除去十个脚趾跟十个手指一样像涂了一层酱油外,脚心处还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色淤血。刚才那钻心的痛就是来自那淤血处。亚东用手指推了推那淤血,痛得眼泪都滴了出来,忍不住呻吟了一声。何融在外面听得不对劲,进来,看到这情景,身上涌起了鸡皮疙瘩。
母子二人合力把亚东送到医院。在路上,何融用手机跟相熟的医生说明了来意,那医生虽然已经下班了,但还是答应过去看看。
两年前,何融在医院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也还定期到医院去检查,长期的接触,令她跟医生护士们亲若朋友。
医生说亚东中毒了。
事后,亚东与何融讨论此事时,认为有人给亚东投毒。何融说:“你们那是什么单位?居然连毒都敢投,毫无人性可言。”亚东苦笑:“其实我应该庆幸,那个人用的是慢性毒药,如果他用的是砒霜,我命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