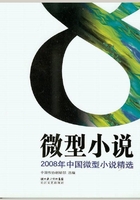扎括的阿爸是草原上少有的骑手,每当他骑着马走在草原上时,他和他的坐骑身上就沾满了人们赞叹和羡慕的目光,像无形的晶体。随着马的颠簸和抖动,晶体的碎片被抖落在地上,又有无数的晶体紧接着附着上去。扎括的阿爸便一身珠宝,一身黄金,珠光宝气中神气活现。当年,扎括的阿妈美貌出众,是草原上的小伙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竞争对象,就是被阿爸身上耀眼的光环所吸引,嫁给了他,阿爸就成了许多小伙子的情敌。
可是现在,马匹一匹匹减少,阿爸身上的光环也慢慢暗淡下去。当草原上出现第一辆摩托车,人们再也看不到阿爸身上的光环了,就像是一支燃烧殆尽的蜡烛无可奈何地挣扎了几下,永远地熄灭了一样。随着光环的消失,阿爸日渐憔悴,形容枯槁。一种怪异的病纠缠住了阿爸——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他就会浑身发颤,不能自已,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短暂的休克。当草原上有了第十一辆摩托车,阿爸在一声痛苦的呻吟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第十一辆摩托车是图罗家买的。
阿爸去世了,他为扎括留下了一匹善跑的白蹄马。这是阿爸这一生拥有过的第三匹好马。就在阿爸像一轮奄奄一息的太阳,就要永远地陨落下去的那一刻,他把扎括叫到他身边,对扎括说:“白蹄马是一匹好马!”
“我知道,阿爸。” 扎括哽咽着。
“白蹄马不是摩托车!”阿爸又说。
“我知道,阿爸。” 扎括哭出了声。
阿爸示意扎括把眼泪擦掉,他说:“我是骑手!”
“我知道。” 扎括强忍着眼泪。
“你就是我!”阿爸说着,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缕锐利的光,直直地刺进了扎括的眼睛。扎括不敢说话,屏着呼吸,看着阿爸慢慢闭上眼睛,就像是把一把锋利的藏刀慢慢插进了刀销一样。
扎括成了他自己的阿爸,成了白蹄马的主人。
扎括和他的白蹄马是注定要出人头地的。
当草原上的牛羊群慢慢接受了作为马的替代品出现的摩托车,把这种笨重的铁家伙视为与自己一样属于牧民,依附着草原繁衍生息的同类的时候,名声远播的青海湖把好多与草原毫不相干的人们吸引到了它身边。
“青海湖太美了,是熔化了的天空凝固在了地上。”
“是一面深邃的镜子!”
“是眼睛,洞视未来的眼睛。”
“是蓝宝石,无价的!” 这些人绞尽脑汁,想出许多溢美之词讨好青海湖。
扎括觉得这些人都是图罗家的亲戚,他们和图罗一样迷恋青海湖。这几天的图罗也是兴奋异常,乐此不疲地骑着摩托车跟随在这些人的前后左右。他还学会了汉语:“欢迎你到青海湖!”,他也学会了英语:“hello”
青海湖飘飘然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它不断地和这些人合影,摆出各种搔首弄姿张牙舞爪的动作来。有些人甚至搂住它的腰,把一张臭嘴贴到它的脸上,它也是来者不拒和颜悦色。
这些人看了青海湖,还意犹未尽,他们要看扎括他们是咋样吃饭的,咋样睡觉的,咋样放羊的,咋样结婚的。
“只要让我们看看,就给钱!”这些人拍着缠在腰里的鼓鼓的钱包,理直气壮地说。
牧民们动心了。更加动心的是乡上的当家人。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赛马队,接着又成立了一个结婚队(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改成了婚俗队,但牧民们仍然叫结婚队)。扎括和他的白蹄马理所当然成了赛马队的成员。曾经遭到牧民们唾弃的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刚开始,扎括对这个草草组织起来的,鱼目混杂的赛马队嗤之以鼻,可是他发现由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组成的结婚队里有彩彩,彩彩是结婚队的新娘。有时候,那些来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们既想看赛马又想看结婚,又不愿意走太多的路——其实只有几里路——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就来到扎括所在的村庄,“友情出演”,扎括就时常可以看到彩彩。因此,扎括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赛马队。这样就不用让白云为他们捎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