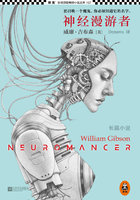晚上,许粼粼推开李亚如房间的门,看到李亚如正趴在床上。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露背晚礼服,把脸埋在一堆头发里,头发柔软蓬乱,裹着她的脸像一只鸟巢。许粼粼倚着门看着她,她也从床上看着她。她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之后,李亚如先开口了,她从床上翻身起来,看着身上的裙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新买的,很贵,为电视台的演奏会准备的。别人一定准备黑色的礼服,所以我就准备一条红色的。喜欢吗?屋里只开着一盏床前的台灯,一束灯光正落在李亚如的红裙子上,那红便像活过来一样,血腥地茂密地蜿蜒着,流的到处都是。她站在那里倒像是从这红色里长出来的。许粼粼站的地方是背灯光的,她的身体和脸都模糊不清,如同剪影。
她静静地看着李亚如的红裙子,突然问了一句,你到底怎么了?口气里的平静深的有些异样,像很深很深的夜里的一种睡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李亚如暗暗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踩着这句话落到了地上。刚才,在许粼粼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她就准备着了,准备着今晚会有一场战争。她一边抚摸着那盔甲一样的红裙子,一边等着许粼粼挑战。可是,现在,她的等待和防御突然用不上了,竟有些一脚踩空的感觉。她想,她究竟想干什么?欲擒故纵?把自己当一只老鼠一样放生了再抓回来?
不行,今天晚上她必须主动地给她点颜色,不要让她以为自己就是坐以待毙的。她扭了扭台灯,灯光从她身上移开,落到了墙上,她们两个人的影子都被投在了墙上,巨大的,松脆的,单薄的,像她们风干了的魂魄贴在那里。李亚如像是从舞台的追光灯里走出来了,她和许粼粼都在舞台下了,她们都看不清彼此的脸。她开始说话,她说,我想我有找男朋友的自由。那个影子在她身后停住了,她甚至看得清楚她雕塑一般高高的盘发。可是她的声音却在她身后响起来了,那声音里面竟带着些笑声,听起来清冽而异样。她说,当然。突然的,李亚如看到那身后的影子和她的重叠到一起了,然后又分开了,现在,许粼粼站在她的面前了。许粼粼直直看着她,突然说,你害怕我吗?李亚如摇头,向后退了一步。
第二天早晨,李亚如狂奔到教室的时候,王崇人已经和另一个男人等在那了。他一见她就说,你怎么能迟到半个小时,你太没有纪律性了。李亚如连忙拿出提琴,一边慌不择路地翻乐谱,一边急急地说,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昨天晚上我竟忘了上闹钟,今天早晨起晚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王崇人指着身边的男人说,这是电视台的音乐编导,过来看看你们准备的情况,后天就是演奏会,你今天要表现好,不要慌,就像平时那样。李亚如把音谱摆好,调好弦,闭上眼睛,大大呼了一口气,然后,第一个音符拉下去了。舒曼的《嘉年华》。音符一路狂流下去,突然的,音乐像撞到了礁石上,音符碎了,七零八落的,到处是碎片,然后,碎片也落在了地上,音乐戛然而止。李亚如抱着突然哑下来的大提琴,扯着头发绝望地喊了起来,我今天演奏不了,不行,我进不了状态。王崇人走过来,问,你怎么了,你是来这学提琴的,就应该专心点,别的事以后再说。我是向编导推荐你参加演奏会的,但要看你自己的表现。李亚如抱着提琴一直在那喃喃自语,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
晚上,李亚如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死命练琴,许粼粼在自己的房间里熨那件红色的晚礼服,门开着,许粼粼像是镶在那扇门里,那扇门是红色的绢扇。她一边熨衣服一边听李亚如的琴声。李亚如反反复复地重复着第一小节,仿佛是个险滩,船怎么也过不去,只绕着漩涡不停在原地打转,进不得,退不得。突然,嘶一声,布帛被撕开的声音,音被拉破了。李亚如一声不吭地又从头开始,但这次调子更高更尖利了,像随时都会折断,果然,音没有再高上去,打了几个旋就一头栽下去了,像一只中了箭的鸟。许粼粼捧着那堆红色走出了自己房间,在她身后说,把心安静下来,你不要为了演奏会而去演奏,就像你平时自己练琴一样,你真的拉得很好,我第一次听你的琴声就喜欢上了。
李亚如没有说话,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又从头开始。还是不行,又堵住了,她狂乱地用手抓着琴弦,沉闷的混乱的音符像石块一样噼里啪啦砸了一地。许粼粼走到她身后把手放在了她肩上,说,安静点,再来一次。李亚如扔下琴站了起来,不要管我好不好,你让我自己呆着,你走开。说完,她向自己的卧室走去,许粼粼在身后死死抱住了她,李亚如越挣扎她抱得越紧。这时候,许粼粼突然把脸贴在了她的脸上,她的泪也沾到了她脸上,许粼粼在她耳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的。李亚如闭上了眼睛,流着泪。
电视台的音乐演奏会结束了,李亚如排到第四名,没有被选上。当所有的人正慢慢退出演播厅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许粼粼忽然走到了王崇人面前,她拦住了他的去路,说,王老师,为什么没选上李亚如,她弹舒曼的曲子再合适不过,充满柔情。我是她的室友,只有我能看到她每天没日没夜地练琴,她勤奋而有悟性,你们却为什么不选她。王崇人看看周围说,不好意思,小姐,她是我的学生,我当然知道,可是这是评委们的决定。由于舞台经验不足,她还没有克服怯场的问题。许粼粼打断了他的话,你根本不了解她,她的确不是四岁就开始学琴的那种,她是在农村长大的,她还要学习大提琴,这本身不令人感动吗?你们把她当什么,当马戏团的小丑,替你们充数?你知道对她这样从小地方出来还想从事艺术的人是多么艰难,给她一次鼓励是多么重要,你们只顾着你们自己挣钱升官,什么时候真正地把艺术当回事过?李亚如穿着那件红礼服从人群里冲了过来,拉住许粼粼就向外走,许粼粼还要说什么,李亚如死死拽住她,拖着她往出走。人群里让出一条路来,目送着两个缠在一起的女人走了出去。在她们身后王崇人说,这位小姐,你应该对着空气去发泄你那些不良的情绪。
演奏会结束之后,李亚如请了两天假没去上课,以示抗议。她的父母来了,来看她,她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晚上,许粼粼做了一桌丰富的饭菜,四个人坐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许粼粼说,其实,我真觉得你弹地比他们都好,你们这个圈子里真是黑暗,谁知道那两个选上的有什么关系。你那老师也不帮你,是不是你没给过他好处。我真看不惯他们,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打算学艺术,科学的东西丝毫差不得,不是谁说了算就可以算。像这演奏会,谁最后参加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李亚如的父亲忙说,就是就是,没有关系走到哪里也难办啊,小如年龄小点,不太懂事,以后还麻烦你多照顾她,我们两口子没什么文化,干瞪眼也帮不上忙。许粼粼笑着给他们夹菜,她手边准备着黑白两双筷子,白筷子自己用,黑筷子给别人夹菜。她说,那是一定的,我很喜欢她的。她要租我房子的时候,我还没见她,只听电话里的声音就想,就她了。缘分真是有意思的事情。她父亲忙对李亚如说,小如你运气真好啊,一来上学就遇到这么好的朋友。李亚如正举着杯子,在灯光下看里面剔透血亮的红酒,听到这句话突然就笑了起来,她使劲地笑着,最后都笑地趴在了桌子上,忽然抬起头来却已经是一脸的泪水。她也不擦也没打招呼就钻进了自己房间。
李亚如躺在自己床上,她母亲也跟着进来了,带着一个长长的虚虚的影子。那影子里像满是问询,却没有一处开得了口,只严严实实地装起来,还扎了口。就像她在家里一样,永远把所有的话埋在深不见底的地方,她独自一个人慢慢消化,即使是铜是铁,她也能把它消化掉。李亚如看着她的影子心里就有些来气,在这样一间租来的小卧室里她都要把自己弄的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什么都怕,见了虫豸都要让路。她索性扭过头不看母亲。母亲却已经无声无息地走到了她身边,她觉得自己的肩膀被什么碰了一下,很轻的一下,芯子里却有坚不可摧的东西。她一扭头,是母亲把一个纸卷伸到了她面前,像伸出来的一截树枝。
她怔怔地看着那卷被包起来的纸。母亲说话了,声音也像是躲在人后面的,与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只远远地怯怯地独立悬在那里。她说,你的停薪留职保不住了,有人告了你,从这个月开始工资就停发了。这钱你先拿着用,还得交学费,还要租房子,这房子这么好,很贵吧?钱不够了就和家里说。李亚如看着那卷钱,不接,那卷钱就直直地一动不动地伸到她面前,干枯地委屈地伸着。最后,母亲拿起她的一只手,把它放了进去。母亲衣服深处的气味从那卷钱里散发出来,像血液一样流进了她的手心里。她瑟瑟地打开,是一沓整整齐齐的钱。她的泪就下来了。她们没有说一句话,李亚如转身静静躺着,闭上了眼睛,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下去,流到了脖子里。
第二天一大早李亚如的父母就起床了,他们要赶最早的汽车回家。许粼粼也起来了,在他们临出门前,她突然取下了墙上的一副画,在李亚如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这幅画已经塞到了李亚如的父亲手里了。她笑着说,这是我母亲的画,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当然,你们要是不愿意留着,也可以卖掉,她的画在市场上还是值些钱的。李亚如的父亲呆了半天才扭头对李亚如说了一句,真是你的福气啊,一定多听人家的话。许粼粼要出去送她父母,她父母亲千恩万谢地往出走,她不忍心跟出去看他们诚惶诚恐的样子,就站在了那里。李亚如看着墙上空出来的那块白,想,一副画就把她的父母亲都收买了,简直已经收买了她的全家。那以后,她全家都得听她的?她成了她们家一个隐形的女皇?这时候,许粼粼回来了,她收起刚才送人的表情,换了一副表情对李亚如说,怎么还不去上课,再不去又迟到了。
李亚如不忍再看她第二眼,她看着别处,一咬牙,让自己尽量飞快地说下去,都是昨晚就打好了草稿的话,说出来不过是回一次锅,我想我得搬走了,我的工资被停了,我没有收入了。我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学,我不能让我们的父母供我。当然,学我还得上完,我不能半途而废,但是我必须得节约,得省掉一切不必要的开销,我得搬出去,到郊区找个便宜的小房子。许粼粼停顿了几秒钟,说,可是你要住到郊区就得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路上。李亚如对着墙笑了笑,没有说话。许粼粼走到了她的身后,她听见声音从她背后传来,像一只手蹭着她的脖子。她说,你不要搬了,就住这吧,我不收你的房租。
李亚如在往教室走的路上,觉得身体里有成千上万个自己在不停地问,为什么就同意了,为什么?再和这个女人住下去?就因为她送了你父母一副画?就因为她免去你的房租了?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她突然打了个寒战,因为她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她其实已经猜到许粼粼会这么做的,可她还是说了出来,并且她答应了她住下来。原来,她其实在以自己为诱饵去要挟许粼粼什么。
又过了一个月,在早晨去教室的路上,李亚如看到海报栏里贴着一张巨大的彩色海报,是大提琴家段天馨要来音乐学院举办一次高级音乐培训班。海报上,段天馨穿着黑色的晚礼服在灯光下演奏大提琴。周围没有什么人,她久久看着那张海报,然后向教室走去。她突然周身燥热和紧张,似乎血液在身体里逆着流动起来,她不由地加快了脚步。这紧张在她身体里凝聚着,挣扎着,像一个人形,这紧张是见不得人的,却还一定要把头伸出来,她只好拼命把它按下去。这天,在教室里拉提琴的时候也是分外的紧张,身上的弦和琴上的弦都是绷紧的,似乎不碰都会响。她一连错了两个音符,拉高了,从音乐里跳了出来,像在一幅画上戳破了两个洞。王崇人打手势,停,你怎么了,好像很紧张,为什么这么紧张。李亚如垂着头,没有的。王崇人说,那先休息几分钟吧,你把自己放松一下,你看你的手腕,都是僵硬的,怎么拉琴。
在他往出走的时候,李亚如在身后叫住了他,老师。王崇人回过头来看着她。她的表情有些奇怪,也像一张拉满的弓,上面是随时会离弦的箭。她把准备了一早晨的话小心地放在了弦上。她说,老师,段天馨要来办高级音乐班吗?王崇人看了她几秒钟,他开始明白她这紧张的出处了。他说,你没看到海报吗,她明天就来。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是高级音乐班,其实是要在音乐学院收两个门徒。如果当了她的学生那已经半只脚踩进音乐家的行列了。你好好准备,你是拉大提琴的,又是女学生,有时候搞艺术的两个女人之间更容易沟通,如果你们某一方面的确很像的话。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李亚如忽然对他一笑,眼睛里亮的可怕,像在里面点起了一盏蜡烛,她说,我就是小时候看了她的演出才记住大提琴的。说完,眼睛里那层亮亮的壳碎了,她忙转过身去,泪流了一脸。
下午的课结束的时候,王崇人说,你今天太紧张,晚上不要练琴了,好好放松一下,明天她会听你们几个大提琴的学生拉琴,发挥得好一些。当他正准备往出走的时候,李亚如忽然在他身后又喊了一声,老师。这声音像一节烧完的碳,看似喑哑灰败的,一摸却是灼人的。这声音触到他的皮肤时,他突然也感到了一丝紧张,一定是对面这个女生太紧张了,没有别的原因。教室外面是草坪,远远的路上有几个学生零零散散地往出走,百叶窗拉着,草坪看上去像斑马一样,一截绿一截白。天光在渐渐转暗,他们之间的那段距离开始渐渐浑浊起来,像玻璃突然增厚了。这时候,李亚如突然迅速地做了个动作,她一言不发地却是准而狠地解开了衬衣上的第一粒纽扣,不带一点犹豫的,她动手前已经把那一点犹豫全剔出去了。接下来的动作便更流畅了,连成一串的,急速的,向一个方向聚拢而去。音节越来越急,越来越快,已经看到底了,她只剩下了最后一条内裤,然后,在一秒钟的停顿之后她毫不手软地把它脱掉了,那条内裤柔软无声地落在了地上。到底了,音节戛然而止。
她站在那里看着王崇人,目光里是严严实实的,没有一点躲闪,也看不到来路。黄昏的光线从百叶窗里透进来,斑驳地从她身上碾过去了。王崇人捡起她落在地上的衬衣,给她披在肩上,她却躲开了,她的脸上也是斑斑驳驳的光线,像一幅丛林里的面具。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清晰地听到了,她说,老师,把我推荐给段天馨,我真的需要这次机会。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等了很多年。王崇人再一次把那件衬衣披在了她身上,李亚如再次躲开了。然而,那件衬衣最后还是落在了她的肩上,然后隔着薄薄的衬衣他轻轻拥抱了她一下,你要相信自己,段天馨也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相信别人的话的。今晚早点睡觉。
教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赤裸着抱着那堆衣服,蹲在地上,把头埋在两腿间,却也不穿衣服。好了,落地了,火已经熄了,王崇人收到一截里面还是通红的碳,退给她的是一截灰烬,真的灰烬。她久久抱着自己,不愿把脸抬起来。今夜剩下的时间怎么过啊,自己像站在跳水板的极端了,随时会一跳冲进明天的时间了,只是这明天,却不知道是什么。她浑身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