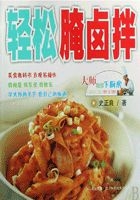丁当还没有回家,我的手机很安静。她不会知道我正跟着一个戴蛤蟆镜的女郎呆在名贵跑车里相顾无言。在出发前,我告诉丁当去见一个老朋友,她也没问究竟是谁。
丁当认识她,有时候也问我。我说我不知道,老死不相往来了。我想到丁当那时的古怪表情,就心生愧疚。戴蛤蟆镜的女人还在开车,她问我听点音乐吗。问完,音乐就响了起来,很熟悉的旋律。
丁当第一次说那个女人不好的时候,我刚从209的小旅馆里出来。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们戏言,209就是我包下来的总统套间,即使床板很硬,热水时有时无,还有残缺的窗帘。那个女人也跟着附和嘻嘻地笑。丁当在她背后说她不好,我只把那些话当小女孩的不良居心,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当然知道丁当喜欢我,她的眼神老是那么咄咄逼人。我问丁当究竟怎么不好,她说不好说,她的意思是让我提高警惕,说完丁当就走了,那天还下着小雨,我想要送她,她说不用了,有人等她。
我和丁当老早就认识了,自然在那个女人出现之前。也有人撮合我们,我说要好早就好了,还能等到今天。她打断我,人家看不上。气氛有些讪讪。我冲她说,要是跟你好了,时间会过得很慢,生命就更加漫长了,我不想活得那么长。她就跳起来捶我,我们俩在桌子周围打得团团转,像两个孩子。
丁当第二次说那个女人不好,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就看不得我幸福。她哭了。她说那个女人真的不好,我眼看着她上了一个男人的汽车,男人还亲了她一口。我说她居心叵测,她说,你要不信,我就再说得详细点,那个男人是个秃头顶。我说够了,打断了她的话。她站在我面前很委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我有男朋友了,你好自为之吧。
丁当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年,我也从来没有找过她。我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不过她的话是真的。
那个女人跟我好了几个月,又搭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她没有跟我分手,她后来说那不叫移情别恋,心还在我那放着。我相信她的话,她只是缺钱,她问我介意吗。我摸了摸她的脸,又看了看她的眼,说不介意。我的爱都低到尘埃里,会不会开出小花儿。
我见过那个男人一次,是个秃头顶。丁当说得没错。他跟我握了一次手,手大而温暖。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俩都很自然,谈笑风生,我觉得怪怪的,我要走,他们也没有拦我。我回头跟那个女人对了下眼,她也希望我走。
突然有一天,她说她要跟那个男人走了,再也不能见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刚说完一个无聊的笑话。她就倚在嗡嗡响着的电冰箱门上,那台电冰箱如今还在,只不过响得更厉害了,我老说要换,丁当说还能用。她垂着头,不敢看我,我说,你还要再想想嘛。我又说,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想。她没有,扭过头去看窗外。
我扑通跪了下来,我怎么会跪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很想把她留下来。她流着泪拼命摇头,我也相信泪是真的。她说,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不可替代,但是我必须走了,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你太屈辱了,我又不能没有他。她说完我就站了起来,站在她面前,又抱住了她,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我永远有个肩膀供你依靠。她伏在我的肩上抽泣。
我说,祝你幸福。她说,你也一样。
再后来,丁当出现了,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丁当变了个样子,头发越来越短,脸却越来越胖,还常常用脚趾头指着我。我只是想要个孩子。
音乐戛然而止。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拍了一下方向盘,就嚎啕大哭起来。我给她递纸巾,她又摘下了蛤蟆镜。
过了许久,她开始说话,断断续续。
她的话我懂了。我说,你不是为我生,事实上,是我为他生,你不就想借个种吗?
她问,他会不会杀了我。她的脑袋耷拉下来,落在方向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