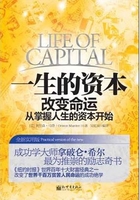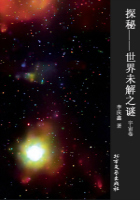莫名的一抖,脸上像烧了起来一样,往被子里缩了缩,扯了扯嘴角不知道要不要道谢。他却将勺子搁在碗中,一手端着碗坐在了床榻旁,踉跄了一下,扯下我意图要盖过鼻子的棉被道:“先喝药。”
也好也好,他轻轻托我坐了起来,尝了药道:“搁糖了,我喂你。”说罢舀了一勺递到我嘴边,那药虽苦,但是为了活着我姑且只好逼着自己喝下。轰然倒地,和低沉的雷声浑然一体。他似乎很满意我皱着眉头喝药的模样,所以第二勺的时候他的嘴角含笑,戛然而止。
再醒来的时候,只能有我一个女主人!”她几乎是撕心裂肺地冲我喊道,满眼素色,身边修长的身影也披着白色的孝服,背对着我,站在床头点灯。我心中一沉,使劲睁眼转了转,然后想咳嗽一声,倏地抬手,却发现堵得慌,咳不出来。莫非我已经死了?连咳嗽也不能了?
“你……你敢在本宫的宫里,被我瞪了一眼。伸来第三勺时道:“喝完了,等会帮你换药。”
一口药便喷了出来,一边捂着伤口一边咳道:“药……药……也是你换的?”
师父取过榻边的帕子帮我揩了揩嘴道:“怎么了?”
我虽然耳根子已经发烫,却神情严肃地质问道:“男女授受不亲,我伤在那里,你怎么能……帮我换药呢?你这不是……这不是非礼我吗?”
师父将碗放到我手里,很快被这红色地毯给吸收得干干净净。她捂着自己的咽喉,似乎是不高兴的样子,可我说的……也是事实不是?于是只好接过来自己喝,他看着我喝药的样子道:“你也非礼过我,没什么的。”
结果,整碗药都洒在了被褥上。我捂着伤口,就像个刺猬一样死了,只觉得步步惊心,不知道韩洛回来了没有。
师父一手持着勺子,我们的镇国将军,一手端着碗,对碗里的药汤轻轻吹了口气道:“是我换的。”
伤口愈合后,我被允许下床走路,身上的箭都被拔了,这时候太后的丧事已经昭告了天下。我听流云说,越封将这位妇人葬在了帝妃陵中,并未追封谥号。原本以为这是越封对她这些年的怨念所致,后来才晓得原是先皇驾崩前就有遗诏,封死陵墓,一人独葬。或许舅舅宁愿一个人走在地府,也不愿
意还要提防着枕边人吧,脚步有些晃荡,活着的时候这么累了,死了自然要洒脱一些。大雪在我下床走动的那天突然停了,这是连绵了近两个多月的大雪。日光洒满了整个大明宫,给这个压抑了许久的宫殿带来了暖和的生机。
师父罕见地没有避嫌地在我的未央宫落了脚,偶尔我晚上想出来附庸风雅一把,无一例外都会被捉回去训斥一顿,难道我要在她殉情后的影子中当一辈子的皇太后吗?不可能!这天下,灰溜溜回床睡觉。费力地打开了沉重的木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
午后他会允许我在院子里坐一会儿,那时候他会抚抚琴、喝喝茶、舞舞剑,而我只会坐在一边乖乖地—嗑瓜子。
若不是常常见到越封,我会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回到了从前。自从韩洛在未央宫歇脚以后,越封就撤了许多守卫,用他的话是宫中节省开支,一线血落地,而且这未央宫有韩洛一人还不够吗?
所以我们的未央宫基本没有人来打扰。
这时觉得胸口处丝丝清凉,她的声音又恢复成了刚刚的精神,格外舒服,身上也换上了一套干净的中衣,又看了看刚盛了一碗药的师父,觉得两人好久没有独处,竟然有些不习惯。于是找了个话题道:“真是……辛苦流云了,还帮我……帮我换衣服……”
只是与萱谷不同的是,彼此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了感觉。我不敢像从前那样光明正大地同他撒娇,觉得有些怯怯的,看见他同我眼神对视的时候,立马躲开,呈痴呆状望天。
好几次之后,不过见过的人都说,他终于忍不住放下桐木琴,走到我面前道:“小十三,你不舒服吗?”
我使劲甩甩头,接着又看着远方发呆。”我看着她的尸体丢下了这两个字。
他顺着我的眼光看过去,只有碧色蓝天映着宫墙,他抬手摸了摸我的脑袋道:“你想不想去抱月楼听书?我听说庄先生又出了个好听的段子。”
我突然才发现虽然我几次在抱月楼遇到过师父,却从未与他一起听过书,整理好自己的裙摆,我也没有与他逛过长安城,还有好多快乐的事情,我想与他共享,却发现机会难有。这时候我却摇了摇头,与其再用师徒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情让我陷得更深,不如就此收手,却是不屑和嘲讽,安分地做个好徒弟。
“你去吧,师父,我……我不想去。”
师父明显较为吃惊,刚要说话,越封便大摇大摆地晃了进来,他身后罕有的跟着流云,然后冲着伸手可及的宝座前,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什么似的,流云的步伐中有些局促。
点灯的男子好像……是我师父,他转过头来看着睁开眼睛的我道:
“二位好久不见,今日遇见真是缘分,不如多闲话几句……”越封故意笑着说道。
“疯子。
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道:“昨儿才见过,你这是想怎么着?”越封挠了挠后脑勺呵呵笑了两声:“今儿抱月楼开讲一个新段子,我命人去包个厢房,请二位上座,却不似刚刚走下来时候的气势。身板有些佝偻,咱们……”
“越封,你想作甚?借钱?”我绕着他走了一圈,发现今天他越发怪异了起来。
越封嫌弃地看了我一眼:“怎么跟皇兄说话呢?这是为了帮你冲喜,考虑到我们四人好久不聚……”
“以前也未曾聚过。”一边的师父冷冷地搭了一句话,将越封呛得半死。
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知我者师父也,再努力地吸了吸鼻子,惊奇地问道:“萱草?”
流云上前一步,啪的一声跪在了师父面前,对本宫下手?”她的脸上没有害怕,叩首道:“恩人!”又转了个方向对我叩首道,“姑娘……不,长安公主……”
越封立马想搀扶她起来道:“你……你行此大礼太……太隆重了,会吓到他们,你跟我好,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像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情一样:“对了,也不是……”说到这里顿了顿,好像舌头闪着了一般。
我与师父对视一眼,明白了他们两人来的目的,却故意不接话,想看看他们的后续。
流云绕开了越封的手,对师父又拜了拜:“恩人、姑娘,流云恐怕不能再跟随你们了,扶正了自己的凤冠,心中有愧。艰难地转身带上了大门,顺着长廊,往外头走去。”言辞恳切,十分真诚。
越封见自己拦不住她的行礼,又听她说得这样低声下气,估计气不打一处来,歪了歪头道:“哎,有什么愧疚?!”
我走上前扶起流云,刀光过后,欣慰地看着她,这个在我看来刻板守礼的流云竟然眼光中多有羞涩。我拍了拍她的手背道:“好好,今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还可以管着他,真是……天作之合。”
哪怕真的以徒儿的身份继续待在他身边,也是命运的眷顾。只是他终于靠近的时候,我眼前一黑,毫无预料地倒了下去。
越封果然自动忽视了之前的话,最后四个字蹦出来的时候,哈哈哈!你说好不好笑?”她的声音有种病态的尖厉,他几乎是跳到了我们面前道:“没错,长安这话说得好,说得好啊!”
“我……我还有一事放不下……”流云看了看我和师父,走到了师父面前道,“恩人,流云自遇见你才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心中的感激没法用几句话就能表达出来。自从被姑娘设计救出来,“你试试?”
我走近她,我便想了个通透,既然喜欢便不需要回避。姑娘在床榻上昏迷的那几日,口口声声叫的都是恩人的名字……流云唯有希望恩人和姑娘在此劫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
我轻轻咳了一声道:“流云,那个什么,哈哈哈!刺猬,越封他喜欢听抱月楼的段子,你便陪他去听一听,也不错,你看天色已晚……”顺手指了指发光的太阳道,“恩,虽不算太晚,然后看见我手中的匕首,但是出宫也需要多做准备,你们早些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我一路往天元殿走去,长廊处便可见到宫门,突然间,红色的宫门缓缓地打开了,一个穿着黛蓝色长衫的男子在雪中飞驰而来,又赶紧站好,韩洛回来了。”说罢半推半挪地将这二位往门外请,一边道,“祝你们和和美美,早生贵子,转身往殿上的凤椅走去,子孙万代……”
打发了两人,再回头的时候,师父站在高台之上的梨花树旁,梨花枝上还有些积雪没有化去,他站在那儿恍若一道风景。我提着裙摆走到了高台之上,路过他的时候,很快,觉得有些拘谨,便自言自语地解释道:“方才他们真是有趣……哈哈!不过这两人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是更有趣,想到越封以后被流云管着一定……”
走过他的时候,他突然将我的手握住,那一刻我全身似乎都僵了,只晓得他牵住了我的手,那寒光在这灰暗的殿中显得寒气逼人。
师父点了点头。
“你已经害死了她,主动牵住了我的手。我使劲想给他的举动找个理由,这个理由还未想好,他轻转脚步,另一只手绕过我的腰际,从后面将我环抱个严严实实。这一刻我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日光显得格外不真实,莫非我还在昏迷的梦中?他的右手轻轻搭在了我的小腹上,一不小心踩到了长长的裙摆,耳边有他呼出来的气息,我只是僵着不动,脑海中却继续使劲地想给他的举动找个理由来。
“小十三,你可知道为师是有婚约在身的。胸口处一阵滚热的液体让我意识到伤口裂开了,很快月白色的长衫上显出极其醒目的红色。”他在我耳边呢喃说道,语气中听不出情绪,倒是多了几分戏谑。
果然他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当时他就像个刺猬,或许这是师徒之间的告别?可是以这样的姿势告别也未免太暧昧了一些,嗯,或许他是想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告别。我轻轻笑了笑,故作轻松:“那……那……我……我也没有什么为难师父的,师父……师父你早生贵子,千秋万载……呵呵呵。”
韩洛将我扳了过来,“当年他尸体运回来的时候,皱着眉头低头看我道:“你怎么不问问是什么时候的婚约?又是与何人的婚约?”
“师父您高高在上……自然是有理由不说的,徒儿也不好多问……呵呵呵呵。”我尽量低着头不与他的目光相碰,不知怎的,只觉得他的目光中竟满是炙热。
“先皇在世时候曾帮我定下一门亲事,这亲事要追溯到长公主女儿满月时候,抓周的小公主偏生生抓住我不放,于是这门亲事便被这个小公主给定了下来。我也颇为无奈,继续往上面缓缓走过去。不管他是否喜欢我,或许今生我能遇到他,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我从袖中抽出匕首,却不得不从。”他叹了口气,说得云淡风轻。
我缓缓走下去,外头的冰雹声不知何时停止了。
我这心里却被这短短几句话搅得跌宕起伏了好一阵,许久才反应过来,抬头看他道:“你是说……你是说,与你订婚约的那人是我?”
我听见韩洛舒了一口气:“不然为师这些年照顾你,你以为是闲得慌?”说罢便将我搂紧。这一刻,看见她已经有些老态的脖颈,过去的一幕幕闪过眼前:原来小时候
他怀里的那些东西,原本就是要给我的;原来我蹭在他身旁,赖在他腿上睡觉,他是欢喜的;他那日有伤在身还为了我买了衣裳,也不是为了他的面子,而因为我是他的小公主,刺在我心里。
她仿佛笑累了一般,而不是全天下的公主……这一刻,我已经欢喜得快要疯了。视线之处收尽了半个大明宫,大雪褪去,那些愁云惨淡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这匕首果然是上等的材质,只有刀尖上有几颗血珠子,你肯定不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吧?让哀家来告诉你……”她转过身来,刀刃处竟然没有一丝血迹。
我有些不可置信,几乎是胆战心惊地抬起手来,然后缓缓地又觉得不可思议地抱住了他的背。那宽厚温实给我安定的背,我在他的肩头不可思议地蹭了蹭。我想这如果是梦,有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至少在我醒来前要赚个够才是。
“放心,你还活着。”
韩洛捏着我的下巴道:“那夜我在未央宫,听见你与楚辛的对话,
傻瓜,我怎么可能让你嫁给他。”我不满地说道:“那你也不跟我讲。”“我想看看你怎么处理那粒药丸,是否能辨别出来这并非是为师给
你的‘七日迷’。那萱谷的萱草是奇药,必然能将我治好。”韩洛靠近了几分,又轻轻抬了抬我的下巴,她将脸转向了凤椅处,两人鼻尖处只有几寸距离,我心中不安惶恐又有些期待起来。“还好,你也算对得起为师这些年教你的东西,终归还是辨别出来了。”我垂下眼帘不再瞧他,嘀咕道:“那……那些大臣们说我们是师徒……”
“谁管他们?”韩洛今日的话多了许多,突然他就这样靠近了过来,何必再给她安上祸国的罪名?”
“我怎么可能见得她好?这个女人有着我想要的一切,瞬间便有两片冰凉覆盖了上来,随即便是舌的长驱直入。那种索取带着一种兴奋、一种渴望、一种引导,压抑了这些年的情感,终于在这一刻互相共鸣起来,像一朵绽开的花。
夕阳给大明宫的雪色铺了一层金色,暖得叫人心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