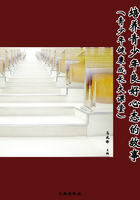一天放学回家,奶奶把我叫住了,她要我坐在她的面前,她背后是那张让香火熏得黄黄的毛泽东同志的脑袋图片,嘴边一粒痣。我知道奶奶有两个多月没给主席上香了,主席早就不食人间烟火了。
屋外不时传来锣鼓的声响,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咚咚哒!撒欢的羊蹄子似的。屋角的广播欢天喜地地大喊: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奶奶手上拿着我家仅有的那把剪刀!我愣了好一会才明白奶奶要干什么,赶紧把左袖捋起来,左臂呢,直直伸了过去。
可奶奶却把剪刀放下了,伸过瘦干干的右手,摸摸我的头。她抬头望了望屋外的天空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孩子,再忍几天吧。”
说完站起身,拉着我的右手,把我牵到了房间里。
我家房间里有一块老镜子,这镜子是奶奶的嫁妆,可它实在太旧了。我五岁那年批林批孔,红卫兵就曾冲进房间里来验证过它,可是却懒得下手,摆摆头就到别人家继续破四旧去了。
奶奶说:“你仔细看看自己的脸,看看你的头。你还小,你不知道一个人活着有多难。而且,你和别个孩子不一样,你打死不回头。我没了儿子,可我还想要孙子。”
我这才发现我头顶心上有一根毛,直楞楞地冲着天,好像对天空很有意见。
可是我刚刚再忍了十几天,奶奶就咳倒在床上,咳着咳着就不咳了。她为什么咳?还不是饿的。等我妈来回走了六十多里路背回一袋番薯针时,奶奶的手已经凉了。
奶奶是全公社第二个火葬的人。第一个是原民国的县委秘书,因为亲戚都死光了,只好火葬。奶奶呢,是因为我爸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全搬给了人家,也只凑够火葬的钱。
送奶奶走的时候,我哭了个一塌糊涂:奶奶走了,谁管我的左手!
奶奶很快就回来了,不过已经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骨灰盒,黑漆漆的。大哥把盒盖打开了,让我用右手摸了摸白白硬硬的奶奶,奶奶的骨头又硬又白,剪刀刃一般,刮手。
突然明白我该干什么了!
我冲进房间里抓起剪刀,挑进去,嚓!
我用左手把那块木板狠狠砸进了正旺着火的灶膛,噼噼啪啪,它怪叫着就烧起来了。
我还能干什么?我一头扎进了望不到边的麦田里,一边跑一边疯了似的大叫起来:嗬嗬嗬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