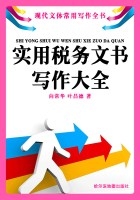老校园连个看门的老头也没有。围墙倒光了,校门还四四方方地站着,显得荒唐,紧张,甚至有点猥琐。实验楼垮了半边,教学楼、办公楼好一点,不过窗玻璃都不见了,只剩窗框子在微风里折腾出一点点动静来。教学楼的琉璃顶漏得到处都是窟窿,椽子不三不四地长在风里,楼脚遍地破砖头碎瓦片。当年为了修这屋顶,听说学兄学姐们把全城的庙宇都掀了。芦苇长到二楼的窗口,似乎还要往上长。
校道两边都是棕榈树,长疯了,高到天上去了。那是家丽她们大一那年植树节种的,想起来了,那天阳光好得离奇,暖洋洋的,呵在背上,像一千只小爪子轻轻地挠着你,人酥了一半。当家丽把树苗放到坑里时,高常青凑过来,埋着脑袋往坑里填土,手忙脚乱,几次把土填进了自己的布鞋里,家丽差点笑岔气,后来还是欧奋强拉开了他,三铲两铲,解决了。欧奋强拉开高常青时顺手给了他一只水桶,高常青却不知如何是好,提着桶站出丁字步,眼睛盯着欧奋强的手,发呆,脸红的像烤熟了的细头虾。那时高常青还没长开,像根没抽穗的野稻子。家丽梳着大辫子,干活时总把辫子绕在脖子上,家丽的脖子又白又长,像天鹅,大辫子绕上去,黑白分明,让人的眼睛没处躲闪。家丽在阳光下笑起来,就像一朵着了春风的野花。
日头贴在山顶,一抹弱弱的阳光挤过山凹罩在校道上,校道正中,一只野猫正在扑腾棕榈树的影子。野猫黑,皮毛亮得像一匹缎子,腰长腿短漫不经心,根本不把他们两人放在眼里,自顾自玩得不亦乐乎,仿佛打铁的嵇康,一不留神来到了二十一世纪。
校道上到处是裂缝,野花钻出水泥来,开野了,黄的红的白的,虽然已是傍晚,却还精神十足,像一群吵吵嚷嚷的少女,眼睛都看花了。
高常青跪在地上挑出一朵黄的,金子一般颜色,小心翼翼摘下来,叫家丽侧过脸去,轻轻别在家丽的右鬓角。他的鼻息呵在家丽耳垂上,家丽眼眶里顿时冒出水来。
高常青伸出手来:来吧。家丽很听话,抿着唇把指尖探出去。高常青急忙擒住,扯过来,转身踩着校道上的野花向校园深处飞去,一边飞奔一边仰脖大喊:“陆家丽,我爱你!”
野猫吃了一惊,喵喵叫着扒上了树梢。
家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飞呀,飞,上气不接下气。家丽张开了嘴,却没发出声来,因为没想好词语,于是边跑边笑。家丽没想到,自己还能跑得这么快,一直跑到后山脚下,还不大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