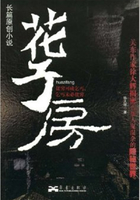它破败
它空无一人
我嗅到了我点燃的清香
我看到了花木上拂过的冷风
——独化
那几天兰城被春天里惯有的沙尘笼罩着,于是我住在了山上。山是兰城空气质量恶劣的罪魁祸首,它们裹挟了这座城市,让风不能有效地驱散各种浑浊的废气,使得废气与尘埃悬浮与天空之上,成为一个巨大的盖子。这一点我在山上看得分外清晰和轻松。清晰是因为高度——那个巨大的盖子如今在我的脚下,将我的兰城笼罩在一种灰心丧气的情调之中。轻松是因为了这种隔岸观火的姿态,那种灰头土脸的生活仿佛与我无关了,尽管它依然是灰的,但是蛰居在山上的我向下俯视,它们就成为了情调。所以每到春天,只要我还在兰城,就一定会躲到山上去。这种暂时的躲避与虚拟的逃离,总会令我的情绪进入到一种写作的状态中去,充满了臆想的热情。
那一天傍晚,我从山上招待所的房间里再一次俯视兰城,看到一个人从那稀薄的灰色中艰难地露出了脑袋。他沿着山路而来,渐渐清新的空气似乎令他张惶起来,他在停下来喘息的空隙,不时地茫然四顾,并回身对着盖子下的兰城无限遥望。他一步三叹地走着上坡路,渐行渐近,成为一个白暄的胖子。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辨认出他——因为现在到处都是白暄的胖子。直到我看清楚他肩头斜挎着的黄色书包时,他才变成了我的朋友独化。毕竟,现在挎这种布书包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更多男人肩头晃着的,是那种粗糙拙劣的电脑包。我遥望着独化,嘴角不由得咧上了笑:呔,你这厮何以如此诡异!
我住在山上的日子里,很少有人造访,所以独化的到来在我眼里便有种梦幻般的虚假。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里,浑身的肉都跟着喘息一同起伏。他问我:你的小说写好了吗?我说还没有,如果兰城的春天总是被沙尘所笼罩,这部我在山上写的书,就永远不会有结尾。他定定地看着我,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笑起来:呔,你这厮何以如此诡异!放肆的笑延缓了他恢复气息的过程,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成为那个我所熟悉的气定神闲的白暄胖子。平息下来后,他问我,那么,《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写完了吗?
《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是独化一首诗的题目,我曾经对他说过,这个题目更适合成为一篇小说的名字,事后我也尝试过完成它,但它却是困难的。因为它已经属于这个白暄的胖子,而这个白暄的胖子是真实的——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他妨碍了我虚构的勇气。更加要命的是,圆通寺在独化那里也是真实的——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真实,它矗立在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上,而那个具体的位置我却从未涉足其间。于是,这种双重的真实,成为了一篇小说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没有把这首诗兑现为一篇小说。可是现在,在兰城的山上,某种如同春天一般蠢蠢欲动的情绪却让我对独化郑重其事地说道:写完了,它已经是一篇出色的小说了。
因为少有人光顾,所以我的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如今独化占据了它,我就只有斜躺在床上,看他从那只黄书包里翻出的新诗。它们严肃地打印在白纸上,等待着在我的眼睛中成为诗。翻过几页后,一张旧照片从中跌落在我的胸口。照片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他神情仓惶,在一片西边的晚霞中忧伤而又惊骇地注视着镜头,注视着我。我问独化,他是谁?独化漫不经心地说,是我,少年时期的我。我有短时间的怀疑,因为,我不能够把照片上的苍白少年和眼前这个白暄的胖子联系起来,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山上和山下,有一个巨大的盖子横亘其间。后来我仔细端详,终于确定了独化没有开玩笑。照片上的少年的确是他,那只黄色的帆布书包就是确凿的证据——它同样斜挎在少年的肩头,连上面红色的五角星都同样的斑驳。一瞬间,我在这个少年惊悸的注视下获得了力量,我知道《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已经成为了小说。因为,所有苍白少年的神情都是一致的,就像那只黄色的书包一样确凿,它的真实大于物理与地理的真实,它是无可置疑的,哪怕少年们最终都成为了白暄的胖子。
晚上我们挤在那张单人床上,独化庞大的身体挤占了太多的空间。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叙述,因为我叙述的故事就是瑟缩的,它不舒展,尽管它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故事,而成长却是一个“舒展”的姿态。
又是徐未?看来你是跟我虚构了,你小说里的女人都叫徐未。独化对我叙述的真实性不屑一顾。
不是虚构,它是真的,听完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的小说中总是以徐未来命名女人。我认真的纠正他,不想让自己的叙述在一种虚假的前提下展开。
那是一九八三年。具体到我的个人阅历,那一年代表着我十五岁,写《蝇王》的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所以对此事我记忆深刻。春天里,我在工厂做行政干部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了她的同事徐未,只身前往南方——我的父亲在一次长途追捕罪犯的行动中负了伤,躺进了南方的一所医院,母亲需要去照顾并且慰问她的丈夫。
宣传女干事徐未,以一九八三年的审美标准去衡量,是一个属于比较怪异的女人,年纪大概已经接近三十岁了,脸和脖子几乎是一样的比例,好在不是由于脸特别的短,而是由于脖子特别的长。脖子长到和脸一样的程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会令人面对徐未时总是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中,你会为她担忧,担忧她的脖子会随时“卡”地一声折断,而向下跌落的脑袋一直会低垂到了腹部。这种幻想出来的情节总是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它令我紧张,在面对徐未时总有些忧心忡忡。我想,徐未长脖子造成的这种紧张一定是普遍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杞人忧天,因为徐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母亲把我托付给她。我叫她徐阿姨,她却不让我这么称呼她,她说,叫我徐未好了,就叫我徐未好了。我尝试着这么叫了一声,突然就被巨大的羞愧压倒了。没有任何道理,当一个成年女人的名字从我的嘴里轻吐而出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眩晕感,有种羞怯混在快慰中,居然却成为了愤怒,令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滋味。所以我依然叫她徐阿姨。但是,我会在心里面不时地唸叨一声“徐未”,时而是低徊的,时而是响亮的。这种反复默念一个女人名字的状况,在一个少年的心中产生出微妙的反应,“徐未”这两个字成为了一个咒语,被反复强调的过程渐渐蕴涵出一种古怪的情绪,它令我柔情似水又惴惴不安。于是,我必然地对这个名字的主人产生出好感——我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吗?或者,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独化不置可否地哼一声,他说,接着说,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