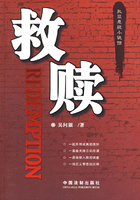暮秋,几个外来商贩深夜点火烘烤受潮的货品,不小心引着了杂物。浓烟炝起,大火烧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烧穿了楼板和紧邻的两间平房。
及南是这起火灾事故中两个死亡者之一。
这是西渡得到的确凿的消息。
伊春冬天的晴朗下午,弗里斯兰花店一地藤萝和花叶的影子。及南埋头修剪着手里的玫瑰。刚脱过水,微微带着潮气,桦木桌上这样的玫瑰还有几枝。阳光穿窗而过,失掉血色的花朵,及南,都有了暖暖的金色。
一个时间停止了的错觉。
西渡现在想得起来的也就是这些。他站在一棵树下,半个身体支着树杆,偶尔抬起目光,树杈像一堆摇动的桅杆,叶子从上面刷刷飘落。
是他从求职人群中领出来及南的。
五六年前的一个早上,已经初夏,天还是很凉。劳务市场照例喧闹纷杂,一有目标走近,等候的人立刻一拥而上,声音也是吵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及南短头发,穿黑色裙子,远远望过去,又坚定又茫然,那样子不知为什么让西渡想起梦境里见到的家。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不知不觉走了过去。
大多数人瞟了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西渡已经走近她,倒挤过来几个人,他不知道怎么拨开面前盯紧的目光,就在看住她垂着的手努力靠过去的时候,很意想不到的,这些人因为新的目标轰地散开了。
西渡有点窘迫,几分钟前,他甚至想拉住她。
“我的花店,弗里斯兰花店,如果你愿意,现在需要一个人。”
“好。”
“时间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中午不休息。”至于报酬,他思忖一下,说了个数字。
西渡记得她犹豫了一下,结果说出的仍是一个好字。对这个简略至极的回答,西渡无话可说了。
两个人只是一前一后走,穿过伊春熙攘的大街。阳光渐渐钻出来,西渡额头无端迸出几粒汗水,及南始终跟在他身后一米左右,每次回头都看到她头发稀疏表情平淡的脸,想说的话就又吞了回去,直到走完四条半街的路程。尽管好几次因为人行道的红灯,他们不得不停在同一道斑马线上。
弗里斯兰吸引过不少行人,等他们推门进来,发觉和附近叫玫瑰花行或者百合花的花店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花还是那些,基本出自郊区育花大棚,有空运来的,数量极少,但也绝非稀有和罕见。
西渡一直想说,关于弗里斯兰荒岛,重回弗里斯兰的女人站在船头迎向暮色中土著男人的电影画面,他的花店,却始终找不到机会。及南除了重复和反问他的话,以确定自己一天需要做的事情,什么也不多说,整个下午就在局促中过去了。
传道书说这世界没有新的,对于西渡和及南,花的运送到可以算作一天的起始,无所谓新与不新。上午总是忙乱得一塌糊涂,修剪,整理,清扫,随时有人来,随时上前介绍应对,依照要求扎好花束花篮,联系雇佣的车夫外送,逢到休息日或者吉日,一辆结婚花车足够他们两个忙上半天。
及南是勤谨的,记性也不错,西渡于是很高兴,为她的灵慧,同时也发觉到她的沉默。
他不知道她在伊春的经历。清早从对面路口出现,穿过马路走进来。晚上走出去,穿过马路,再消失在对面路口。
基本不主动说话,镶着两层玻璃的窗口对于她似乎有极大的魔力,一遇空闲,十之八九站在那儿,习惯用一只脚站着,另一只勾着站住的那条腿。奇特的姿势。有时她唱着什么,细而坚韧的声音,对着窗外灰色建筑之间激流一样的喧闹。尽管断断续续,西渡还是听出了大致的旋律。
等听说这曲子原来叫黑色星期五,西渡吃了很大一惊。“这曲子不好。”他果断地说。
“据说听过的人很多自杀了。”
“音乐史上有这个传说,一个匈牙利男人创作的。以后不要听。”
“其实听多了也没什么。”她侧向一边的脸突然扭过来,带着微微惶恐的神情。
西渡第一次发现及南性格当中怪异的东西。她好像受过损伤,又被神秘的力量支撑。以后,连这没有歌词的曲调她也不再唱了,窗口的背影无声无息,如果他问累了吗,就用很快的速度转过头,笑一下,表示不累,接下来回到桌子后面,埋头翻看几本有关花卉的书,天知道她后来做的那些干花是不是就从这学来,总之某天下午西渡外出回来,看到一把颜色古怪的花束。当时她不好意思地说用隔过两天的玫瑰脱水再风干做成。因为另有一种质朴,很快吸引了不少正走向中年半路的女人。对西渡的赞赏及南没作多少解释,他给她加薪,她态度还是淡淡的,谢过他,并不显得如何高兴,也并不因感激就与他有所亲近。
西渡有时难免疑惑,她丈夫呢,她从来不提,也从不提起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偏爱黑白两种颜色的衣服,不多的几件,式样简单,质地很好。习惯说我自己可以,拒绝任何人善意的举手之劳。
“不再换个环境?”西渡总是觉得她应该有更稳固的职业,而不是一家琐碎的花店。
及南摇摇头,又笑起来,说,“这儿很好啊,这么多花。”
他想她一定努力过,只是不大会诉苦。
及南的沉默,西渡已经很习惯了,也习惯自己刻板的一天流程。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花店,一天两次去“十字坡”吃饭,这家由两个江苏人开的饭馆专做淮扬菜,还能合他的口味。他们有一味招牌菜要用到玫瑰和菊花,西渡经常送一些过去。
除此就是“月光”酒吧了,它原先只是两个高层建筑之间的过道,后来才被改装成酒吧,采用了全玻璃钢的结构,通体透明,西渡留意过,果然是有月光照耀的,而且因为和马路相隔很深,坐着的人就有了点半空的意味。月光的调酒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台湾人,很有一手调酒的技艺。西渡关了门经常会去坐坐,喝酒,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