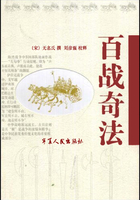我叫鲁拙。
鲁,是鲁蜀的国姓,我的父皇,是鲁蜀传承的第二十八位君主烨帝,国号:“墒”。
而我的母妃,则是蜀国第一绣娘。
相比于叫她母妃,我更愿意叫她作娘亲,似乎只有这样的称呼,才能配得上娘原本的平民身份,才能让我,于那冷寂的宫中,体会到一丝人情温暖。
娘亲并不绝艳,与蜀宫中那些倾国倾城的妃子相比,她只能勉强算得上是清秀。以这样的姿色,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在喜新厌旧、贪恋美色的父皇眼里,只不过是露水浮萍,过眼云烟,在寥寥数次侍寝之后,便会落得个老死宫中的命运。
娘是不幸的,但同时,她又是幸运的。在父皇未曾厌腻她之前,她就怀上了龙儿,也就是我,鲁蜀第二十八位皇子,众多皇子公主中,默默无闻的一个。
得知有孕的那日,娘亲被封了莲妃,那个时候,她还天真地以为父皇对她的宠爱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可是短短几日之内,父皇的兴致,就从她身上,转到了另一位美人怀里。
自我懂事开始,最常见到的情形,就是娘孤单一个人,坐在芙蓉轩回廊的滴水亭里,遥遥向着宫门的方向眺望。
我知道娘在等父皇,可是,我从来没见过父皇,传闻说他只在我出生的那一日来过一次。
阳春仨月,天气仍有些早寒,淅淅沥沥的小雨连绵不断,打得亭外池塘里的荷花莲叶簌簌作响。
在这样如烟如雾的雨幕中,娘最爱的事情,便是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述她当年与父皇相识的经过。
那一日,也下着如丝般的小雨,娘亲做了活计,撑了船去鲁蜀第一布庄交绣品。
一路飞奔,赶到布庄门前,娘亲刚收起赭黄的油纸伞,便撞进了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中。
那个人,自然就是父皇了。
看多了浓妆淡抹的莺莺燕燕,乍一见连看他都要脸红的小家碧玉,父皇当时的感觉,必定是耳目一新。在得知这个看起来娇小清丽,像莲花般羞涩微笑的女子,就是手艺好到专门分担宫廷绣品的布庄第一绣娘,他不由有些惊喜。
接下来的故事,便落入了俗套。父皇专门为娘亲举办了天下第一绣品大会,而娘的一幅雨后初荷图,毫无悬念地夺得了魁首。
在天下第一绣娘的光环落在娘亲头上时,她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父皇的女人。
女人,总是喜欢回忆那些美好的过去,特别是在这高墙深院的皇宫中,回忆,几乎成为那成百上千女人活下去,并用谎言安慰自己的精神支柱。
只是这贴药,虽然管用,却也是慢毒。
时间,永远是残酷真相最好的验证者!
帝王薄情,最苦的,便是那些过气的妃嫔。与娘亲在宫中生活十几年,我看过无数因为空虚寂寞而疯癫,而心性扭曲的妃子,所幸娘与她们不同,娘还有刺绣,还有我……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几年,十几年过去,娘亲已经习惯了没有父皇的日子。她仍然喜欢坐在芙蓉轩的滴水亭中,只是抱不动我,也不再向宫门眺望。
娘亲是有子嗣的妃嫔,那些宫人虽然刻薄,但也不敢太过克扣。本以为我娘儿俩的日子,会一直在这狭隘宫墙内平平淡淡地度过,却不料天降横祸,一场他国的来访,打破了我二人相依为命的美好时光。
那一天,我永生难忘!
依旧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天空却透着一股不正常的灰,沉闷压抑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已有些破败的滴水亭中,娘亲绣着为贵妃娘娘置办的富贵团圆枕幔,我则拿了竖箫,为她吹奏新学会的《芙蓉谣》。
明亮的黄色那样突兀地出现在宫门之外,在如油画般的暗色背景下,夺目得有些刺眼。娘亲与我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上前去接驾,将那个姗姗来迟十数年的男人,与他身后的一众妃嫔侍从迎进了芙蓉轩中。
原本宽敞的屋子,因为多了这许多人,难免有些拥挤。这样阴暗狭窄的环境,身为一国之帝的父皇自然不愿多呆。伸手召过一旁的使臣,他向他示意了我的存在。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父皇。
这个男人,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高大威猛,器宇轩昂。过多沉溺于酒色,让他两眼虚肿,肚腩突出,根本不是娘亲所说那般风流倜傥的模样。
我有些失望,而对于众人都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又有些奇怪,只是,当时才十二岁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我和娘的,是即将骨肉分离、再难相见的惨剧!
时至今朝,天下六分。
东卫西晋,与我鲁蜀相隔甚远,并无交界;南宋燕齐民风纯朴,素来与鲁蜀交好,互通有无;只是那日里来的使者,隶属于与鲁蜀交界最广的北楚。北楚地大物博,帝王亦野心不浅,乃是鲁蜀帝王第一要防范的对象。
当然,仅仅是防范而已。
西晋土地贫瘠,人民多彪悍,那几年恰逢雪灾,饿死冻死了不少牛羊,北楚边陲,便不时有暴民动乱发生。
借着二国也许要开战的借口,北楚使者专程前来的这一趟,便是要父皇答应:在任何时间都会以友邦的身份援助北楚,而不是落井下石,趁乱再掺一脚。
口头承诺当然好办,可是要楚王相信,鲁蜀便非要拿出些保证来不可。
这抵押,不是物,而是人,也就是众位大臣妃嫔,与父皇亲口所说的,被疼爱无比的我了!
就这样,当时还懵懂无知的我,没能完全弄明白情况,就被北楚的使臣带上了回国的马车,而娘则在与她交好的贵妃娘娘的寝宫外,跪了足足三天三夜,也没有换来一个能够亲见圣颜开口求情的机会!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被众人淡忘的我母子二人,能够再见天颜,完全“得益”于那“面慈心善”的贵妃娘娘!为求保住她的爱儿,我的十四皇兄,她向父皇提起了我这个被淡忘的皇子,而“二十八”这个“吉利”的数字,也获得了众人交口一致的称赞,认为我,是代替诸位有为的皇子们,被送往北楚作质子的最佳对象。
此去经年,漫漫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