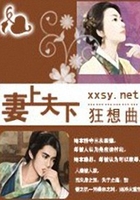不到三分钟,房门打开,小梓穿了短裤和背心,汗涔涔地走了出来,又飞快地消失进洗漱间。过不多久,他甩着湿漉漉的头发,躲着黎海的注视,走出洗漱间,脚跟抽筋了似的,咯噔噔地奔到沙发上,把抱枕扯过去,蒙住那个大脑袋。
“你疯了!像什么话嘛!”黎海过去一把抢走他手里的抱枕,在小梓高高跷起的小腿上,狠抽了一下。“那个李什么倩把你搞疯了吗?啊?”
“哎呀!她叫李锡倩!”小梓侧躺下来,用头撞了撞沙发靠背,又扑腾坐起来,梗了梗脖子,上齿咬着下唇,眼睛上翻着,一眨不眨地望着黎海,用一种忧郁又恼恨的眼神地回敬黎海说,“抗议!她哪里不好了嘛。总比你那女朋友好——口臭女王。”
“荒唐!”
“你要怎么样嘛?说啊你说啊!打死我?来呀黎大侠!来打噢!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嘻!”
16
黎海错了。只能说,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隐瞒什么,那是很简单的事。黎海的智力之所以被蒙蔽,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觉得小梓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再夸张也夸张不到哪里去。但小梓这些天来的秘密作为却夸张得令黎海惊骇。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他们正在家里睡懒觉,敲门声响起来了。黎海脑子混沌着打开门。出现在他眼前的是高矮胖瘦不等的四个陌生男人。“这个ID号是你的吗?”年龄稍长的男人站在最前面,向黎海亮出一张卡片——说是一张纸也可以。上面是一行结实的数字。黎海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后面那个黑壮的圆脸小伙补充了一句,“就是说,你家里是用这个号码上网的吗?”他还冲黎海笑了笑。黎海把床头柜上的眼镜拿过来,仔细看了看。那的确是他的上网号。他认可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年龄稍长的那个,显然是组长,或是他们的“代表”,向黎海亮了亮警官证。
四人鱼贯而入。接下来,他们言简意赅地跟黎海陈述并核实了一些情况。黎海听到中途才明白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确切地说,是最近大约半个月来,他这个上网号码成为网络色情表演的工具。黎海清楚,这个表演者当然是小梓。他竟然应聘成为某个色情网站的值班“男优”,那天下午被黎海撞见的那个场面,不过是小梓的一种工作状态而已。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电话,都是五湖四海的那些小梓在网上认识的具有恋童癖倾向的无聊女人打来的。最近的扫黄打非,公安局的网络侦察部门侦破到那个色情网站,主办者和替该网站服务的所有人员,在近几天里,已经和正在落网。
小梓,这个混账东西,他可真行。原来这就是他自信满满的挣钱渠道。这就是他的未来,他的狗屁李锡倩,他的房子,他送给他小姨的红色跑车。黎海气愤而惊惧地坐到沙发上。四个陌生人紧随而上,左右站在黎海身边。他们说话的同时,关紧门的里屋一点动静都没有。但黎海知道,小梓已经醒过来了,并且就躲在门后偷听。如果他没醒过来,里面不会那么静。黎海脑子乱了,无法思考对策。那男人开始对黎海作最后的核对:
“家里几个人?”
“两个……多数时候是一个。”
“都上网吗?”
“不!就我一个人上。”黎海很奇怪自己混乱的脑袋,此际,为什么突然这么条件反射地护住了小梓。“那还是个孩子,我坚决不让他上网的。”
“哦!”“代表”睿智的眼神迅速落向里屋门。“可以打开门,让我们看一看吗?”
黎海的心变成了开足马力的发动机,但不得不打开了房门。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床上空无一人。警官们只潦草地向里面打量了一眼,退回客厅。黎海狐疑地关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他看到床下的象形枕头。看来小梓躲在下面。
“那孩子不在家?”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黎海。
黎海木然道:“出去玩了。”
回答完,他匆匆望了一眼那象形枕头,猛地被一种由愤怒、自责、伤感、痛苦复合成的情绪击中了。他狂躁地关了房门,推了身边某个警官一把,撇开他们,大步走了起来,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你们想干什么?警察有什么了不起?乱抓人吗……”他像个发高烧的病人那样胡言乱语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滚!滚开!你们……”
他们面面相觑。都笑了。“代表”拿出另一张“纸”给黎海。黎海仓促看了一眼,是一张什么单据。他挥手就打飞了它。
黑壮的年轻人骂了句什么,上前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黎海的下巴。另一个人扭住黎海的手,他的手凉了一下,他低头,看到一副手铐。
17
黎海从来没被收容过,也从未设想过会进入这种地方。对他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他都要崩溃了。恨着自己,恨着别人;也许不知道在恨谁。在收容所的这个夜晚,他的情绪低落到极限。他做了一堆梦,其中两个被准确记住了。第二天一早,陈珏带着钱来“赎”他时,他正待着幽暗的禁闭室里,惶惑地回味着那两个梦。
第一个梦:黎海梦见父亲失踪了。母亲站在安庆街头,跟他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以及他,回顾父亲失踪时发生的一件怪事。母亲说,父亲失踪的第二天,他单位来了一男一女,请母亲不要担心,说父亲只是去沈阳出差了。母亲却将信将疑。她敏感地认为:父亲有可能被人谋杀了;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这桩谋杀案的主谋。
第二个:黎海梦见,他回到中学操场。集合哨响起,同学们开始列队。个子矮小的黎海抢站到第三个。有同学迅速把他扒到一边。他愤怒地跑开,向队列后走去,孤单地站在队列的末尾。
黎海想,第一个梦显然在说,父亲老了,再活也活不过多少年,同理,母亲也如是。这是否说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处于某种自责当中?他游离在亲人们无法洞见的空气里,寻找着自己的理想家园,与此同时,也逃避了作为一个晚辈、一个儿子应当尽的本分。他愧对年迈的双亲。
那么第二个梦,是不是在说,他一直被别人侵略着,或者说,他总是惧怕着别人的侵略呢?而这,成了他情绪的翻覆之源。
黎海很抑郁。两个逼真的梦搅得他魂不守舍。他情绪落到谷底。他绞尽脑汁,想弄懂它们的确切所指。陈珏在说话。她的声音响在他耳边,他听得似是而非。他们来到了常去的溢源香茶餐厅。黎海的思绪部分回到身边,他听到陈珏说:“……你多大岁数啦?怎么越活越不懂事了。人家查到你了,找上门来罚你的款,你认罚就是了,犟什么犟啊?你看你把事弄得……收容所里舒服吧?这回的体验很特别很爽吧?真是个傻子。要不是我,你看你怎么收场。我觉得你怎么像个小孩啊。陈小海都比你理智。我要像你这么不理智的话,一个保险都卖不出去。你不知道,我每天出去跑保险,会遇到多少事。什么样的人都有的,有一次……”
黎海感到急火攻心。一口气淤积在胸口几百年了。牢笼在前面,他要像豹子一样冲出去。他望着陈珏,嘴唇哆嗦个不停。他拍着桌子,突地,站了起来,指着陈珏,语无伦次。
“……你……陈珏,你别在这儿自以为是了。你懂什么?什么都不懂。可你总是自以为什么都懂。你把自己想得比谁都厉害,可实际上呢?你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陈珏,你说出口的每句话都很在理,都好听得要命,可做起来,你什么都不行——你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你是真正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就是个自大狂。知道吗?我一直想告诉你一句话。现在我告诉你:除了你自己,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可笑、顽固、自以为是的女人……”
黎海斥责着陈珏。她始终盯着他的眼。她在克制,这显而易见。她用一种真正强悍的力量控制着自己,使她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之时,能屹立不倒。她竭力维持着平静的表情,做出谦和的样子,“倾听”这段看来必然是她有生之年她听到过的最伤她自尊的话。渐渐地,她由内而外、真正地平静起来。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坦然和淡定赋予她的冷静。她笑了。很有分量的笑——任多大的风暴都无法吹跑它。
“你说完了吗?”趁着黎海喘息的片刻,她及时制止了他,“如果没说完,就继续。要是暂时没想好还有什么要说,那,下次,找时间,再听你的高论。嗯?”
黎海沉默了,虚弱无比。他低下头去,听到陈珏在用一种比任何时候都完美的嗓音叫服务员过来买单。服务员过来了。她拿出紫色钱夹,检查点菜记录,和服务员讨价还价,末了,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服务员。一切,都有条不紊。
早晨的餐厅食客寥寥,不够嘈杂。不久服务员拿着一堆找赎回来。陈珏接过这些散钱,将它们撸直、抻平、叠在一起,塞进钱包。终于做完所有事,再无表演的余地。她按着小腹,优雅地,错身走出卡座。等黎海盛怒又愧疚地抬起脸,她已快速走出门口。离开的同时,没忘留下一串放肆的大笑。
18
“你才是个自以为是的东西!”
“你幽闭、自哀、自怨、自怜、自找没趣、伪善、难以取悦、不识好歹……是一堆无可救药的垃圾!”
“你非常非常无知和无趣。”
“你不过是只可怜虫!”
……
陈珏的大笑所要告诉黎海,或黎海可以借由这短促有力的笑声体会到的,便是这些话。黎海怒不可遏。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叫服务员过来,买了一个杯子。在茶餐厅食客们惊惧的目光中,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将杯子砸向地面。
19
黎海没骂小梓。奇怪,当他打开家门,看到小梓诚惶诚恐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一点生气的念头都没有。他的心情是平静的,也可以说,是空洞的。他什么也不说,径直去了里屋,囫囵躺在了床上。他觉得困,只想痛快睡一觉。小梓变得少有的懂事,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小很小。黎海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种极谦卑的力量推醒了。小梓站在床旁,欲言又止:
“……对不起!……”
黎海冲他挥挥手,背过身,重又睡去。
“我知道你烦我了……我……”
小梓的声音滞重起来。黎海想,小梓理解错了。他只是突然在这一天感觉特别疲乏,不想说任何话,他想心思空空地在床上睡上一整天,就像从前小梓未在这个家里出现,他独居时,经常干的那样。但小梓显然将黎海的沉默理解成了淡漠。他粗重地呼吸了两下,带上门,出了里屋。黎海再次醒来,是被小梓的声音喊醒的。
“我走了……喂!我走了!”
黎海飞速扭头,看到小梓背着他来湛江时的那个红色旅行包,站在门口,一脸伤感。他跳下床,去抓小梓。后者早有防备,一手握住门把手,用力扭开。在黎海尚未起步的时候,小梓已把自己关在门外。
黎海终于怒了,顺手采了鞋架上的一只拖鞋,打开门,向楼梯扔去。
“滚吧!”他吼。
拖鞋沿着楼梯骨碌碌往下滚去,小梓已不见影踪。黎海“砰”地关了门,在屋里踱步,不知道该向谁生气。他思绪混乱,懒得做任何事,便重新爬上床,似睡非睡地躺着。有一会儿,他想到了小梓——就对自己说,小梓是不会走的,这不符合他的行事逻辑。
可小梓的行事逻辑又是什么?这其实又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后来,黎海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清醒过来,慌神了,迅速出门。
小梓没走远,他坐在离黎海家约一站地远的十字路口。黎海上去拉他。小梓反手推了黎海一把。黎海烦了,瞪着小梓。他看到小梓脸上被风干的泪迹。但此刻,小梓的眼睛里已无一点伤悲,有的则是些黎海不解的内容,复杂、晦涩,也吓人。小梓就这样望着黎海,直到黎海再次过去拉他的胳膊时,一句类似烂片对白的话出场了。小梓说:
“我在这儿坐着,等你来追我。我对自己说,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可是——”他抬起手腕,向黎海扬了扬手上的电子表。“刚好,时间过去十六分钟。”
黎海又好气又好笑。小梓站了起来,向马路对面跑去,奇快无比,差点被快车道上的一辆出租车撞倒。等黎海追到马路对面,小梓已在二十米之外。天热得能叫人昏厥,阳光像少年人仇恨的目光,灼热无比。黎海看到小梓迎着密密麻麻的阳光,向他这边转身,定定站着,遥望他的表舅。黎海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表情。他整个儿僵了,感觉有桶冰水从他头顶直浇到脚底。完蛋了!他想,他已经成为一道伤疤,一道被小梓隆重刻进记忆深处的伤疤了——这就是小梓的表情要向黎海表述的深意。
黎海颓然站在那里,考虑着该不该追上去。小梓跳上一辆摩的。摩的拐了个弯,拖着长长的尾气风驰电掣般远去、消失。黎海知道小梓身上有足够的路费,当然是这些天来他自己“赚”的。他不用为小梓的安危操心,他所担心的是小梓的心思。他还站在马路边考虑着,该不该把小梓追回来。他沿着人行道往前走,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拨陈珏的电话。三次,陈珏都不接。黎海收回手机,继续走。途经步行街的入口,他的脚步被一个非比寻常的中年男人拌住了。那男人站在步行街的入口处,口中叫嚷着,吸引行人的注意。在他的脚前,是一个约三十厘米见方的灯箱。黎海不由走近去,俯看灯箱。
本人原为专业文艺团体歌手、导演、钢琴演奏员、贝司手、美工。世道沦落,本是专业演员的我遭人暗算,被迫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浪迹江湖的民间艺术家。今天,我流落到贵地,向广大爱好艺术的朋友们献艺,欢迎大家真情赞助……
黎海转看灯箱的另一个面,看到的是一则广告:
诚招女学员,免收学费,要求姿容出众,年龄18至26岁之间。有意者请致电×××××××
那男人先前在清唱庞龙的《两只蝴蝶》,现在换成了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此人长得不是一般的丑。完全可以用奇丑无比来形容他的尊容。更令人愤懑的是,他唱得太难听了。那五音不全的嗓音简直就是来自鸭子养殖场。
黎海看着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男人抖动着他的脚尖,将高亢、尖利、普通话极不标准的声音强行刺入路人的耳膜,他被这男人的自恋或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胆量震撼了。他围着男人转了两圈,开始慢慢把手伸进裤兜。终于,他找到一张很久前不幸得到、至今仍无法花出去的百元面值的假币。他拎着假币的一角,在男人因期待而迅速充血的目光中,走过去,将钱丢进其脚前的不锈钢钵子。他看到男人向他颔首,可笑地向施舍者展示他下贱的自尊。他跟男人握了握手,后退着走了,心里觉得此举无异于蹂躏了整个世界。他感到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