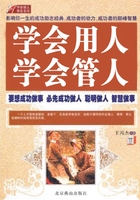12日《解放军文艺》1957年9月号刊出诗歌特辑,刊有江枫《我们挺身战斗》、肖英《右派分子的脸谱》、徐迟《我的歌》、公刘《河西行》、李瑛《时代纪事》等诗。该刊1957年10月号《编后记》说:“诗歌方面,我们在九月号出了特辑,不但集中地发表了较大数量的诗,而且极力注意到诗的质量,注意到发展其不同的风格,极力发扬诗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鼓舞建设者的战斗意志的作用,以及它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号角的匕首作用。这些努力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我们要扩大这方面的战果,准备一九五八年一月号再来一个诗歌特辑。”
14日《人民日报》刊出沙鸥的诗《脸谱种种续集》,有《冯雪峰》、《艾青》、《李又然》、《陈明》4首。
15日《文艺报》1957年第23号刊出李季、阮章竞的文章《诗人乎?蛀虫乎?》和李宝靖的文章《李白凤要歌颂的是些什么?——评李白凤的诗和〈给诗人们底公开信〉》。李宝靖文章讲:“李白凤的‘致诗人们底公开信’(《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是一篇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充满着反党的右派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许多错误论点,都是从作者的阴暗的思想情绪述说出来的。他特别厌恶和反对诗人们用最好的形容词——太阳来歌颂新时代的光明、歌颂伟大的共产党和敬爱的领袖。他说:‘在我们的诗歌中,有着不同签名而内容变化不多的歌颂太阳的诗。……过多的使用太阳这一象征不觉得单调么?’显然,长期呆在阴暗的角落里,或者和阴暗角落的气味相投的人,是怕见太阳的。”
15日《青海湖》1957年9月号刊出王浩《韩秋夫、程远反党联盟“理论家”的自白书——反右火线传单诗五则》、秀山《斥反动诗——“林中试笛”》等诗。
15日《新港》1957年9月号刊出邹荻帆《斥丁、陈反党集团》、白桦《毒菌——为丁玲画像》、公刘《粉碎章罗集团的恶性“大发展”》、顾工《他忘记了……——在党内有这样一个右派分子》等诗,编者《这一期》讲:“这期的诗,主要的都是些反右派内容的诗。许多诗人如邹荻帆、公刘、白桦等同志对我们热诚协助,是应当在此志谢的。”
20日《文学杂志》第3卷第1期刊出梁文星(吴兴华)《绝句》、余光中《浮雕集》等诗。
22日《文艺报》1957年第24号刊出阮章竞《“宇宙歌王”》、闻捷《塔塔木林画像》等诗和署名“记者”的报道《艾青是怎样“检讨”的?》。报道说:“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24次会议上,胡海珠同志代表在作协整风办公室工作的八位同志发言,揭露了艾青怎样做‘检讨’的故事。”“艾青发言中‘关于和吴祖光新凤霞的关系’这一部分的检讨和交代,完全是他爱人高瑛替他写的,不仅从笔迹上可以看出那是高瑛的字,从内容上和语气上也完全可以肯定这是高瑛替他写的。他谈到吴祖光第三次到他家时,发言稿上写着‘是在我生孩子之后’!(胡海珠念到这里,全场大笑)说到他们夫妇有一次到吴祖光家吃饭的情形,发言稿上说:‘席间大家大谈笑话,艾青听着很少插嘴,我和新凤霞谈家常。’(全场笑)……这不是高瑛的语气是谁的语气?艾青同志对党没有一丝一毫的诚意,他是以怎样卑劣的态度来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对待同志们的批评,从这里不是看得十分清楚吗?”
24日《人民日报》刊出徐迟的文章《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文章讲:“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讲他是靠国际影响吃饭的。他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的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艾青是非常骄傲的。别人的作品从来都不在他眼里(可以参看他的‘诗论’)。他对同时代的诗人都诽谤过,讽刺过,甚至对同时代的外国大诗人也在口头上散播过许多刻薄话。其实别人的诗他很少看。这两年几乎根本不看。他对整个文艺界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艾青近几年的作品大体说来分为两类,“一类是暴露了他的不满情绪的。一类是偷运资产阶级的颓废派、现代派诗风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这首诗真真是现代派诗风的走私了”。“这首诗非但没有热情明朗地描绘一个政治斗争,却反而写得晦涩难懂,引起每一个读者的许多猜测,大家像打灯谜一样。但灯谜还是有底的,这些诗句却连谜底也没有。我们要反对这种诗风。它的底细,其实我们也摸的很清楚:这种晦涩和朦胧正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派诗歌的特点,它们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有着血缘的亲族关系。二十年前,艾青曾经从欧洲带回一枝阿波里奈尔的芦笛,用它来吹过革命的歌曲。时代大踏步的前进了,他应该抛弃这样的音乐了。”“这样看来,艾青这两年有何改变?他何曾为社会主义歌唱?他写的“‘官厅水库’显得很平庸。事实是艾青这两年生活得很不正常,很腐化,很堕落,骄傲已极,和一些反党分子来往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原来问题还不在于他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而首先在于他今天能不能过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关?”
25日《诗刊》1957年9月号刊出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田间《艾青,回过头来吧!》、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等文和郭小川《发言集》、公木《恶鬼底画像》、严辰《洋奴的悔和恨》、顾工《喂!同志,你应该站起来大声发言》等诗。编者《反右派斗争在本刊编辑部》说:“本刊编委之一吕剑,编辑唐祈,是两个右派分子。”“新华社八月四日的电讯中,曾经揭露吕剑、唐祈两人的右派面目和他们的一些罪恶活动。这个电讯发表在五日各报上。电讯中提到吕剑、唐祈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先在作协召集的民盟盟员座谈会上,攻击‘人民文学’和作协的党组织。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又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开会,密谋‘公开’作协的问题。而后,按照了议定的谋划,吕剑、唐祈又在‘人民文学’的整风会上,大举进攻。他们污蔑了作协的肃反运动,还说‘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宗派主义’的,‘党包办’的,并特别恶毒地挑拨‘人民文学’编辑部和非党作家的关系。”“根据继续揭发的材料和他们自己的交代,已经证明:他们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李又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又然和吕剑、唐祈在一起策划,并供给了他们进攻用的炮弹,企图为丁、陈反党分子翻案。吕剑、唐祈已经承认他们充当了这个反党集团外围的‘哨兵’。他们的其他活动,他们和其他右派分子的关系,则正在继续的揭发中,他们自己也陆续地交代了一些。”“本刊另一编委,诗人艾青,最近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受到了严正的批判。艾青的反党言行被揭发了。他和丁玲、陈企霞、江丰这些反党集团以及吴祖光右派集团都有关系。他充当了这些集团中的联络员,为他们传播反党活动消息。一个深夜,艾青主动招待‘文汇报’记者,告诉他们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污蔑党批评丁玲、陈企霞、江丰是党内宗派主义,挑动‘文汇报’向党进攻。此外,他也说过各式各样反党、反领导的言论。”“艾青被揭发了。他的灵魂深处也是很腐朽、很卑劣、与‘诗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全不相称的。这也难怪他近年来的创作缺少革命的情绪和生活的气息,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流露了对党的领导和对党的文艺政策对抗的情绪。”“本刊其他几个编委和编辑部工作同志都积极参加了对艾青的揭发和斗争。与这同时,编辑部也积极地开展着对吕剑、唐祈的斗争,要他们老老实实、彻底地交代问题。斗争将坚决地、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田间文章讲:“在艾青的身上,原有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没有经过多少改造,而他又很怕改造;进城以后,尤其是这几年,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经常埋怨党,讲怪话,从不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诬蔑党内有些同志打击他、压制他,和党对立;他对党的工农兵文艺方针,也是不感兴趣的。终于他走上反党的道路。‘大鸣大放’期间,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角色,奔走在几个反党集团之间,几处点火。他的这些反党言行,谁能容忍?我们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有一些成就的诗人,就允许他反党,允许他生活堕落腐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丝毫没有这种权利。”黎之文章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以后,诗歌创作不论从题材上和形式上都比过去宽广了,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在我国文学艺术的花园里,诗歌开始开放了五彩缤纷的花朵。”“可是,我们同时不能不看到,这一个时期诗歌创作上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以至毒草。为了使我们的诗歌创作健康的发展,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都必须和这些不良倾向以及那反党反人民的毒草进行斗争。”“我们知道诗应该是时代的声音,应该是战斗的号角。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前一时期却出现了低沉、忧伤的调子,出现了一些带有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甚至资产阶级低级庸俗感情的诗。而这些东西在某些刊物和某个时期某些地方竟占了上风。如‘星星’诗刊创刊号就出现了一些色情的和有反党情绪的诗,现在我们知道它是被右派分子霸占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直到最近这个情况才改变的。”“发表在‘延河’七月号张贤亮的‘大风歌’,也是一首表现了反动情绪的诗。这首诗写得比较含蓄,初读的印象好像只表现了作者狂怒的情绪,但仔细一读,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真实含意的。”“‘要破坏一切’!倒[到]底他要破坏什么呢?原来是:‘庸俗的、世故的、官僚圈子’。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们总是骂新社会‘庸俗’,骂新社会到处是‘官僚’而要一棒子打死。‘大风歌’也就是企图在反‘庸俗’和‘官僚’的幌子下,破坏新社会的一切。”
25日《奔流》1957年9月号刊出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和贺力震《右派分子苏金伞的真面目》、牛星斗《苏金伞的反动文艺思想》、李书《“诗人”的秘密》等文。《我们的检讨》讲:“刊物对培养新作家负有重大责任;发现和培养了多少有才能的作者,是衡量一个刊物成绩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奔流’在‘编者的话’中虽曾提到这一问题,但在右派分子的掌握下,与编辑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支配下,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脱离省内广大青年作者,扼杀了新兴的创作力量。右派分子苏金伞认为新起的作者是‘政治上的宠儿,艺术上的无知’,对培养新作者进行恶毒的诬蔑说‘刊物培养新作者是丑表功’,他‘耻与新作者为伍’。而我们编辑部也出现了‘自然淘汰论’。所以在‘奔流’第三期‘编者的话’里,就公然提出了‘跳高’问题;这样,广大青年作者就被拒于大门之外了。”“不仅如此,‘奔流’在右派分子苏金伞、栾星等所谓‘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口号下,在编辑部的追随下,完全抹煞了刊物反映河南人民的生活斗争、历史传统和地方特点这一任务,因袭了旧社会的私人拉稿约稿路线。苏金伞等这种通过私人朋友交往稿件,也就抹煞了选稿标准。朋友寄来好的作品固是香花,毒草也成了香花。为同仁吹捧,为朋友拒绝批评。所谓‘跳高杆子’又是可升降的了。如李白凤的诗‘落日’、陈雨门的诗‘无声的春雨’、栾星的杂文‘说话难’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刊登出来的。苏金伞的诗作,不少读者的批评稿件寄来,都被压住没有发表,而一至七期仅发了一篇评论稿件,却恰是为苏金伞捧场的。问题很明显了,所谓‘质量’,不过是排一排老朋友的名单,来排斥新生力量,把刊物变成朋友们的名利场。”
9月方冰的诗集《战斗的乡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9月何其芳的诗集《预言》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9月沙鸥的诗集《夜明珠》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田间的诗集《芒市见闻》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丁芒的诗集《欢乐的阳光》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在祖国的天空飞行》、《洱海之恋》、《访杜甫草堂》、《青年高举火把》等诗25首。
9月公刘的诗集《在北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五月一日的夜晚》、《因为我是兵士》、《在工业的地平线上》、《春天,又来到了我们身边》等诗50首,有作者《代序》。
9月青勃的诗集《乐园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分为《太阳和玫瑰》、《流着蜜的河》2辑,收《真理的太阳》、《她望着西边工地的灯光》、《我带着千万农民的敬礼,走到石漫滩水库》、《我们两点钟创造了奇迹》等诗54首,有作者《后记》。《后记》说:“这是我的第六本诗集。其中有一首是在1952年写的,其它都是1953年—1956年这一阶段所写的短诗。”“我在乐园里工作和生活着,我的心无时不在颤动,但是:我唱出的歌,我写出的这些诗,却只能算作乐园里嫩弱的小草。”“我自然希望在我的诗歌创作上能够抽出枝条,开放一朵小小的红花。”“我在努力这样作。”
9月万忆萱的诗集《金黄金黄的婆婆丁呵》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分为3辑,收《醒来吧,古老的森林》、《金黄金黄的婆婆丁呵》、《问候你,祖国的汽车城》、《草原工地》等诗26首,有作者《后记》。
9月严辰的诗集《最好的玫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分为《苏联行》、《韶山冲》2辑,收《克里姆林的红星》、《雪落满了你黑色的大氅》、《让我们插上幻想的翅膀》、《敬礼,埃及的兄弟》等诗42首,有作者《后记》。
9月北京出版社编辑的诗集《北京的诗》由该出版社出版。收公刘《致中南海》、艾青《景山石槐》、李学鳌《心上的图画》、沙鸥《节日前夕》等诗100首,有编者《前言》。当时的广告讲:“这是解放后各报刊发表的歌颂北京的诗歌选集,这里选辑了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田间、李季、徐迟、沙鸥、邹荻帆、顾工等四十四位诗人和青年作者的一百首诗。在这些诗篇里,歌颂了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巨大的变革;歌颂了首都人民的豪迈的劳动热情和幸福欢乐的生活;歌颂了首都的美妙动人的景色和节日的欢腾景象。这些诗篇表现了亿万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的无比热爱。”(1957年10月6日《文艺报》1957年第26号)
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的《“超阶级”的“灵魂”——反右派讽刺诗集》由该出版社出版,收有俯拾《章氏“政治设计院”》、邹荻帆《右派的逻辑》、邵燕祥《大人先生们的心事》、陈山《孙大雨“看病”》等诗。该书《内容提要》说:“这是一本以反右派斗争为题材的讽刺诗集。其中所辑的四十八首诗歌,大都是揭露右派分子的阴险、狡诈的丑恶嘴脸及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的,也有几首是批判阶级立场不明和嗅觉不灵的人的。读了这些作品,使我们认识到在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诗人们如何运用诗歌形式作为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的武器,也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