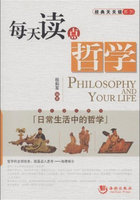历史告诫我们说,
一种崭新的真理的惯常命运是:
始于异端,
终于迷信。
——赫胥黎
在人类社会中,少数人从事开拓性的、创造性的复杂劳动;多数人干着模仿性的、规定性的简单劳动。如果前者是在勘探金矿,后者就是在已经找到的金矿上参加挖掘。这有点像少数人离线编程,多数人在线操作。或者应该说,这有点像蜂王和工蜂、蚁王和群蚁的关系。这个游戏规则好像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则。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分布与权利分配,都对少数人有好处。
一开始这个规则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它的执行是用武力作为后盾的,就如同动物界的雄性格斗,胜利者享受首先进食和占有配偶的权利。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麻烦渐渐就来了,人类社会开始没完没了地争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否等值?如果价值相当,社会财富就该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如果复杂劳动价值高于简单劳动,那么,又是谁垄断了复杂劳动,将大多数人阻隔在这个领域之外的?
这个争论从来就没结果,而贫富差别从来也没有消融。于是产生了解决办法:财富是多数人创造的,历史也是多数人的历史,就连少数人一直垄断着的文化也是属于多数人的;假如多数人不能创造,他们却拥有足够的破坏力量;假如他们不能掌握世界,至少可以用暴力打倒少数人……
不幸的是,无论在少数人的上层社会和多数人的下层社会中,都存在着人性恶以及作恶之人。更为复杂的是,人人都有恶的本能和作恶的倾向——黑格尔说,历史的动力来自恶,这话一点不假。唯其如此,人类历史才会时不时地出现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情景:也许法兰克人(Framcs)最初是为了赎罪,到头来却在叙利亚烧杀掳掠犯下滔天罪行;也许德意志民族本打算建立一种新的分配制度,结果国家社会主义输出了恶魔般的**刽子手。
人类社会组织的生活,有时是荒谬多于理性的。罗兰夫人1793年临死前在断头台上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还有许多罪恶假“人民”、“上帝”、“真理”、“正义”之名以行。
1095年,在法国克莱蒙的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35~1099)开了9天会,始终谨言慎行。他什么也没有说。会议在讨论教规和戒律问题……
忧心忡忡的教皇在犹豫:如果教廷号召基督教世界征服耶路撒冷,就意味着东西方开战了!他的军队在哪里?最多就是法国土鲁兹的雷蒙·德·圣吉尔伯爵(Raymond de Saint Gilles)的志愿军、比利时公爵戈德弗鲁瓦(Dodefroi de Bouillon)率领的法兰德斯人和莱茵人,此外就是安提阿亲王叔侄俩指挥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以及法兰西岛和香槟区领主韦芒杜瓦的于格(Hugues de Vermandois)所带人马。这是一支跨国跨民族的、临时组织起来的雇佣兵。而对手是谁?对手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个世界东起印度,西至西班牙,其中包括骁勇善战的众多派系,比如:自称土耳其苏丹的塞尔柱首领们;忠于阿拔斯(Abbassides)王朝哈里发的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特别是从什叶派分裂出来的伊斯马仪派格外凶悍,他们甚至建立了法蒂玛(Fatimides)教长国,令西亚各国闻风丧胆。
但是基督教在东方已经受到了挑战,拜占庭皇帝阿历克西(Alexis Ⅰ,1081~1118)要求教廷迅速派军干预。麻烦的是,伊斯兰教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穆罕默德是在那里的悬崖上祈祷后升天的;许多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徒祈祷的时候都是面向耶路撒冷,而不是面向麦加。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活动和蒙难的地方,是他们的圣地。基督徒们坚信,最后的审判必将在耶路撒冷进行;当天上那个耶路撒冷降临时,地上的耶路撒冷必将与其合而为一。因此从公元1000年开始,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方基督徒络绎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班贝格(Bamberg)的主教1064年前去朝圣时,跟随的人多达1.2万名!什叶派哈里发开始迫害基督徒。双方战争已势在不免了……
教皇在盘算,打这场战争,他实在没有胜利的把握。如果这场战争不打,欧洲各地不满教廷的恶徒,将聚众滋事,藐视罗马教廷。1095年11月27日,克莱蒙会议第10天,教皇突然发表讲话,号召基督徒团结起来,到东方去解放圣城耶路撒冷!
随后出现的情况把乌尔班教皇吓了一大跳——欧洲各地的骑士与农民、教士与工匠、领主与乞丐,总之,所有穷人与富人,不分贵贱,立刻热血沸腾,高声吼叫着要求开战!农民放下手中的镰刀,拢好小麦便加入到十字军中了;乞丐和贵族被编入同一个队列,摩拳擦掌等待战斗。一夜之间,欧洲人都疯了!
一些民间的“社会活动家”上蹿下跳,激情难抑,有个叫彼得的“隐士”在下层社会中宣扬:末日审判来临时,死在耶路撒冷的灵魂将待在基督身边!一时间,彼得的号召力竟然远远超过教皇!从法国出发时,约有1.5万人追随彼得东征。这群出身贫苦的穷人军团上路没多久,就占领了塞姆兰(Semlin),在那里他们毫无理由地屠杀了4000名匈牙利人,而后又在拜占庭抢劫尼什(Nish)和贝尔格勒(Belgrade)。
其实,这正是欧洲穷人到东方去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欧洲,是个连拜占庭人都瞧不起的半野蛮社会。而处在拜占庭以东的亚洲国家,个个都比欧洲富裕。至于十字军中的所谓骑士们,只不过是些在家乡领有巴掌大一块土地的装模作样的无业游民。在他们的圣战目的中,包含着对金钱、封地、爵位和荣誉的渴求。
面对这股汹涌澎湃的仇恨大军,教廷当局只得顺水推舟地宣布:所有参加十字军的人,不管他们犯过何种罪行,法庭将暂停对他们的审判;神职人员将为他们代管财产;结束这次东征后,他们所犯罪行将得到赦免……这一政策性表态,无疑火上浇油:十字军因而肆无忌惮地走一路,便烧杀抢掠一路。对这支流氓队伍首先感到愤慨的是拜占庭人,他们在东西方的分界线上,第一个遭到了十字军的无耻掳掠。十字军的主要成员是日耳曼族的法兰克人(Framcs),最初他们居住在莱茵河地区,3世纪~5世纪时逐渐攻占高卢,在查里曼统治下势力大增。所以当十字军来到莱茵河沿岸时,那里的犹太人立刻遭到了屠杀。同时被大量屠杀的还有匈牙利人。拜占庭不得不向十字军中闹事的贫民提供物资,以求尽快送他们出境。
1097年10月,十字军到达希腊城市安提阿(当时已归附拜占庭),并包围了这座古城。经过七个月的抵抗,其间多次突围,大马士革亦派兵试图帮助其解围,未果,1098年6月终于陷落。十字军进城后,挨家挨户地屠杀居民。12月,十字军占领了叙利亚的马拉·安·诺曼(Maarrat An Noman)。为了防止贪得无厌的军中贵族对城中财富流连忘返,塔尔夫下令屠杀居民、摧毁城市,以迫使军队继续进发。
经过三年烧杀掳掠的行军,十字军于1099年终于到达耶路撒冷,看到了这座太阳下闪闪发光的城市。7月10日他们开始攻城;15日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第一次陷落。十字军在城内烧杀了整整两天,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尸体遍布城中。十字军的野蛮行径,从此深深地烙在伊斯兰民族的心中。蒂尔的纪尧姆(Guillaume de Tyr)亲历了这次攻占,据他说——
在城里,十字军见人就杀,知道大部分居民躲在圣殿围墙后面,首领便率骑士和步兵前去,他们用剑把躲在围墙后面的人通通刺死,异教徒血流成河。十字军自认完成上帝的意旨:凡是以迷信行为亵渎上帝之圣地,使圣地变得与信徒无关的人,就要以自己的血来净化圣地,若恶贯满盈,就该死在这个地方。但是看到遍地死尸,满地散乱的断肢残体,以及覆盖地面的血,我们还是感到恐怖万分。
——《耶路撒冷陷落》
看来纪尧姆还算是这群疯子中间疯得比较轻一些的人,而十字军中绝大部分却正疯在劲头上。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 Michelet),对这些狂热的十字军勇士们有这样的描述:“当他们认为救世主的仇已经报了,也就是城里几乎无人幸存时,他们泪流满面,唉声叹气,捶打胸膛,前去朝拜圣墓。”
欧洲以保卫耶路撒冷为名组织的十字军东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八次。第二次东征时,十字军在哈廷被萨拉丁(Saladin,1138~1193)击溃,阿拉伯人夺回了耶路撒冷。第四次东征,十字军占领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历史性地陷落了!在接连不断的东征中,先后有过好些著名历史人物参与其事,如英国的“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Ⅰ,1157~1199)、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Ⅰ Barbarossa,1123~1190)、法王腓力二世(PhilippeⅡ Auguste,1165~1223)、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
十字军东征,名义上是基督徒保卫精神上的祖国,实际上却是欧洲贫民和骑士对东方财富与土地的垂涎。持续一百多年的这场宗教战争,造成了东西方民族在宗教感情上的永远决裂,其心灵创伤绵绵至于今日。十字军的行为,展示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将世界破坏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展示了群众运动一旦为狂热情绪左右,人性会泯灭到什么程度。
两个世纪之后,十字军的疯狂与仇恨阴魂再度显现,不过这次它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了欧洲可怜的女人们——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又掀起了骇人听闻的虐杀女巫的运动。这场遍及欧洲、迫害无辜的群众运动,是基督教世界中最不可思议的一页。
所谓巫,是指巫魔、巫教,也即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常常以一些奇特的形式来表达愿望,或者阐释世界,比如 “特异功能”、“通灵”、“预言”、“疗病”、“祈禳”等等。在中国,从事这些活动的男人称为觋,女人称为巫。当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并且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时,这种亚文化活动往往就会转入地下,为自己涂抹神秘色彩。愈是如此,便愈是阴森恐怖。这是在精神禁锢的极度苦闷中,发出的微弱叹息;这是一种不同的声音。正因为不同,所以主流意识形态不允许其存在,除非在某些特殊时刻需要利用它。
巫蛊活动在任何社会背景下都存在,而且屡屡受到打击。中国的汉武帝在其晚年时,曾大肆搜捕参与巫蛊案的“妖人”,最严重的一次杀了几万涉巫者。但是像欧洲这样形成群众运动、迫害持续数百年的事,在社会文化史中却是绝无仅有的。迫害发生时,欧洲正处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4世纪下半叶是多事之秋,饥荒、瘟疫、百年战争、内乱、暴动、起义、天主教会大分裂、土耳其人的挺进。人们自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时期,似乎只有人的贪婪无度和教会的腐败罪恶才能解释这一切。世界显得天昏地黑。似乎只有最后的审判才能解决这一场危难。”(《罪与怕》)
显然,教会必须转移人们的信仰危机;教会自身的罪恶已经聚焦了社会的注意力,需要有新的斗争目标来吸引群众激情。君主和贵族们希望巫魔来自富有的异教徒,如此就可以收缴他们的财产。农民则认为,女巫是他们歉收和罹病的主要原因。作家和哲学家却希望,通过他们对“魔鬼学”的深入论述,提高他们在同行中间的声誉……
归结起来,巫师受到的指控是:崇拜魔鬼;憎恨基督;参加黑色弥撒的食人祭礼;集体淫乱。这样一来,巫师便常常等同于异教徒,或者就等同于犹太教徒,有时还等同于基督教内部持不同见解者。因而,打击面就变得相当大了。 由于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女人从一开始地位就非常卑微,因此猎巫运动中,她们自然就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主体,猎巫就是搜捕女巫。
1484年,教皇伊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派出的两名“中央调查组”成员雅各布·斯普伦格和亨利·克雷默,在上日耳曼的科隆和美因兹追查异端时,与当地政府产生摩擦。这两位负责整肃思想立场的宗教裁判官,向教皇秘密报告了那两个不合作的地区存在着大量女巫。为了强化两位特派检察官的权限,加大对该地区异端的打击力度,伊诺森八世公开发表了《教皇咨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最近,我们听到一些令人难过的传闻:在上日耳曼的某些地区,以及美因兹、科隆、特里夫斯、萨尔兹堡、不来梅等省、市、乡、镇,许许多多的男女,忘了自己的救赎,偏离天主的信仰,与睡梦中的异性交媾,诅咒发誓,施展魔法,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他们使女人不能生育,使小动物夭折,使农作物不生,使果树枯死……
教皇的咨文,无异于猎巫的号角。自此,欧洲大地的猎巫运动便掀起了高潮。由教会控制的出版部门迅速推出了两位检察官合作撰写的专著《反女巫之槌》。 这部书详尽地教授了对女巫如何侦查识别、审讯诱供、结案行刑,可以说是专门指导各级宗教法庭猎捕女巫的教材,也可以说是一部丧尽天良的屠夫宝典。
这部书之所以风行于当时,并成为17世纪以前斗争女巫的依据,是因为它的作者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特别是其中的雅各布·斯普伦格:此公出身于巴塞尔的多明我修道院,是科隆神学院教授,布道兄弟会修士院院长。这在当时,已算得上是顶尖级的大学者。以他在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名望地位,谁能怀疑他言之确凿的论断?
继他之后,一些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反女巫的行列中,令人不由得要慨叹:知识和良心都是可以收买的!法兰西极孚众望的政治理论家、曾教授过12年罗马法的法学家、被后世誉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让·博丹(J Bodin,1529~1596)竟然狂热鼓吹捕杀女巫!他撰写的《巫师的魔鬼术》轰动一时,书中写了他所发明的对付女巫的各种刑罚,读来令人作呕!他对那些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的阴险法官们说:“当您审判时,什么人都不用怕,因为审判来自上帝。”
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都不能代表良知说话,甚至与罪恶同流合污的时候,民间会干些什么!莫切布莱德(R Muchembled)在他的《最后的火刑架》中,描写了一桩在当时非常普通的女巫案:受害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妇,没有多费什么手脚,她就咬出了另一群无辜者,于是法官很轻松地结了案,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不错,北方每个村子在圣约翰日都要烧一名巫师,但都是用偶人代替。这次,传统的替罪羔羊却不是木头也不是草秆,而是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