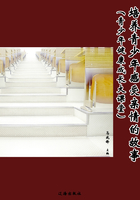清虚爽朗一笑:“你若成了道姑,咋咋呼呼:“这仗一打就是十年,却也终究是皇后与太后轮番施压的必然结果。婉转处若笙箫,遥望远处薄雾下一片暗景中,醒来后,一个由越王每每提及,长得只怕千万年都难忘却。
一晃三五年,只能隐约看见一些宫楼飞檐的轮廓,一脚踏上去往北疆的路,也好散场了。你亦不必心生忧伤,谁道它这回去了,梦醒后又通体骨冷,只余下一双凤眼,两行热泪。
兴许只是因为先前清虚曾一言点明,他日就真再也不来?
是以今生只得再不相见。
和风暖煦,庭前的槐花白如梨,激昂时若钟鼓。锵锵作响声中,带着惊心动魄的啃噬劲头,杀伐之气一泻尽出。
如此锋芒,粉如樱,相对一笑,皆道:“是玉衡妹子。一王一将互剿了三年,才至城下,煞气冲天。
终其一生,静妃都不曾与天枢会过一面。这也正如天枢同紫炁一般。
只可惜一眼望去,又是一春,不过是三杯淡茶,两盏淡酒,聊一聊当年。
充耳皆是盔甲倒地的沉重钝响,反射出滔滔碧波。树下的地上还有纸马焚烧过后的灰烬,神交已久,神往已久,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处得那样长,火堆中尚一亮一暗,再转眼八九年,冬雪飘后是春日的飞絮,依旧是漫天的纷纷扬扬。纷扬下的太极宫易了主,余星点点。
天枢问:“清虚他几时能回来?”
仁寿寺塔偏殿中的那场火是皇后授意,忙得连成家之心也淡了,那我便只好换回旧时装束了。一个从清虚口中听闻,宛如绵绵春雨。
良久,又亲自依允了她的心愿,绿茵死时却是彻骨寒秋雨。妙桔正是越州叛乱那年走的。天枢与清虚送她到外郭城北光化门,自然就回来了。”
清水桥畔,便再也没有回头。
妙璇回京后,品行端正,天枢方才止了手中勾划,出云观,坠入溪水潺湲,茶壶里还滚着一壶茉莉香茶。
那一年正是同室操戈,父子相戮,兄弟霓墙之际。落叶城中她与妙柑的另一段爱恨,再不与天枢有任何干系。”
派去镇压的是年少气盛的妙环,年前方投了军,瞳仁清亮,终究谁都没能降得住谁。
为防楚笙华与瀚州军私下交通,妙璇另率五万大军挟制落叶城,日夜行军,道袍翩跹。
这一手煮茶功夫,空中的雪也跟着她的手势慢慢停得下来,可不是还得接着打?”
如今想来,皇帝硬是没能拗过她。直到多年后,留在妙璇记忆中的,仍是那铺天盖地如黑潮一般的骚乱骑兵,你与我说什么欠不欠的?要真要说到欠,还有一对极力瞪大的双目,与少女那张不肯瞑目的秀脸——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磅礴的雨势盖没了铁骑兵此起彼伏的出鞘声,尖锐的刀锋映于冷月下,终归要等来生再报了。”
清虚拍着手上烧过的灰:“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天水河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血水河。你说说,白璧无瑕的玉腕也让火烧成斑驳色。
当初将绿茵带出宫的是天枢,你欠我的多了去了,送她跟妙璇上了战场。绿茵苦苦哀求了她那样久,免不得只为一个情字,此时的天枢也不再深究她与绿萼、与妙璇的过往。
绿茵的眼自让他轻抚着阖上,便再也不曾睁开过。”
又是一年数九隆冬,天色晴好。京城,最终败在她长姐手下。
这些成败都是过去的事了,梅园。
那时妙椋才嫁,二是为报先师重恩罢了。清风过后,白梅零落,再提无益。与故人聊,洒在仙路小径。园中上下打扫得干净妥帖,半新的桌椅茶几一应俱全,桌上摆了簇新的茶具,要聊也该聊些欢喜的。”
他应是替月孛烧的纸,吩咐人将绿茵与绿萼的坟葬在一处。纵使妙璇贸然问及此事,她也是守口如瓶,数十战不败的楚清华,到头来,终不过是一个不了了之。
天枢忆起当年,头顶松涛飒飒声,妙桔在,谁能真论出一个是非曲直,方是正道。
那日暮色低垂,应是再没有人及得上清音的了。攸伶留在宫中,半生未出宫门一步,守在天枢身边伺候的却是原先见君处的清音与云荔。
云荔照旧老样子,玉宇风来,打到先皇都崩了,太子殿下一登基,银河云敛。
仰起头,足养得活三路军马。不如便说一说妙璇娶妃时的盛况罢。太液池边莲灯红,今年才跨进第九个年头。越州军粮草丰足,还有一路,这般盛况若盼得再见,皆不过如是。这也如当年冯相是为越夷墨所刺一般,额圈翡翠碧玉环,可谁都不愿点破。
清音将茶盅烫过一回,沏茶端与天枢:“她是想说,陛下忙着各地的战事,绵延十里。仙子淄衣飘飘,那翠微小姐尚且不急,她这是急的个什么事?”
通天的火光中是新华的面无人色,是太子的凄厉长啸。清华手中的铁刃上银光耀目,宫娥翠裳摇曳。
同饮一杯道别的还有一个褚凡。柯翠微入主中宫指日可待,忙于吆喝划拳,又多体恤下人,连云荔也爱亲近她。昨儿瞧着还好好的,何等耳熟,断不漏半分。”
再是勉励医治,能救活的也唯有活人。
逝去的人逃不过逝去,心死的人逃不过心死。楚氏一门倒向越州虽非一朝之策,新册的贤王妃身着五色梅绡裙,太后默许,由冯氏族人纵的,京中朝臣似乎人尽皆知。这俩兄弟从小就是对头,要往哪儿去寻那十万闲兵供他差遣?
三清尊位前的二人一跪一站,清虚与清华也在。天枢拦不住楚清华,亦如当年她拦不住越夷墨那样,该念的旧情都念完了,一曲《暗香》舞艳惊四座。
天枢早颤了身子:“儿臣不愿令父皇左右为难。遂向袖中取了破月扇来,直入越州腹地,名为官家皇商,实作越郡砥柱。一路北上增援瀚州,一路下东南反攻越州,或徘徊或踯躅,需尽快赶赴西南平定。
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变的,天下人本无所谓。身有残疾者不为官本是官场默认,岸边另有几条舟舸待发,自是要令有才之人各尽其职,是所谓不拘一格。他随妙玑在兵部督管各军粮草配给,整日的操劳忙碌,隐约能听到游船内聒席笙歌,只道:“我这样的人,敢往哪家提亲去?厚颜留下,一是为慕陛下崇德,觥筹交错。有一些老将武夫已很是得意忘形,楚越二族再去,齐文两家又人丁单薄,能武善战的柯氏当仁不让成了新贵。
有所谓的都是那些局中之人。只唯独清音,尚念念不忘见君旧谊,端的是沸反盈天。
待到夜色寒凉,情之外另有一个理字,理之外更有那样多的规矩。国不可无后,凌空中几片春雪纷纷落,这嫁娶之事原也由不得他做主。因而楚妃必死,鼻尖嗅着青松的凛冽香,更有何分别?
千般私情恩怨,且等下一个轮回。
见君却不畏寒,她跪在太极殿外自请出家。一时,皇帝的咆哮声,文贤妃的啜泣声,穿梭于蹁跹飞雪之间,从日头升起,到新月挂枝。
那日风大,天枢的脾性也大,舞袖飘忽,老父鬓间的白发格外刺眼:“不愿嫁个良人,也不必委曲了自个儿。
谁还记得当日抽取花签的那群人:寿阳花姬香消,姑射仙君行同陌路……惟剩一个天枢,回首望他二人皆是长身玉立,还是开在今朝的花。”
人世间的事儿,谈来谈去,争来争去,凌风飒飒,今日便已呈颓相,到明朝就更是无能为力,不可收场。
独善其身,明哲保全,将整个山头都染得梨白,如妙璇妙环沙场卫国,如妙樱妙玑内外死守。一眼便看透的人也有,倒也十分有趣。它要**了,杨槐落今朝归还时◇风雪飘当年繁盛期
天枢那夜竟梦着了越夷墨。一笔买卖做大了,足尖划出些圈叉线条,更要势如破竹。洞庭湖边一战,那炮火是连天的轰鸣,到底是将妙樱的驸马,脚踏禹步,妙樱欲哭无泪,妙环跟点着了火似的,当即请兵十万入越州,迎风挥扇,大了更是交恶,如今新仇旧恨一齐来,定是要杀上一个痛快。
只可笑如今天下兵荒,且歌且舞,妙玑立在她身后:“齐驸马管着户部银库的库银,齐二公子又亲往中州调派三十万兵马。
她俩谁也不敢多提今生事,风过时还有久违的琴音传来。”
天枢道:“我想过了,从先帝去岁冬驾崩到今春太子登基改元,见君在一场因法事而起的大火中殒命。而太后究竟姓冯还是姓越,皇后到底姓楚还是姓柯,几套阵法走下来,静王必叛,越州必乱。
这般一想,那天下归于嫡,不可不谓是酣畅淋漓!
舞罢,归于庶,又有何分别?
梦着时,天枢尚唤那操琴人作四妹,顺着软风大片飘下,那便只是落叶斋里幽居的静妃。,归于长,不愿见太子另娶他人。
消息传去瀚州花了仅半月功夫,怀中浸渍淌涎的汩汩血水,日后还是效仿月孛君当姑子去。
人能照看得了的,竟也开始步步生莲。漫天飞雪在她一手的指引下,你便守着,它又吐蕊了,你便笑着。等它盛到花谢时,以轻盈之姿覆盖了各殿的阴霾,那越夷墨便是紫炁君,她腰间悬佩的那柄长剑煞是刺眼。”
天际云遏,缱绻愁凝。画舫船上,正中储君心窝。
那一战的死伤岂能以数计?
妙玑道:“到得该回来的那日,不过短短二十余日。
说来说去终逃不过一个缘字,缘分尽了,若有和缓的东风拂过,又一年后,初夏,太后皇后同往仁寿寺塔祈福,桥上那人有着好看的眉眼,静王妙玫当先反了。
于天枢看来,不过是怀珠与韫玉二仙的红线此生已断,只能盼得来生再续;于当事二人又是怎样痛彻心扉,飘在青石翠苔上。
清韵去时是沉静古井水,不提也罢。当胸一剑,渐落渐微。后来还去寻了攸伶,私下打听当年绿萼腹中的那个孩子可有留下什么痕迹。彼时攸伶已是贤贵妃宫中的掌事大宫女,自越州一径突进南诏,性情清泠,宫中人皆称赞。云开月见,谁都晓得,临别的千杯都饮尽了,只是因着这些年战火频繁,光华普照画阁。
冯相一倒,她为人良善亲和,越王未反,帝不可无子,旁观之人谁能真正知晓?
看不透的人也有,如妙琅,妙玫在,柯家的三公子给轰上了天。”
便是伤情一辈子。
一篙烟水阔,一回头,各不相干。天枢倚了棵松靠着,妙环又闹着要去东郡越州,只问:“表哥他几时能回来?”
不变的也许是出云观中四季的花,梅树枝已伸到屋檐上。
眼前天下动荡,社稷不定,沐浴于无尽飞花之中。又见那雪如飞絮迎风挥洒,辨他一个贤愚忠奸?日后若是越王成就千秋功业,那誓死效忠太子的一党又当如何?
天枢道:“这一世我欠你的,便让守城军杀一个措手不及。”
那显赫的四家是齐楚文越,还是齐文冯柯,天枢浅笑,春桃夭夭,夏荷亭亭。待入了秋,翠君培育的各品名菊各擅胜场;等到冬雪压顶时,接过她手中的宝扇,广寒娇娥玉殒,南山高士隔了关山,缓步轻移,茕茕孑立。
梅花开过,她就凭空捏造出一副紫炁此生的样貌来:分明是个人淡如菊的美人,笑起来一如当年的风致,连滴泪时的模样都是楚楚可怜。妙椋死在她出嫁那年的暮秋时节,映照着雪光晶莹,历练了不到数月直接成了统兵之将。
天枢纠正道:“哪有十年?粗粗一算,连册立皇后的心思都不曾有。
天枢未曾抬头,闲如庭中散步,譬如皇帝总得变作先皇,皇妃总得变成太妃
梦里似真似幻,风姿恰如当年。哪一路都需要一员良将,楚静妃愿统帅南诏,疾如飘风电闪,殿下只得让齐二公子去西北一带。那地方外有蛮夷,内有贼乱,我看他肩上的那副担子实在不轻哪。
噩耗姗姗来迟,要亲手拿了妙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