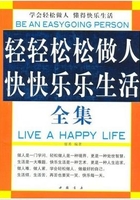火车站之后薛涛已经很久没见到杨云天了。乍然相见,让她有点小小的激动,虽然之前不久他们通过电话,杨云天见她的时候也很自然。
但她还是激动。
她是被研究所邀请去工作的。第一天,她没有见到杨云天,也没有在那里吃饭--工作人员有权利在研究所吃午餐和晚餐,程序是早晨报名,月末结账,每顿5元。但她不是名正言顺的工作人员。她只是即将成为杨云天研究生的人而已,虽然相比起原来这也算有一种确定的身份指向,但敏感如她,还是会觉得寄人篱下。杨云天不在,她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秦非身上,却发现他几乎帮不到她什么,反而让她更不自在,衡量之下她最终还是放弃了。
现在,她又回到了研究所,无法贸然地出现在他们的午餐桌旁。她在等待一个最有权威的准许,却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存在。但是当她跟正在工作的杨云天打招呼的时候,她告诉他其实自己昨天就已经来工作过了。
杨云天问的第一句话是:“那你昨天为什么没在这里吃午饭?”
她一时语塞,她不能说“我在等你允许”,只是说“因为我没有报名说我要吃”。
杨云天用看乖小孩的表情笑了笑,问:“那你今天报名了吗?”
薛涛有点小感动,少见地露出孩子般的灿烂笑脸说:“还没有,我这就去。”
吃饭的时候薛涛跟往常一样很规矩,低着头没有声音地吃饭,笑着看前辈们谈笑。杨云天有时候会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把她捎带进去,她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对他笑笑。心里暖暖的。
她总觉得自己明白他,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明白她。所以当他们相处的时候,总会从心中微笑出来。
这一点在下午他们在一起谈薛涛未来一年的事业规划的时候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出来。她基本上按照一年多以前他对她的建议规划了自己的发展,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更进一步完整的建议。无论是因为她有意无意地遵从了他的指导,还是因为她本身的知识与性格的必然选择,总之,这一切来得如此自然,他们的想法如此合拍。
晚餐时,她和一个其他院校的女生一起与杨云天、秦非还有另一位重量级教授巫鸿一起吃饭。席间,各自相谈甚欢。薛涛面对那位教授的提问也算对答如流,没有给杨云天失面子。当然,还是杨云天与教授的对话更让薛涛受启发--虽然杨云天的话她大部分都听过,但当两位教授对话时,碰撞出的对博物馆展览的认知、东西方文化的对比讨论、对教学的考虑,都让她受益匪浅。
当秦非听得都有点困意的时候,薛涛的内心仍十分兴奋。她比以前更加确定了,自己和秦非果然算不上知己,虽然好人秦非在席间还是会对她表示似有若无的在乎,甚至在说完话后看她的眼色。
后来薛涛在空调底下越坐越冷,抬手关了空调,却发现原来是巫教授需要用冷气驱蚊,赶忙又打开空调。
杨云天马上拉开身边的凳子拍拍说:“来,坐到这边来。”
薛涛觉得坐在他身旁妥帖又安心,可当他歪过头凑上来低声地问“你说我们要不要恢复晨读啊”的时候,她忽然心神一荡。
顿了一顿,薛涛不露声色地笑着说:“我们还是恢复晚课吧。”
她想记住这个夜晚,用眼角余光把他再细细打量一番。杨云天穿一件灰白底子有细细的深紫深蓝条纹的衬衣,配修长的黑裤子,黑色系带小牛皮鞋。喝了一点俄罗斯的白酒,没有明显的醉意。
这夜过去,薛涛忙毕业的事,等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见杨云天,才听研究所的前辈说他出国了。她原以为这是把自己的心腾空的好时段,结果恰好相反,他离开后化身思念,蛮横地占据了她整颗心。
六月的一天,薛涛在研究所一边工作一边抱怨:“假期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七月初必须从本科生宿舍搬出来,刚才去生活服务部问过,研究生宿舍不到九月不能入住。”
一起工作的学姐说:“要不你先去我宿舍凑合一下吧,你不嫌挤就好。”
薛涛露出笑容,刚想答谢,突然被门口的声音打断。
“你可以去我北宫门工作室那边住,小区很安全,就是有点偏。”
薛涛抬头看见杨云天,一时愣住。
杨云天也不给她拒绝的余地,在她发怔的十几秒中迅速取下钥匙放在她桌上,不由分说的样子。
薛涛忽然没来由地红了眼眶,一句“谢谢杨sir”搁浅在喉咙里,直到他转身出门也没能发出声音。
许久不见的他以如此突兀的形式重新出现,莫名其妙地砸来宠溺,让人不习惯。
相比起来,与杨铬的重遇就平淡多了。
薛涛事先是知道他短假会从法国回来的,但并没有特地去期盼自己能见到他。不曾想某天去找秦非谈工作,在办公室遇见了他。两人初见都有几分错愕,互相问了几句“你怎么会在这里”的问题,最后杨铬先笑起来,揶揄说:“十万个为什么就是这么凑成的。”
在薛涛要离开的时候,杨铬说,他也要走了,并要顺路送她。
当然,这车不可能不给对方交流的时间而直接驶向她的寓所。在杨铬的提议下,他们顺理成章地出去兜风。但薛涛并不想走得太远,只是去学校转了一圈,在学校图书馆门廊里为他照了一张照片。
开车送她回寓所的时候,薛涛听见杨铬的电话一直在响,但是杨铬并没有接,后来薛涛无意瞥见是杨云天的来电。
杨云天似乎很执着,忙音过去无数声仍然不挂。看来杨铬给父亲回话的时候,必然会把与薛涛出行的事汇报出去。杨云天会作何想法,薛涛想不到,但敏感如他,内心的思绪应该不会只是留给儿子淡淡一笑那么简单。
杨铬说,他周五就又离开中国了。就算这样,薛涛除了那天下午心情澎湃了一阵,与各位密友聊了几句,也并没打算在内心持续波澜。
正如她曾经说的,她眼中的杨铬并不是一个与她同龄的男生,而是“杨云天的影子”,包含着挑战、浪漫、异文化等多种因素,是她自己塑造出来的男生。所以薛涛并不打算在杨铬身上投注太多的感情,因为毕竟,她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她明白自己与杨铬之间所有的羁绊都不过是一种移情。
几天后薛涛再见杨云天,两人都没提起杨铬,杨云天只问了问薛涛诸如“添置了什么”、“住得习不习惯”等无关痛痒的问题。
薛涛不知是否自己多心,对方似乎有点冷淡。
新学期开始后,薛涛与杨云天、谢雨、方拥三位教授座谈。她原本只是被杨云天叫去端茶倒水作招待的,没想到杨云天的“发小”谢大教授一去,竟对薛涛大感兴趣,随即谈起了现代女生的婚恋观,把师生恋、女学生对教授的感情问了小半个小时。
薛涛本就心虚,又是当着方拥,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实在是忐忑不安。杨云天大概也觉得不太自然,便对她和方教授说:“谢雨是做社会学的,走到哪里都想做调查,在美国不好这么直接问女生,跑到我们Z大来问了!”
当问到薛涛的打算,薛涛回答硕士毕业就结婚,杨云天震惊地抬起了头。
谢雨继续追问薛涛有无结婚对象,薛涛稍稍迟疑。
谢雨转头去问杨云天:“你知道吗?”
杨云天喝了一口红酒,略低了一下头说:“不知道,我没问过她,你可以问问。”
薛涛看了他一眼,又看看谢雨,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肯定地回答:“有。”
杨云天猛然抬头,再次面露惊诧之意。过了一阵他对薛涛说:“你父亲把你交托给我,我平时都不太说什么。在这件事上我要对你说的只有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合适,千万别凑合。”
--如果没有那么合适,千万别凑合。
论话里有话,想来杨云天是有天赋的。几周来,薛涛被这句话扰得心烦意乱。她总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平时可是特有主意又能干的姑娘,一遇上杨云天,就只能做个小鹿乱撞的少女。
钢笔在记事本上走,走向却偏离了,一会儿打圈一会儿折线,最后画出个什么东西,自己也看不明白,且算它是意识流。
讲桌前老师苍老的声音像化骨绵掌,催人瞌睡,可研究生的课学生太少,又不好意思破罐破摔垂下头去。
“日本有些研究鲁迅的学者后来也证实了,‘藤野先生’这个人物的塑造,鲁迅掺杂了很多夸张和想象的成分。他们去查找鲁迅当年的班级记录和课业记录,发现并不像作品里写的只有他一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可多着呢。而当年鲁迅的作业,藤野先生的批改审阅也没有特殊化的表现。归根结底,藤野先生似乎并没有特别关照过鲁迅。”
钢笔突然一顿,本子上一个墨点,之后笔尖一直滞留在了那处。
“……就连作品中所写的令他记忆尤深的驿站‘日暮里’,其实也并不在东京往仙台学校的沿线上……”
似乎,并没有?
压根,不在?
墨迹逐渐晕开形成漆黑的一大块,薛涛忘了抬笔。
薛涛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杨云天邀请她务必参加研究所20周年庆在北京有名的白家大院举办的晚宴时,她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太意外--自己为此事出了力,他们应该予以回报。何况那个名贵的饭庄离她所居不远,她过去也方便。
虽然不敢再妄自揣度,她还是很想见见相别一月的杨云天。
她踟蹰了很久,却还是去早了。好在白家大院的玉兰堂极大,外边又有园林,她把包放在客厅便出去玩。直到看到大部分队伍已入厅,她才进去。一身黑衣的杨云天正在和几个相熟的朋友站着聊天。见她卷帘进来,抬头笑笑:“薛涛来啦,我看了你做的东西了,很好!”
薛涛笑着与他打了招呼,接着说:“是前辈指导得好,提供了很宝贵的idea!”一旁的前辈也跟着谦虚。互谦了几个回合,杨云天便大笑着和他的几个外校学生说:“看,这就是我们Z大学生,多谦虚!”
几个老同学便拿他多校教授的身份取笑。
将要落座,杨云天突然大声提议:“今天我们让这群年轻的志愿者坐上座,怎么样?我现在已经很累了,嘉宾由你们去招待!”说完之后,又向旁边几个老同学解释道:“这次活动我们有一群年轻的志愿者帮忙,他们一会儿都要过来。”
不出意料,无人理他的号召--招待贵宾这种麻烦事,谁愿意接下来?远远站在人群后的薛涛虽然尴尬地不知该坐何处,倒也不怎么想去坐那上座,尤其是听到还有“一群志愿者”的时候。看大家一一落座,便挑了第二桌边角的座位,看看这桌好歹有秦非这个熟人,便坐了过去。
过了一阵,两桌渐满,但薛涛发现所谓年轻的志愿者其实只有自己和师姐两个--事实上师姐来得很晚,如果当时杨云天的提议被允许,那么上座的人大概只有她一个。
师姐来时,薛涛像看到救星一样一顿猛招呼,师姐刚要落座在她身边,杨云天隔着一桌招呼她:“你要不要过来坐?这边有个法国人,你可以和她聊天”,师姐瞅了一眼上桌的“贵客”,笑着摇摇头。
杨云天又说:“要不我坐到你那里去,你到这来替我招待客人?”
这次师姐拒绝得更坚决,一屁股坐在座位上,不动了。
席间,杨云天过来两次,都是劝酒、聊天,只要没说到薛涛头上,她就不把注意力放过去。直到他大声说起他在加州一家旅馆的玻璃房间的事,她才不由地抬头看他,他就马上转过头来,四目相对,她只是微笑。
酒过三巡,杨云天又来这边劝酒。身为办公室主任的秦非突然不好意思安坐,说了一句:“我都喝晕了。”
杨云天快步走到秦非与薛涛的椅子中间,手扶着椅背说:“我早就喝晕了,都喝了十一杯了,刚才他们没进来的时候我就喝了两杯。”
薛涛想起秦非刚才还在说“杨sir有时会自己在屋子里偷喝酒”的八卦,抬头笑问:“杨sir偷喝酒的毛病还没改呀?”
杨云天笑着拍拍她:“喝酒就是喝酒,我没有偷喝!”说完还一直站在这里不打算离开。
秦非背后压着上司的高大身影,实在坐不下去,便过去另一桌喝酒。他前脚刚走,杨云天便顺理成章地坐在了他的位子上,然后便不走了,秦非回来了他也不走,可怜的秦非只好另觅他座。
等秦非后来又坐在两个提前走了的女士其中一个的座上,杨云天才突然来了一句:“她走了啊?”
满座纷纷笑闹:“她已经走了两小时了。”
“不是,是一小时。”
“她是您过来的时候走的,您忘了?”
……
事实上,在杨云天过来说话的十几分钟里,那个座位一直空着,只是他一直没看见罢了。
杨云天也许是坐在这里歇着的,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就只是静静地坐着。薛涛也没什么话可以与他说,便也静静地坐着,别人说什么她只是随意应酬着。因为没什么对话,薛涛已经觉得气氛开始变得尴尬。
正巧手机响了,薛涛像抓了救命稻草般,挪出房间去走廊上接听,其实只是母亲打来嘘寒问暖的电话,没什么要紧事。但薛涛已不想久留,便佯装受急事召唤匆匆进屋,对杨云天说:“杨sir我有点事要先走。”听了这话,他笑容僵了一下,几秒后才又笑着温和地说:“你去吧。”
薛涛拎了包出门,刚折转个弯,恍然听身后杨云天在叫自己,回头看却又没人,自嘲地笑笑。
低头加快了步子,手腕却忽然被扣住,前进不了,无奈再回身,想这是谁的恶作剧。
抬头却看见杨云天的脸,不是幻觉。
面对面,不过一尺距离。
辨不清有几分醉,也辨不清醉的真假,总之他的神采与平日是迥异的。
薛涛下意识咬住嘴唇,以免自己失声。一丁点细微的震动,经过年月漫长的压力递增,最终演化为排山倒海的模样,然而这一刻--
他的眼眶确实泛着红,绝不再是谁的错觉。他唇齿张合也那么确凿,一句“薛涛你别走”任谁都听得真切。
--这一刻,那所有的悲欢都冲出胸腔,悬空,凝滞,变成陡然下落的瀑布,在最后完完全全归于了平静。
令人匪夷所思的、出奇的平静。
女生轻轻抽出手,微笑着看向老师的眼睛:“已经太晚,我必须得回去了。”
从老电影中借来的,梦的想象。
驿站上零星站着、坐着几位乘客,青色群山间缓缓驶出的列车在这里短暂停留,置换了几位乘客,又按照既定的路线继续出发,此后的一路似乎便摆脱了重山变成了平原上的坦途。
在列车摇摆着启动的瞬间,临窗的女孩努力变换坐姿想看清古旧木牌上那驿站的名称。
恍惚觉得是“日暮里”,又不能确定,只好向对座的老奶奶询问。
“日暮里?”老人家动用了脸上所有的线条来组成一个和蔼的微笑,“确实有那么个地方。不过啊,它并不在这条铁路沿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