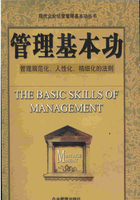登山者的目标不是登顶,而是体验人生中的勇敢行为,向自己挑战。这是一种灵魂的攀登,把壮丽的雪山和大自然抱在怀中,向世界上热爱生活的人呼唤一种崇高和美好的生活信念。
王勇峰不太爱说话。
在珠穆朗玛峰的一场狂暴的暴风雪后,我问过他:“勇峰,你认为下次行军登顶有希望吗?”“太难说了。”他望着帐外的飞雪,摇摇头,”那得看老天爷保不保佑了,登顶时暴风雪一来,谁也不敢放大话。”“你有信心吗?”他默默无语。
--这就是他。他是我所见过的又一个真正的登山者,从来不说大话、空话。人,活得像山一样实在;心,也像冰山一样透明。
过后他对我说:“你真是干记者干出了职业病,总想从被采访者那儿得点儿豪言壮语。我跟你说,我反感那一套。你问我有信心吗?废话,没信心我干什么来了?实话告诉你,为这次登珠峰我苦苦等了五年。五年前的1988年,我登到8000米,结果失败而归。我的泪水流在肚子里,我发誓要记住那次惨痛的失败。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还用说吗?”又一次,我问他:“假如你登上了顶峰……”他打断了我,笑着说:“不要说假如,没有假如,就是真的登上去了!”“好,就是真登上去了。你到了顶峰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我以为他又会奚落我“犯病”。但没有,他沉默下来,只说了一句:“我想过,真的不止一次想过……”他没有说。
中学时代,他就喜欢户外运动,常去郊外旅游。大自然说不清的一种美,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他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什么东西,早已交给了自然。1980年高考时,他在重点院校报考栏中,填写的全是地质院校。结果如愿以偿,中国最出色的地质院校--中国地质大学录取了他。
他生性好动。一入校,他就十分渴望加入学校的业余田径队,迷到了每天下午在体育教研室门口转来转去的地步。老师说,行,你练练试试看。结果,学院的几项长跑纪录都是他打破的。1983年底,他如愿以偿,被学院登山教练看上,走进了登山运动的行列,成为一个登山运动员。
和雪山打交道,最适合他的性格。第一次登山是在青海的阿尼玛卿二峰,当时他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随着中日尼联合登山队进山,在经历了雪崩、滑坠等各种危险之后,他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了。奇艰绝险面前,随时有丢掉性命的可能,但他从老登山者身上发现了这项事业的价值。登顶峰的那一刻,他享受到了人生最美好、最巨大的幸福和荣誉感。
“它充满着我的全身,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征战沙场的英勇无比的将军,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去做,那时真是年轻气盛。”他说。
1988年底,他和队友李致新作为中美联合队的队员,去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这是中国登山者第一次到南极去攀登,也是第一次完全要依靠两个人的力量去登一座险峰。在那里,出发进山前,他们被要求必须填写一张表,得说明自己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意外,将无人对他们进行援救。这使他们深感离开祖国、离开亲人的孤单。但此时此刻他们又感到肩上的任务是那么重,又那么危险。他们是代表祖国来完成这次登山任务的,祖国在他们心中是坚强的后盾。
他毅然拿起笔,在此表上签了名。之后,真感到有点儿“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他们成功了。只是在顶峰上,有种想笑笑不出、想哭哭不出的感觉。这一次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登山者也同样有着远距离、小规模的探险能力。外国的登山伙伴向他们伸出了大拇指。作为中华儿女,能为祖国赢得荣誉,他们感到无比自豪。
1992年,王勇峰等四名中国队员到美国阿拉斯加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这是一座神秘的高峰,变化无常的气候和风暴随时都有可能把登山者卷下山谷。有许多著名的登山家在这里遇难。出发时,按中方的意愿是,沿比较安全的传统路线完成大陆队员首登这座高峰的任务,可是美国队员提出要攀登难度更大的西壁路线。这条路线危险性很大,三名韩国队员前几天刚从这条路线摔下身亡。为了给祖国争光,他们同意从这条路线攀登。在接近顶峰时,美国三名队员出现了危险,王勇峰和队友李致新不顾个人安危在冰崖上救出了美国队员,使美国队员钦佩极了,直夸“中国队员了不起!”结果,这支队伍只有他们这两个中国队员登上了顶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93年春天,他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海峡两岸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这次,他要还五年前的登顶之愿。
且不说珠峰恶劣的自然条件,台湾队员实力也较弱。在山上,近两个月的运输、修路、攀登过程中,内地队员必须负担得更重一些。
王勇峰每天仍旧默默地在营地奔忙。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分物资、整理装备,准备次日的运输。自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至7028米的天险北坳,王勇峰顽强地往返攀登运输达九次之多,成为运输次数最多的队员。台湾山友被他的顽强深深打动了。
我刚到珠峰大本营时,高山反应强烈,头疼欲裂,连呼吸都格外艰难。王勇峰时常坐在我的睡袋边,笑着让我起来活动活动,或和我聊天,给我唱歌。我很感动,我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勇敢的力量在召唤!暴风雪之夜,我和他坐在几乎要被狂风撕碎的帐篷里,听他平静异常地给我讲述许多登山者的故事。他说他很佩服意大利著名登山家梅斯纳尔。
“真的,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登山家。”他的眼睛发着亮亮的光,“不光是他专选最难最险的路线攀登,也不光是他敢在珠峰冒死创下无氧登顶的奇迹,我认为他最伟大、最深刻之处在于对登山探险的理解。他认为登山者的目标不是登顶,而是体验人生中的勇敢行为,向自己挑战。这是一种灵魂的攀登,把壮丽的雪山和大自然抱在怀中,向世界上热爱生活的人呼唤一种崇高和美好的生活信念。我要以他为榜样……”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心,知道了他为什么盼望攀登珠峰达五年之久。
如今,他作为内地唯一的一个汉族队员,将和突击组的队员向顶峰发起冲击。他会顺利吗?
作为王勇峰的队友和校友,此时在山上的还有马欣祥。他和王勇峰应当算是祖国第三代的登山者。这一代人身上有个突出的特点:文化素质较高,对山的理解观念较新。台湾队员都很喜欢小马,称他为“小马哥”。“小马哥”是一部童话中一个善良的小哥哥形象。
我认识马欣祥,是1991年的10月。那次是不期而遇。我到南迦巴瓦峰采访,刚到拉萨就遇到了从希夏邦马峰下来的张志坚和马欣祥。那一次,他们所在的中日尼登山队在希峰遇到了山难,两死两伤。张志坚在第一突击组,山难发生后从雪地爬出,艰难地营救其他日本队员。就在他们这几个幸存者处于绝境的危难时刻,第二突击组的马欣祥和另一个日本队员赶来营救,使他们得以死里逃生。
张志坚对我说:“那真是九死一生!人在那时候,感到突然和世界分离了,它比雪崩和滑坠更可怕,因为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和山下一切联系中断,谁知我们出了事?谁知我们在哪里?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伙伴马欣祥上来了,一步一步走向我,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说不出,我们只有抱在一起痛哭。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体味到友情的纯洁和崇高。从他搀扶着我下山起,我的吃、穿、睡及其一切,都靠他一步不离地精心照料。我的双手严重冻伤,连解个大便小便都是他为我帮忙。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好像就交给了他。若说兄弟般的情谊,也难以到这个份儿上。山,甚至山难给了我太多东西,而小马给了我更多的东西,我将永远感谢他……”我望着小马。小马直摇手,那意思是不值得一提。
“应该的,谁都会这么做。”他说。
他很文静,也不太爱说话。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单纯而明净。
那一次,我们几乎没谈什么。但是,他的那双眼睛,我清清楚楚记住了,而且不会忘记。我很相信我的感觉。
果然,我们有缘分。不到半年,海峡两岸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活动组队,他正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博士,应邀前来入队了。他和金俊喜、王勇峰、罗申几人在怀柔的登山基地训练时,我去采访,恰与他住在一屋。我们谈了许多,我再次感到他的直率、善良和气度。
我们一起和海峡两岸的所有山友进藏,进入珠峰。他和队友上山时,我在大本营送他,那是一个风雪呼啸的上午。他没有和我说什么,只向我挥挥手,坚定地迈出每一步,向珠峰的冰山雪谷走去。行前,我请每个队员写下一句话,那是面对珠峰最想说的话。他开始说请我代他写一句,我写了,他看了摇摇头,说有些让人费解。他给了我这样一句:“当我从珠峰下来的时候,让我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美好的回忆”,真的无比美好,但又那么悲壮。
一个希夏邦马峰,一个珠峰,这两次攀登,对他来说,都是他人生历程中很重要的攀登。他没有登顶,但他用那颗美好的心灵救助了战友,一次次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我明白,这付出,需要很多看不见的代价。对于两次高山救助战友,他一直说是应该的,别人也会这样做。这是心里话,但我想使所有的山友明白,他内心深处的另一种茫然甚至痛苦--那是大部分登山者不能承受却必须要承受的,便是:最终没能实现登顶之愿。目标确立之后,一而再地受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残酷,可这就是现实和人生。
我和他接触时,就注意过他的“相”。他很善良很纯真很坚强,但是,眉宇之间藏着一种忧郁和坎坷。这一点,是任何一位优秀青年都必然有的命运。这是上苍在磨难、在锻造一个坚强的灵魂。这次去珠峰前,他就和我说:“可能我太想去珠峰实现登顶之愿,反而不好实现。”到珠峰后,从4号营地到5号营地运输物资途中,他对我说:“没有办法,我感到我的体力和适应性不足,这次登顶是不可能的了。”他说这些时心里很苦。
成功是辉煌的;失败,同样是辉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经受的就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成功的喜悦,只是很短促的,马上就会迎接又一个考验、又一个失败。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勇士,将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