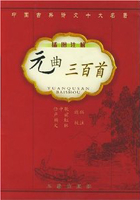他们是美的发现者,但在这发现的途中,他们所经历的无数悲剧和喜剧曾在这里的大自然之怀上演,他们勇敢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被这冰清玉洁般的圣境所吸引和感动!于是,他们的性格和人格也悄然变得如此真实透明。
全队休整几天,准备突击顶峰。
这是在珠峰最惬意的日子了。
整个大本营地区成了一个“小联合国”,韩国、爱尔兰、德国、美国等来自各国的登山队东一片、西一片地将营地扎遍了珠峰下的古河床谷地。而最醒目、最大的营地,还是中国的。所以,客人常常来我们营地“串门”。我们也去他们营地“回访”。任何人相见,都笑眯眯地互相问好。
我看到一些老外,从帐篷里搬出个凳子来,美美地面对着珠峰,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享受”。
两位美国姑娘,看到珠峰既激动又兴奋。她们进了老曾的帐篷,老曾和黄国治用茶和饮料热情招待她们。她们感动得要求给中国登山队当义工,就是想在珠峰多留几天,多度过几天“金子一般的美妙时光”。老曾笑着谢绝了,给她们解释了半天,又送她们出来。我们称老曾和老黄是“大堂经理”,他们每天都要热情接待很多客人。
看老曾钻进了帐篷,我就跟了进去。
我发现老曾的脸色很难看,他手捂着胸部,摇头,然后躺下,闭上了眼。我问他:“老工人,是心脏吧?我去叫队医……”“不用。我自己知道,熬过这阵子吸点儿氧就好了……”他摆摆手。
老曾的两鬓已经花白了,他严重的冠心病根本没有好转,却非要从医院逃跑出来。这一次进藏,只会加重他的病情,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与九年后他在家中心脏病突发而猝死有很大的关系。他让所有的亲人和山友悲痛至极。
他闭着眼睛吸氧。
又是心脏突然间歇跳动?进山前我们体检,他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心脏间歇跳动被医生抓住。谁都知道,一旦心脏这个主机出了问题,是很难通过治疗好转的。
吸完氧,他坐了起来,把氧气罩一摘,脸色好看多了。他笑着对我说:“好啦!刚才死了,现在他妈的又活啦!”这就是老曾,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这里职位最高的干部。
但很奇怪,没有任何人把他当“领导”,都把他当成慈祥可亲的兄长。所有的队员,都称他“曾老工人”,称老于为“于老工人”。为何出来两个“老工人”?在山上,他们都爱穿一件很旧的背带工装裤,一会儿帮人修理相机,一会儿雕刻石头,一会儿修车……从来没有闲的时候。几年前,从大学里出来的王勇峰、李致新、马欣祥刚进队不久,就对老曾说:“老曾,你哪里像领导?整个就是一个老工人啊!”于是,这名字就叫下来了。
老曾的老伙伴于良璞也是。在南迦巴瓦峰,每天晚上他都给当地小村庄的藏民修理半导体收音机。藏民非常感谢,送来了一些核桃和鸡蛋。核桃和鸡蛋我们吃了,一看到老于在灯下忙活,我们就气他:
“老于,又在骗人家少数民族的核桃和鸡蛋啊?”老曾和老于是老搭档了。1974年,两人带领珠峰第四登山队从北京进珠峰。老于是书记,老曾是队长。那时是坐大卡车走,翻山越岭要跑十几天,而老曾却是一直开着挎斗摩托跟着汽车走的。进了青海的途中,老曾让老于上了他的摩托。老曾在前边开,老于背着一支卡宾枪坐在后面。见到黄羊了,老曾边开边喊:“打一只犒劳犒劳大家!”当时黄羊是可以打的。老于就把枪架在老曾的肩膀和脖子上,咣咣两枪。老曾大叫:“哎呀!羊没打着,子弹壳崩着我的耳朵啦!”老曾的爱好多,手特别巧,驾车、驾摩托、照相、摄像、做动植物标本、唱歌(他最喜欢苏联歌曲,一次给我唱《伏尔加纤夫曲》,浑厚雄壮,让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列宾的那幅最著名的油画),甚至当导演!
那是1980年前后,一家电影制片厂进珠峰拍摄故事片《第三女神》,老曾被请来当高山顾问和高山摄影。导演带着一帮演员来到珠峰后,高山反应强烈,事故不断,女演员天天在帐篷里哭,最后拍摄工作进行不下去,停工了。老曾一看,急了,越俎代庖召集全体人员开会,把他们痛骂了一顿,最后说:“从明天起,我来指挥!你们都得老老实实听我的!”他成了总指挥、总导演!而每个人真的全听他的指挥,电影终于拍摄完成。下山时,一个从部队借来的司机战士不小心将车撞在了石头上,人没出事,但车撞坏了。这个战士急得哭起来,怕回部队没法交代,要受处分。老曾拍拍他的肩,转身马上召集大家开会,说:“都给我听好啦,今天这车,是我老曾开的!责任在我,是我出的事,我来向部队交代!谁要是敢走漏半点儿风声,我对他不客气!记着,这件事都给我闭上嘴,给我保密!”他真的把这事兜了下来,亲自向部队说明,而那位司机战士被免掉了责任和处分。
于激流中力挽狂澜,敢做敢当,这才是爷们儿、男人!
他最恨那些假大空、虚招子。1984年在阿尼玛卿登山的攀登途中,山上的雪崩差点儿把他活埋了,幸亏王勇峰和李致新把他从雪里扒了出来。回到营地,一个女队员代表一家报社对他采访,请他说说被埋后脱险的感想:“这时候想到了什么?”老曾气坏了,吼道:“想什么?想你!”他爱动物。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找不到鞋了,拍着帐篷杆向外面大声喊:“小黄!我的鞋呢?我的鞋!”“小黄”是前面提到的那只小狗。
小黄一听,马上把他的鞋叼进来了。
老曾一穿:“妈的,谁让你给我尿啦?哪里不能尿,往鞋里尿!”看看小黄,又笑着说,“行,尿就尿吧,还热乎呢!”登山结束后,返回的第一站是协格尔。老曾从车上下来,牵着小黄进宾馆的院子。满院的大狗呼地全站了起来盯着小黄想咬,老曾乐了,像一个老鬼子一样左右晃着,牵着小黄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大狗们一看老曾的气势,全都老老实实乖乖地趴下了。小黄也挺着脖子,很牛气地穿过它们的队列……看老曾的心脏病缓解了,我对他说:“老工人,我的事该提上日程了吧?”“哈哈,我知道你又来了!”老曾说,“没门儿!”我跟他要求过几次,希望去山上的营地看看。我私下的愿望是能到3号营地,海拔7000米左右。
登山是有很严格规定的,进队,就是队里的一员,必须服从指挥。我太想去体验一下山上营地的生活了,再艰苦再危险也愿意。但是,全队就我一个记者,每天要向北京和台北发稿、联系,我无法脱身。队里给我的规定是,上山,也不能超过海拔6500米,因为曾经有一个新影厂的记者就死在这个高度。但只要让我上去,能攀多高,也就自己说了算了。否则,来一趟珠峰,总在海拔5100米的大本营窝着,心有不甘。这两天休整,不用发稿了,能有这机会吗?
队员们在行军修路的时候,我是无法提此要求的,因为如果一旦在山上出了问题,队员们为了救你,会影响全队的攀登进程和计划。现在他们休整,我觉得可以了。
老曾还是不同意:“不行,你没经过训练,就是不出事,上去也会拖累别人的。”过了一会儿,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跟老于说说,明天如果天好,让他带你们去趟冰塔林吧。”冰塔林!
“怎么样,我的大记者,满意了吧?省得回到北京骂我,进一趟山让曾老工人给软禁了!告诉你,别看这冰塔林,一般人能进去的也不多,你试试就知道了。”这是真的,一般人就是到了珠峰,高山反应一来,就马上撤了,哪有体能去冰塔林?几天之后,从台湾来了20多个人的旅行团,名义上是来慰问我们的。他们是飞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从珠峰南侧乘汽车进来的。到了我们大本营后,他们激动地又欢呼又拥抱,说要在珠峰好好玩几天。一个女记者对老曾说:“圣母峰好漂亮啊!”老曾笑了,说:“你们今晚会更漂亮。”果然,当晚高山反应袭来,很多人头疼得大叫快撤,马上就撤。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上车了,老曾问女记者:“圣母峰漂亮吗?”“好恐怖!”老曾说:“多少人想去冰塔林,去得成吗?这是给你吃小灶啊!”我说:“熊掌的不给,鱼的凑合凑合的干活儿!”“哈哈,那可是条美鱼啊!”我还是少年时,看过1960年首次攀登珠峰的纪录片,被电影中冰塔林的神奇所吸引。那如同一座冰的天堂,仙岛宫阙,梦幻迷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瑰丽奇绝,那真的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梦。但近年来,听很多登山者说,随着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频繁,当年那宏大壮观奇绝之美,已在慢慢消融。近年去过的一个老队员说:“已经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但还是举世之美啊!”次日上午,老于带我们出发了。我、队医李舒平、台湾队摄像李诚彦和小林、一个姓游的台湾老登山者,还请来三个藏族牦牛工。摄像机等较重的设备,只能请他们帮助运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