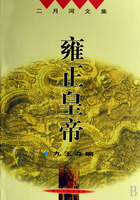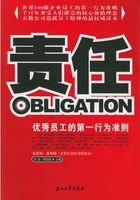庄庄美娴第一次发现除了去港口,还有用得上那个黑色假发的时候。
销售部经理"马屁刘"--她的直接领导,为了使销售部的业绩更上一个台阶,想出了一个不太高尚的主意。他把所有销售人员都派出去,见到高级写字楼就进,把里面所有公司的名称都抄下来,然后打电话过去询问租金报价。这就是他所谓的"一箭双雕"的"商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挖墙脚"。
庄美娴很不走运地成了一个"商业间谍"。尽管她每天想尽办法变换造型,今天是奥黛利*赫本的高贵,明天是索菲亚*罗兰的性感,后天是酒井法子的清纯,大后天是蔡琳的可爱,大大后天是布兰妮的大胆......可是她忘记了一个关键--她那一头璀璨耀眼的红发!她的头发成了樱木花道一样的招牌标志,写字楼的保安就算是白痴,也很难看不见这个在每层都要停一下抄抄写写的红头发女人。于是,她那写满"商业机密"的小本本总是被没收,她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
庄美娴很聪明,她很快想到了问题的结症--她的红发,于是便把那个东方淑女的黑色假发戴上了。她还做了更充分的准备,随身携带一个录音机,看到招牌随时口述记录,回去整理就是了。而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现代化写字楼全都装了摄像头。庄美娴在如此酷热难耐的日子里整天戴着假发,头皮都要起痱子了。她痒得实在受不了了,趁电梯里没人搔了一下,红色的小卷毛一不留神就露出了那么一小撮,而电梯再次停的时候,迎接她的人就成了保安。庄美娴休想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之中。
"没办法,我实在是太漂亮了,想混同于一般群众是不可能的。"庄美娴第N次被保安抓获时,一边微笑一边摇头晃脑地这样安慰自己。回头望一眼这幢二十几层高的写字楼,里面有八十多家企业,几天来的辛苦努力全泡汤了。阳光跳过楼宇刺进她的眼睛,她知道她撑不住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她逃似的跑了起来,躲到一个阴暗无人的小巷,失声痛哭。
"庄美娴?庄美娴!你怎么在这儿?"
庄美娴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那人的鞋子,没理会,继续低头翻自己的包。那人递过来一张面巾纸。庄美娴喃喃地说了声"谢谢",抬起头来。怎么这么丑的样子偏偏让他看到?匆匆路过的行人偶尔会好奇地看一眼他们,她使劲儿咽了一口唾沫,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翁先生......我很好。"
"叫我'阿飞'吧,这又不是在公司。你怎么哭了?"
这话问到了庄美娴的伤心处,她的眼泪再次像小溪一样涓涓成行。
阿飞飞快地咀嚼着嘴里的口香糖,四下环顾了一圈,说:"我的车就停在附近,你等我一下,最多五分钟,我们上车再说。你一定要等我,最多五分钟!"
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不放心地回头看一眼,直到自己消失。
庄美娴掏出包里的小镜子,她涂的是防水睫毛膏,游泳都不会掉色,需要专用卸妆水才能洗掉。哭过的女人更要注意自己的仪态。
这五分钟比想象中要漫长许多,当那辆银灰色的克莱斯勒君王停在她面前按喇叭时,庄美娴觉得自己已经一百岁了。
"你想去哪里?"阿飞透过反光镜看着坐在后座上的庄美娴问。黑得发蓝的假发挡住了她的脸,她呆呆地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什么。
"我哪里都不想去。"
"那就跟我走吧!"
这是一座还未被众所周知的山,所以才保持住了它的自然风貌。车子停在山的这一面,看不到山荔学院的那一面。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映在车子的前盖上,庄美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么陌生,就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她问。
"因为我到这里以后还没来过。想陪我一起走走吗?"阿飞回过头问她。
"下次吧,周末,那时应该有缆车可以坐。"
"你应该多走走路,多出一些汗,身体里的水,不是只能从眼眶里溢出。"
阿飞把口香糖放进嘴里,率先开路。
沿着碎石子铺成的小路上山,庄美娴觉得自己是个苦役犯,正被1940年的日耳曼人押着去蹚地雷。她的防晒霜防晒指数只有15,这会儿感觉皮肤快被晒破了。阿飞把西装脱在车上,可即使是这样,衬衫也很快湿透了。天又热又闷,空气都好像加了包装,沉甸甸的。身体里的每一滴水真的就这样被榨干,庄美娴再也没了哭的欲望。
"可以吗?"阿飞解开了衬衫的扣子。
"当然。真羡慕你们男人,可以光着背。"
"是啊。"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
"在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背?"
"不,我只是希望我能用实际行动教会所有男人怎样去爱一个女人。"他们对视了一眼,她继续说,"当然,还可以光着背。"
他们笑了起来,脸都很红,大概是热的。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无话可说的时候就拼命走路,他们很快走到了缆车的终点站,只是苦了穿着高跟鞋的庄美娴。黄绿两色相间的缆车吊在电缆上,小小的办公室像是用积木搭的,房子背阳的地方竟还种上了葡萄。
"我们一共用了75分钟。"阿飞看了一眼手表说,"感觉真舒服,像踢了一场足球。"
庄美娴出于礼貌对他笑了笑,依旧望着远处。山那边就是山荔学院,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建设中的礼堂。未竣工的建筑物周围布满脚手架和五颜六色的小旗子,那样明目张胆地张扬它卓尔不群的未来,像个肤浅的肚皮舞女郎,摇摆,扭动,旋转,热情洋溢的肚皮下是她伟大的子宫,让人浮想联翩。
"你看的地方是哪儿?"阿飞站到她身旁问。
"心血,智慧。"庄美娴没有理会他疑问的目光,像是在自言自语,"那将是这座城市最伟大的建筑,我相信它决不会是图纸上的那副鬼德行。我了解他,他不会让它变成那个样子的。一定不会!"
山上开始起风了,天气凉爽了一些,人变得很容易满足,笨重的缆车偶尔也会被风吹得动一下。看着树枝舞动,庄美娴好像已经忘了所有的不快。她扯下假发垫在屁股底下,抬起头望着阿飞。
"你的裤子很贵吗?为什么不坐下?"
阿飞站着没动,他被眼前的一切迷住了。太阳在他的视野里一点一点地矮下去,当最后一滴阳光消失的时候,他低下头,他发现,在他的腿边,还有一颗火红的太阳。那么,他心里的沉重是否也可以减轻几分呢?
"你的头发真好看,那个假发不适合你。"他由衷地说道。
庄美娴看着自己的脚趾笑了一下。
"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他们都嫌我这个颜色太夸张了。"
她迅速看了他一眼,又低下了头,一队蚂蚁忙忙碌碌地走过,整齐有序。每天都这样搬来搬去的,从来不觉得厌烦。
"其实,我也认为他们说的没错,这个颜色确实太夸张了。因为我的头发,别人都很难接受我,我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糟。可如果我没有了这样的头发,我就会害怕没有人能够看到我。"
"相信我,他们都错了,你也不要怀疑自己。你的头发很漂亮,很美的那种漂亮。"
"为什么只有你这么说?"
这是希望之后的失望。大多数人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庄美娴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心情沮丧的她用小石块给蚂蚁挖了一道深深的壕沟,阻碍它们前进,想让它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无论变好还是变坏,有改变总是好的。
"快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阿飞突然拉起她的一条胳膊,"天已经变了,你看西南方的那块云,最多十分钟,雨就会来了。"
"如果真的会下雨,十分钟后我们正好被淋在那棵老槐树下,它是整座山最高的树。你不觉得雷击比淋雨的危险更大吗?如果雨注定要来,何不欣赏一下雨中的山林?" 庄美娴怡然自得地说着,一回头却看见阿飞抱着一块石头冲向缆车终点站的办公室。"喂,你要干什么!"
一声巨响,玻璃碎了一地,阿飞用衬衫包住胳膊把手伸进去拧开了门。
"快进来吧,这是一场大暴雨,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
他的话音刚落,密密实实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庄美娴捂着头跑到屋檐下,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又冲进雨中。
"你还要那个假发干什么?快进来吧,会被雨淋病的!"
庄美娴像没听见一样拿着假发蹲在地上,似乎在找什么。
"你在干什么!"这么大的雨,几秒钟就可以把人淋个透心凉,雨声压倒一切,阿飞不得不用喊的。
"我在找刚才那些小蚂蚁......"
"别傻了,它们早不在了!"
"可是我把它们的路切断了,我怕它们回不了家......"
她抬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他,他分不清她脸上的究竟是什么水。
蚂蚁和她,哪个更可怜?
阿飞惊喜地发现他竟然还有同情心,那么,当他看到那些把全部财产都压在那张图纸上的业主,最后愤怒地挥舞拳头、无望地哭泣、绝望地哀号时,他的同情心又在哪里呢?
雨把Colin送到了银子的咖啡店,吸引他的当然不会是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店面,而是硕大的玻璃窗里呈现的那架乳白色的施特劳斯牌钢琴。他只需瞟上一眼就知道那是施特劳斯的光芒,雨中的它还是那么熠熠生辉。他在伦敦的餐馆里整整弹了三年寂寞的钢琴,他当然认得。
Colin的父亲是小学音乐老师,从小就把他按照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模子培养。他却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冲锋打仗这类集体游戏,父亲必须把他捆在琴凳上才能保证他的手指可以挨上琴键,有时还不得不对他进行一下"鞭策"。是Colin不屈不挠的游戏精神让父亲最终放弃了这个幻想,明白了有些事情永远是梦--"他连《致爱丽丝》都不能完整地演奏。"父亲逢人便讲,仿佛这是天底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年Colin8岁。到了伦敦以后,同乡介绍他去餐馆做清洁工,每天从凌晨3点工作到凌晨6点,每小时4英镑50便士的报酬,而一份麦当劳巨无霸套餐的售价是4英镑20便士。那里就有一架乳白色的施特劳斯牌钢琴,无人弹奏。因为老板的女儿威胁说,如果再让她学钢琴,她就把它砸了,老板这才肯把它抬到店里来附庸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