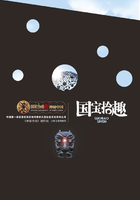1964年。
与年轻的共和国一样,三星堆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光。
也许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天人感应”,“政通人和”。此时,在沉寂数千年之后,面临和煦的春光和舒展眉头的民众,20世纪30年代偶尔展露身影而平素深藏于地下的三星堆文明似乎终于忍耐不住,渐渐地、羞答答地又展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同年春天的某日,月亮湾的几位农民在距离燕家大院出土玉石器地点五六十米处挖粪池时,又发现一坑有成品、半成品的玉石器,其中还有石坯。
三星堆文明,似乎在向人们发出某种信息。或许,四川考古的春天已经来临?
然而,又应了另一句老话,“好事多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4年,当人们对十多年前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记忆已经逐渐淡忘,偶然间,当地农民又在附近梭子田发现一坑磨石。时任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的敖天照回忆,该坑为石板封闭,坑口有1米长、50厘米宽,约50厘米深。坑内出土的磨石为大小卵石数十件,青黄如玉,坚硬细腻,均有打磨面,当为作坊使用的加工工具。
1976年9月。广汉县高骈公社机制砖瓦厂挖排水沟,发现玉器三件。时任广汉县文管会干部的敖天照,立即与省考古队的王有鹏赶至现场清理,又先后发现刀形玉器和石矛,以及青铜牌饰。该地历史上曾是“石鼓寺”建筑遗址。敖天照认为应是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一处古蜀国的小型祭祀坑。
此次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青铜牌饰,它的出现,与后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的铜牌饰有类似之处。其所出土的刀形玉器、斧形玉器(玉戚)、石矛和青铜牌饰,均显示出较早年代特征。
可惜的是,这些重要发现,在当时恰如“泥牛入海无消息”,连一点涟漪都未出现——长期的政治运动,四川考古文博学界的专家学者已经麻木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不过,表面平静的河面下暗流涌动。具有远见卓识的冯汉骥教授,就是在最困难之时,也未放弃对学术真理的追求。
不久,冯汉骥教授与童恩正合著的学术论文《广汉三星堆玉石器》在刚复刊的《考古学报》杂志上发表了。而张勋燎,冯汉骥教授的另一个弟子,著名考古学家,也对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有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冯汉骥和童恩正教授主要对1929年至1964年出土的玉石器进行研究,但重点讨论的是1929年出土的玉斧、玉璋、玉琮、玉钏和石璧五类器形。并分别论述了这些器物的形状及可能的用途。认定它们基本上都属礼器类。
他们并对以前的相关考古发掘作出判断:
在秦灭巴蜀以前,四川地区是被称为“夷狄”之国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通为郡县”。广汉玉器的出土,说明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了与中原相似的礼器、衡量制度和装饰品。
他们敏锐地察觉,三星堆古遗址对于研究蜀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认为它再一次证明了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而张勋燎先生的文章,将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与历史上的度量衡联系起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参加1963年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教研组(后改为教研室)的林向、宋治民、马继贤老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沈仲常、王家佑、李复华等人也在此期间做好了学术准备。
四川考古学界,在默默地等待出现考古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