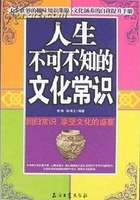任凭皇弟将自己软禁在睿王府,御承觉得,也算暂时闹了个耳根清净,算不得什么委屈。
御轩耳里听着皇兄的话,心里直堵得慌。暗暗吁了口闷气,他很严肃地道:“若皇兄还是这等心思,恐怕就只能留你到初八喝完喜酒再回康王府了。”
对于弟弟的言外之音,御承自然听得出来。御轩这是怕他横刀夺爱,搅黄初八他们的婚事,遂将他扣下,以求心安理得。
“你就不怕,这几日,青青那丫头趁你不注意来书房与我见面?如此,我岂非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御承高深莫测地道,让人听不出他此话是戏言,还是威胁。
御轩不以为意:“在我眼皮子底下与你见面,总比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被蒙骗来得好。”
“你对她是真心的?”御承皱了皱眉,之后又睨着弟弟,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
御轩反问:“你对她是假意?”
“你不觉得,这是个弱点?”御承不答,反而又抛出个问题来。
御轩嘲讽地将唇角提升了三十度,而后不声不响地走到书架后,两手各拎了坛陈年老酿过来,递了坛给御承,自己留一坛。
御承顺手接过酒坛子,举起坛子,将坛口翻倒下来,对着嘴,咕噜噜,豪爽地喝了起来。醇香的酒水倒得他满身都是,浸透了一身名贵华丽的蟒袍。
看到皇兄似宣泄般饮酒,御轩只是眸色沉了沉,随后也以同样的方式,气儿也不歇地,一口将坛中美酒终结。
“啪!啪!”
接连连声巨响过后,地上多了两摊碎陶片。
兄弟俩对视一眼,而后同时起身。御轩开了门,疾步走了出去,但没有再将门关上。
是夜,丞相百里荣浩造访睿王府,将御轩要的资料送上。
厚厚的一沓纸,将百里一族近三代以来,女眷的生平死因都跃然纸上。
“王爷对青青的用心,老臣铭感五内。”依着百里荣浩的智慧,他岂会不知御轩要这些资料的用意?不管最终能否如愿破解密咒,王爷的心意都令他动容。
御轩却道:“丞相不必如此。此事断不要让旁人知晓,若有消息,本王会第一时间告知丞相。”
“不必了,既然王爷愿意出手,微臣便将此事全权托付王爷。王爷有真龙之相,必能护佑青青。”甭管百里荣浩平日里是个多么德高望重的宰相,每每提到百里家这点儿事,他都会像霜打的茄子焉不溜揪的。这样的他,又有什么勇气自揭伤疤?
御轩闻言,不解地问道:“在朝为官,谁不知审时度势的道理,何况丞相乃两代元勋,怎会如此偏重本王?若最后得势之人是御承,御墨……”
“老臣看人的眼光,不会有错。如若不然,当年您皇祖父也不可能临终托孤,将满朝文武屏退,独留老臣叙话。”百里荣浩似乎知道点儿什么内情,但不便明说。
御轩也不强人所难,送走了百里荣浩,自个儿关在房里研究起手上这沓厚厚的资料。
越看,他的心就越沉,渐渐地,他约莫可以体会到百里丞相的心境了。
按说,百里家娶进门的媳妇,无一例外都是名门闺秀,健康漂亮,妙龄年华,怎么进门没几年便英年早逝?而且,一个个死因各不相同,让人很难从中寻出端倪。
从这些资料中,实在找不出任何与魔煞门的关联来。莫非他猜错了,百里一族的惨状与魔煞门无关?倘若如此,魔煞门此次欲行邪门左道加害的人,不是青青?如若不是,他们又怎会盯着青青不放?
“叩叩叩!”
御轩沉重的思绪被几声叩门打断,厉声问道:“谁?”
“这么晚了,你还亮着灯,真够勤政的。”青青打趣的声音传来。
话落,不等他回应,她已经推开门进来。反正她都叩过门了,他也应了她,就算默认她进来了。
御轩刚收拾完手中的资料,放妥,青青的身影便映入他的眼帘。
“你紧张什么?我又不是来抓包的。天儿太热,睡不着,起来走走,见你这儿还亮着灯,所以过来看看。”说话间,她亮晶晶的乌眸转啊转,目光飘啊飘,活像个密探似的。
凤翔宫。
“皇上,臣妾给您缝了件褂子,您试试,这料子是真丝的,夏天儿穿着凉快。”皇后坐在凤榻前,手里拿着件明黄的褂子比划着,一脸的笑意,眼中尽是柔情。
夜已经深了,皇帝有些坐不住,心早就飞出了凤翔宫了。
于是,他有些不耐烦地地道:“你是皇后,一国之母,这些针线活,让绣工们去做,朕还有事,你早些安歇。”
“皇上……”皇后可不那么好打发,连忙起身,快步走上去,拉住皇帝的胳膊,软声道:“臣妾白日里要管理后宫,晚上好不容易逮着点儿空闲,连熬了好几宿给您缝的褂子,您好歹领领臣妾的情不是?”
“你搁着,朕改日再来试穿便可。”皇帝是真想走了,言语都有些心急的味道。
皇后心里委屈,她还不知道,皇帝这么急着走是为什么?还不就是去月清宫跟庄妃缠绵恩爱?
可今儿不行,说什么都不行!甭说是轩儿托她绊住皇帝,即便轩儿没这意思,她这会儿也不准备放人,心里堵着一股子气呢。要说白天他忙也就罢了,深更半夜的,他还走什么走?在这凤翔宫住一宿,能怎么着?
“皇上……”皇后眼眶有些湿润了,苦笑道:“臣妾是人老珠黄,不及当年了,可我们终究是结发夫妻。皇上连这点儿情面都不给臣妾留么?想当年,臣妾做姑娘时,我们也曾郎情妾意,如胶似漆过。那时,皇上还是太子,臣妾给皇上也是缝了这么件褂子,皇上可着实高兴了好久,如今……哎,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