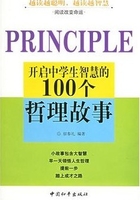天亮了,我从浅眠的状态醒来,在这温泉旁边,即使是极寒的夜也不觉得冷,踏着露水我走在来时的路上,很快就回到了宿营地,他裹着毯子假寐。我知道他是醒着的,但我也懒得和他计较,看向狼群,果然少了色勒莫和那只美丽的母狼。
等太阳升起来,空气又充满了热度,我拿了陶罐去了孔雀河边,继续捞鱼,没一会儿,就看见他在岸边,我对他笑笑,他低下头,捡起被我甩到岸边的鱼,开膛破肚,出奇地用力……
三天后的清晨,色勒莫和母狼回来了,它兴奋地蹭着他,那头母狼向坐在地上的我靠近,开始我有些不安,但看到母狼眼中的目光,我轻笑,也许它为了不让我再接近色勒莫而看紧我吧。于是我大方地抱住它:“你也该有个名字才好。”我揉着它一身雪白的皮毛,它安静地趴在我的腿上,“就叫凌雪吧!”
它眨了眨眼,就当它是同意了吧。
再次上路,我们一如既往的沉默,一路行来,虽算不上千辛万苦,也绝对够受罪了,偶尔的城市、河流、山川、沙漠、绿洲让我的玉足已经磨破了N次,结了厚厚的痂。就这样走了2个月,还以为永远到不了头,却突然看到远处一个巨大的都城。
冒顿回头对我说:“那就是月氏国的边塞了,穿过月氏国,就是我们匈奴的土地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不是从这里逃出来的吗?还要穿过去这里,不能绕道吗?”
他摇头,冷峻的脸上写着坚毅:“这里最近,虽然危险,但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点头,话虽不错,可毕竟凶险,我的眸中露出了担忧。
他冷冷地一笑:“我讨厌你的担忧和同情,就如你讨厌我的冷笑一样,所以你不要再对我这样。”
我撇撇嘴,低头看着大腹便便的凌雪,说:“算算日子它该生狼崽了。”
他点头:“今晚我们先在这树林里,明天一早我们就进月氏国,等色勒莫它们的狼崽能够跟上狼群的时候,它们会去匈奴的王庭与我们会合。”
无可辩驳,我跟在冒顿的身后走进茂密的树林。和他同行了2个月,除了那次温泉边的对话,我们不再探究对方的身世,只说些关于行程的话,然后沉默以对,我微笑,他冷笑。
这将是个不眠的夜晚,色勒莫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到的树洞,让群狼衔来松软的干草,给凌雪做好了生产的准备。
吃过晚饭,我坐在树洞对面的歪脖树的树干上,冒顿在树下坐着,等着小狼崽的降生。
这晚的月亮很园,月光很亮,透过密实的树冠,仍在林中洒下斑斑点点的光芒,沉默的空气在这样的夜晚真是有些浪费,于是我问冒顿:“月氏国是怎样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祁连山下有一片绝好的牧场,月氏国的国都是座大城,城内是重重叠叠的石头垒成的房子,男人裹着头巾,女人蒙着面纱,和你们精绝国差不多,但是人来人往,非常繁荣,几与中原相同。”
我点头:“月氏国地处贸易通道的中心,自然更兴盛些。还有呢?”
他冷笑:“都在天空的底下,能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了他们住房子,我们匈奴人住帐篷。”
我撇嘴:“长得就不一样,你们匈奴人的身材高大凶悍、肩膀宽,脸都比较大。”说着我低头看他,正对上他不屑一顾的眸,连忙说:“你的脸还好啦。”
他别过脸,冷哼:“应该是男人对女人的脸比较有兴趣才是,怎么女人对男人的脸也这么热衷。”
我没接他这句话,而是继续问:“月氏国的女人美吗?”
“月氏国的女人都很美,因为她们那有座胭脂山(焉支山)。”说完故意看我一眼。
“切!连原因都搞清楚了?”我冷嘲。
“胭脂却只能美丽她们的脸。”他说完起身向树洞走去。
我也好像听到了奇怪的声音,跳下树来,凑过去,天啊,凌雪生出第一个“宝宝”了……
天就要亮了,凌雪生出了第九只小狼,在它撕去胎衣,咬断脐带后,疲惫地趴在一边喘息。我看到这几只小狼都挤在凌雪的腹部吃奶,它们都还没有毛,除了最后一个出生的小狼是纯白色的,其它都是银灰色的。
缓过气力的凌雪开始逐一舔舐这几只小东西,等到最小的白色的小狼的时候,它突然停住了,发出呜咽的声音,色勒莫连忙跑进树洞,当它看见那个白色的小狼的时候,也停住了,继而趴下来磨蹭着凌雪的脸。
它们的眼中有惊喜,也有疼惜,还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情,只是这唯一的白色小狼最为虚弱,我不由得叹息。
冒顿站起身来,也拉我离开树洞,对我说:“走吧!”
出了树林,我们向月氏国走去,路上,我依旧想着那只弱小的白狼,连连叹气,冒顿回过头来望着我说:“那只小狼会渡过最为悲惨的‘童年’还会成为孤独的‘少年’,但是它会成为另一群狼的首领。”
我讶然,他回身继续走,然后说:“狼群中一定有一匹地位最低的狼,就是狼崽中最弱小的一个,狼群上下都会对这它加以虐待,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把它置于最后的位置,尤其在进食时,而这匹地位最低的狼则一定会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然后独自到别处冒险,成为孤狼,它最终会把自己磨砺得非常强壮,找到一个配偶并建立一个新狼群,或像王者一样归来,打败老狼王,统治狼群,尽显王者风范。”
从冒顿的话中,我终于知道了他那天所说的该怎样活着的真正意义,我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