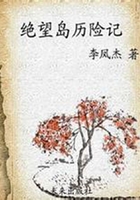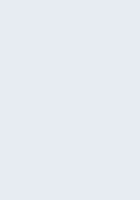珍珍小月以后,长岭怕何长山埋怨她,反复叮嘱珍珍,小月的事,千万不要对何长山说。
何长山白天又来过两次,都是刮风的时候。何长山来了以后,什么话也不说,直接就把珍珍搂住了,搂得紧紧的,好像要把她化在怀里一样。长久的搂抱之后,接下来就是狂热而猛烈地亲吻。珍珍在何长山的怀里颤抖着、心酸着……可是,当何长山想再进一步时,珍珍都坚决地拒绝了。
火着得正旺的时候,被生生地泼灭了,何长山既扫兴又不甘心,他像个孩子似的向珍珍祈求,珍珍,回去以后,我一次都没有和大凤……什么事,就怕开个头,自从那次以后,我净想你,想得晚上睡不着觉!何长山期期艾艾地说着说着,就又蹭到珍珍的身边,把头埋在珍珍的怀里。珍珍既心醉又心碎,她抚摩着何长山浓密的黑发,眼里忍不住落下泪来,那一团模糊的血肉一直在珍珍的脑海里闪现,她几次张口想把打掉孩子的事告诉何长山,但想想长岭的叮嘱,她都忍住了。何长山用头拱拱珍珍的胸脯,像是抗议又像是孩子向母亲撒娇。何长山比珍珍大六岁,在她的面前,何长山总是稳稳当当的,珍珍从来不知道,他这么孩子气。珍珍特别喜欢何长山这个坏坏的动作,她的心总是被他拱得像个小兔子一样蹦跳起来。可她不敢有任何的回应,她怕自己管不住自己,只能像家长一样和何长山讲道理,长山哥,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想,可在长岭姐的地窨子里,我不想……那样了。
何长山冷静下来,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珍珍,你别说了,我都懂,是哥不好。何长山这么说了,可珍珍总觉得没有依从何长山好像欠了他什么似的。
何长山走的时候,珍珍从后面搂住他的腰,絮絮叨叨地道歉,长山哥,对不起,是我不好,你忍忍啊,等咱们结婚了,你想啥时候要,我都给。
何长山走了以后,好长时间没来。虽然何长山走的时候告诉她,法院最近要调解离婚,这段时间不来看她了,但是,珍珍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总觉得何长山这么长时间不来,好像与她拒绝亲热有关。想起何长山说的那句“什么事,就怕开个头”,珍珍就更不安了,觉得自己招惹了他,让他有了念想,又不依从他,是在折磨他。珍珍对何长山有了一种深深的愧意和怜惜,这种愧意和怜惜慢慢转化成了一种强烈的想念,无论白天和黑夜,珍珍满脑子都是何长山祈求而渴望的眼神。
因为这种强烈的想念,珍珍觉得地窨子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难熬了。她每天趴在地窨子的墙壁上看墙上的报纸,报纸上枯燥的新闻都被她背熟了。实在无聊,她就在地上胡乱画竖杠。双数代表何长山来,单数代表着不来。如果数的是单数,她就会沮丧难过。如果数的是双数,她就会有一刹那的喜悦,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期待,当然这样的期待十有八九会落空,接下来就会是更深的落寞和失望。
以前珍珍最讨厌刮风,觉得刮风脏。现在她却天天盼望刮大风,因为刮大风的时候,何长山可能要来。她还希望刮东风,一刮东风,她就能听到木庄的高音喇叭广播。从喇叭上,她能听到木庄的消息。台乱在喇叭上广播得最多,台乱带人砸了她家,刚开始听到台乱广播,珍珍觉得生气。但听得多了,她不觉得生气了,反而有点亲切。台乱的一段广播,让珍珍高兴了好几天。台乱是这么广播的:“昨天晚上,夜个黑介,十二点以前,半宿以后,有人偷了六队的长果和花生,严重地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经大队研究决定,一定要按着护林公约严肃处理!”珍珍听了,笑得差一点喘不上气来。这个台乱,真是颠三倒四,不光来回重复,还驴唇不对马嘴,偷花生和计划生育有啥关系?还按着护林公约处理呢,真是笑死人了!
台乱这段广播珍珍听了一遍就记住了,心情烦躁的时候,她就默念这段广播,念着念着她就会笑起来,这段广播成了珍珍在地窨子的娱乐。一天晚上,长岭下来送饭,珍珍把台乱的广播给长岭念了一遍,长岭听了也说笑得肚子疼。不过笑过后,长岭鄙夷地说,就台乱的水平,还当大队长呢,给长山拾鞋也不够格!
什么事也就是一个新鲜,新鲜劲儿过了,也就淡了。台乱的广播,珍珍念了几天,也就觉得没多少意思了。于是她就盼着,能在喇叭上听到二哥的声音,可是一次也没有听到。她还盼望能听到何长山的声音,可是一想,何长山不当支书了,喇叭上怎么会有他的声音呢?
天一天一天的长了,地窨子里潮气又慢慢地重了。又一个难熬的夏天到来了。
地窨子里潮热得几乎让人窒息,珍珍手里的蒲扇一天到晚几乎没有停过。一天到晚,珍珍身上都汗渍渍的。由于长时间不能洗澡,她的身上有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到了晚上,珍珍知道没人进来,干脆把衣服脱了,可是嗡嗡乱叫的蚊子围着她乱转,她的身上脸上都是蚊子叮咬的红疙瘩,痒得难受。实在受不了,她就点燃长岭拿来的干蒿子。地窨子空间小,蒿子点燃以后,很快就烟雾弥漫,熏得她两眼冒泪。珍珍从小就怕虫子,看到虫子她就浑身哆嗦,地窨子顶上有很多蝎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到珍珍的头上。珍珍已经被蝎子蜇了好几次了,那种钻心的疼痛,让她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一到晚上,她几乎不敢睡觉,顶上掉一块土,也会吓得她满地打滚,失声尖叫。她一会儿挪到这儿,一会儿又挪到那儿,可她却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哪儿都有蝎子在爬动。到了白天,她就瞪着眼瞅着地窨子顶上仔细看,地窨子是用稻草棚顶,到处都是缝隙,珍珍根本找不到蝎子藏在哪儿。
珍珍实在无法忍受对蝎子的恐惧,等长岭送饭走了以后,她就偷偷到地窖口的梯子上趴着迷糊一会儿,虽然睡着了免不了掉下来碰个鼻青脸肿,但总比蝎子蜇着了好受。没想到,有一次被长岭发现了,长岭以为她想上来,就把梯子搬走了。
怎样才能不让蝎子蜇呢?珍珍在地窨子里转来转去。一个念头从她的心里冒了出来,在墙上挖个洞钻进去,不就可以挡住蝎子了吗?珍珍用筷子在墙壁上划出了洞的大小,开始挖掘起来,墙壁带沙性,不一会儿墙壁上就出现了一个凹坑。珍珍手中的筷子又增加了力度,墙上的凹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珍珍在这种狠劲儿的挖掘中,得到了一种发泄的快感。为了不让长岭发现,珍珍每天在长岭下来以前,把挖出来的土重新填进去。一连几天,珍珍挖了填,填了挖。随着墙洞的加深,地下的土往洞里填时再也盛不下了。尽管珍珍把剩下的土匀摊在地上,但还是被长岭发现了。
长岭问她做什么?她战战兢兢地把原因说了,长岭不但没有责怪她,下来的时候,还把一个小铲扔给了她。有了工具,珍珍的挖掘顺利多了。
洞挖好了,珍珍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由于空间太小,身子根本不能左右转动。珍珍躺在洞里,抬眼看洞顶,没有一丝缝隙,藏不住蝎子。珍珍直挺挺地在洞里躺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自己这个样子很像是躺在棺材里,心里一酸,落下泪来。
有了这个墙洞,珍珍晚上实在困了,就到里面迷糊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而已,时间稍长,就憋闷得受不了。为了不让蝎子爬进洞里,珍珍每天都用土把洞口堵住,然后再用手拍实。
牵牛花又开了。今年的牵牛花比去年开得稠开得也大,藤蔓顺着树枝向上攀爬,树有多高,它们就能爬多高,郁郁葱葱的藤蔓和茂盛的树叶纠缠在一起,一朵朵的小喇叭朝天怒放。珍珍趴在小窗口上,看树下的牵牛花茎蔓一点一点向上爬,觉得日子还不如牵牛花蔓爬得快。
一直到牵牛花落了,何长山还是没有来。长岭也带回丧气的消息,大凤死活不离,娘也跟着到法院闹腾。法院调解,不准离婚。
珍珍觉得地窨子的棚顶突然朝下降了一尺,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几乎让她窒息。珍珍在地窨子再也待不下去了。她快步走到地窨子的出口,噌噌地登上了梯子,脑袋使劲朝上一顶,窖口的铁锅就被顶在了一边。长岭听到动静,急忙跑过来,把她的头朝下使劲一按,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你疯了?赶紧下去!珍珍的头使劲朝上挺,脖子差点被折断了。长岭松开手,低声问,珍珍,你愿意回头了?珍珍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长岭,叫了一声姐,眼泪刷的流了下来。长岭把手伸给珍珍,上来吧,姐不拦你。珍珍流着泪冲长岭摇了摇头,把头缩了回去。长岭叹了口气,把铁锅重新盖在了窖口。
长岭晚上下来送饭,对珍珍说,如果你真憋不住了,姐晚上可以带你上来看看。珍珍摇了摇头,瞅着墙洞发起了呆。她的心里在想,法院不准离婚,何长山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珍珍让长岭问问何长山,如果何长山想回头了,她就成全他。
长岭从娘家回来,却没有回话给珍珍。珍珍就问她,长岭姐,你问了吗?长岭气呼呼地说,你给俺兄弟灌了啥迷魂汤了?
长岭这句话,让珍珍吃了定心丸,何长山婚是没有离成,但肯定没有回头的想法。于是,珍珍对长岭说,长岭姐,俺已经是长山哥的人了,还怎么有脸再跟别的男人呢?
长岭动了恻隐之心,她实心实意地对珍珍说,我看长山和大凤离婚没个准儿,也许三年五年也离不了,你真为他耽误自己一辈子?
珍珍说,只要姐能容我,我愿意在地窨子里等长山哥一辈子!
长岭叹了口气,看着珍珍,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