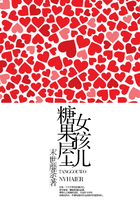冲在山沟里的水发出轰轰的响声,有节奏地冲过浑圆的,众多的山石。马樱花树错落地生在山沟两边断崖的红土上,羽毛似的叶子,粉绒似的花,点缀在苍翠的山谷间,放出清香的气息。天气阴沉沉的,高峰上绕着云雾。
三妞儿已经把衣服洗完了,她见四周没人,把鞋袜脱了,卷起裤管来站在一块圆石上,任山水冲着自己的腿脚。水劲很猛,她几次站不稳,而且凉得使她一口一口地倒抽着冷气,她却偏要站着不躲开,黑布裤子完全湿了,红布小褂的大襟也被跃起的水花打湿。她小声骂:“缺德的。”她想脱下小褂晾在树枝上去,陡地听岸上一阵笑声,只得把解开的扣子又扣好,大声骂:“缺德!”她提起盛衣服的篮子和鞋子,光着脚走开,到水边有草的地方。草扎了她的脚:“缺八辈儿德!”她只得穿上鞋,跑到山坡上,找那笑她的人。
“我想没别人,又是你,你笑什么?”
“亲妈还不管人笑呐,你管得着吗?”那个拿着铲子掘野菜的黑牛说。
“缺德的!掘野菜做什么吃呀?”她说。
“喂猪!”
“呸!还喂猪呐,人吃什么?吹牛!”她说。
“要不你就不给我做老婆了吗?怕吃野菜呀?”
她拾起一个小石头向他投去,他就笑着跑开了。但是不往远处跑,搂住一棵白杨树,防备石头再来。她不再砸他了,倒对他点头说:“过来,我问你正经的。”
“什么?”他并不动。她正色叫道:
“真的,有事呢,不过来你不是人!”
他过来,但并不走近她。她往前凑凑说:“怕什么?我又不吃你!”说着,乘他不备在他赤裸的胸上打了一拳,然后转身跑开。他追着,一把抓住她,笑着说:“凭你这个小身材敢打人?今天有你的……”
他把她拥在一个大山石下,亲着她的脸,她推着,骂着,笑着。山水声还是轰轰地吼,天更阴了,山里到处弥漫着浓雾似的云。
“你说前面那大山石像什么?”他已经放开她,两人坐在山石下的竹叶草里,他没话找话说。
“爱像什么像什么,我可该走了,三件衣服洗了半天,妈准得骂我。都是因为遇见你这丧气鬼。”
“嫌丧气,别对我使那股子劲,你不打我,我也不能招惹你。你妈骂你,你把实话告诉她就得了。”
她“呸”了一声走开了。眼看就要下雨了,他还在狮子坡摘野菜。
她到家把半干的衣服晾在篱笆上,抛下篮子到屋里。妈正纺麻绳。
“我还当你死在外头啦!也知道回来,还不快烧火哪,你爸爸从地里早回来了,要不是和你王五叔在门口说话,早要吃饭啦。”她把干柴煨在土灶里嘟嘟囔囔地说:“就知道纺麻绳,谁做饭不一样,必得要我做。”用力折山柴,用大把的柴烧着。
“你还不往锅里添水?锅就要烧炸了。”妈说。她才把锅里添上水,洗米。饭好了,把外面说着话的爸爸找回来,又把野马似的和人家捉迷藏的弟弟叫来。她真气极了,她想:他野马似的玩倒没人说,我又洗衣服又做饭妈还骂我。啪!给了弟弟一个耳光子。弟弟本来玩饿了,一打可打起火来了,躺在地上打滚不起来,骂着,手脚乱蹬。爸爸拉不起来他。妈说:“都是这个死丫头,做一点饭没好气,拿他撒气。”
“不用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吃完洗碗。”爸爸大声说。这句话很有力量,弟弟顾不得打滚,带着眼泪、鼻涕、污泥……吃饭来了。三妞儿看着弟弟不由得一笑。雨真下起来,很大。
北山上已经看不出山峰来。她想:“他也许还在狮子坡上吧!”
经过一场大雨,天已经不那么炎热了。没衣服可洗,妈叫她学着纳鞋底。她没好气,她想出去。
“又是福子的底子,我不管。”
“别找骂,好好做我不骂你。你弟弟的不管管谁的?你爸爸的鞋底大,你做不了。”妈说。
“屋里都把人闷死了,我上山坡上做去。”她说着就要走。妈把她叫住:
“你的心里长野草啦?在屋里就坐不住。拿着底子,别只是玩。等一年半载叫人家招走了,看你可怎么好?去吧!看你嘴噘得那么高!躲着人家的果园子走,省了人家瞎害怕。”
“听见了。”她拿着弟弟的鞋底子跑出去。
她坐在一棵大树底下,山水在下面吼着。昨夜的雨水从峰顶上往下流,流成一道道闪光的条子。黑牛还没来。她看那个像大狮子头的石头又像个人脸,怪得可怕。她四处找黑牛,没有影子。她又恼又怕,小声骂着:“缺德!”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走出一个人来,不是黑牛,可是她也认识,是胡大爷的儿子--狗剩儿--也就是她新订婚的未婚夫。她很看不上狗剩儿,可是爸爸种着胡家的地,去年收成不好,还借了胡大爷六十元钱,一直没还上,五月前连本带利已经一百二十元了。爸爸没主意,愁得整天打转,后来要把青苗卖了,弃了自己经营了半年的青苗,得了钱好还账。胡大爷倒有主意,要和爸爸做亲家,把三妞给狗剩儿做媳妇。不但不用还钱,还又给出五十元钱,一匹布,两对银镯子。爸爸对这位亲家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只是三妞儿不愿意,她知道狗剩儿天生的只有一只耳朵,据说前生死后狗要吃他,可是命大的人狗一尝就知道,不敢吃了,只吃去一只耳朵。名叫狗剩儿,不但纪念着前生的事,连这一世也表示出与众不同来,狗都不敢吃,长命是无疑了。不愿意又怎样呢?爸爸欠人家钱!她一见狗剩儿从石头后面出来,又失望又生气,彳彳地纳底子装看不见。
“我知道你今天准来,可是黑牛给我们放牛去了,来不了啦!”他大约昨天在什么地方隐藏着,看见她和黑牛的情形。
“来!来!谁也管不着!”她还纳底子。
“你可不能老早的就叫我当王八!”他凑过来说。
“天生要是王八,怎么也不会不当。”她说。他却站在她旁边,伏过短少一个耳朵的头来,要有一点丈夫的表示。她却不容情地用鞋底子打在他脸上。他摸着脸,懊丧地说:“开玩笑是怎的?打起男人来了。”可是并没生气,又凑过去。她狂了似的推开跑了,一直跑到回家的路上,见黑牛果然牵着一头牛从对面走来。他见她狂奔着,又往狮子坡上看了看,看见狗剩儿,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今天真美呀!还没过门就先圆房了。”说着牵着牛走向山坡去。三妞儿又气又委屈,坐在路边一块青石上大骂:“死不了的缺德鬼们,都滚山死了才好呢!”骂着往山坡上看看,只见狗剩儿穿过他家的葡萄园子溜开了。黑牛把牛撒在山坡上吃草,他看了她一眼。她扭过头去不理他。黑牛在山上唱起小曲来,声音很大,弄得山里起了回声,和有节奏的山水合成一种动人的调子。
六月里的天儿呀,天是热的,
谁家的姑娘,坐在那野地里,
伊呀,呀呼嘿。
野地里青草多呀,草是绿的,
谁家的姑娘呀,想那个少女婿,
伊呀,呀胡嘿。
……
她心里噗噗地只是个跳,不由得又走上山坡去。他满不理会她,还是俚俗地唱着。唱完了又用舌尖打嘟噜儿,看着牛吃草,看都不看她。她生来没受过这个气,这个滋味可不是人该受的,比打一顿还难受。她用鞋底子敲着自己哭了起来,边哭边骂:“缺八辈儿德的。死不了的短命鬼儿,瞎了眼的老牛……”她哭着,他咯咯地笑,又唱:
六月里的天儿呀,天是热的,
……
她觉得哭也哭不出好处来,拾了一块大石头用力投在山沟里,哗啦!溅起几尺高的一丛水花,她的气似乎泄净了。懒懒地回到家去,可是一个鞋底尖也没纳完,塞在炕席底下,没敢给妈看。
事儿总是往一块挤!本来她就睡不好觉,又偏偏从房顶上出来个大圆月亮,不歪不斜地使劲照着三妞儿的窗户。炕又小,容不得她翻几个身就碰在墙上,蚊子又咬她,她真烦了,烦得捶墙,捶了几下墙还是睡不着。用力闭眼睛也觉得亮。她坐起来披上衣服,开开屋门,弄得门轰隆轰隆直响,可是爸妈屋里一点动静儿都没有。从院里看北山上蓝微微的,比在太阳里还好看。她走到后门外边去,原来哪儿都有月光。连毗的果园里、山谷里、树上、草上都被银光笼住。她想早知道这么好看,天天晚上出来看看。忽然脚底下一个东西一蹦,把她吓得倒退一步。见那东西咯的一声又咚的一声跳在面前一洼积水里。三妞儿终究是三妞儿,胆怯起来,转回身到门里,关上后门。一闪,一个黑影抱住她,她吓得要叫,那人堵住她的嘴小声说:“是我,黑牛。”她也小声问:“你怎么进来的?”
“你开门发呆的时候我溜进来的。”
“我怎么没见你?你为什么晚上出来?”
“因为白天没好气,晚上睡不着。出来想在狮子坡遛遛弯。可我也不知怎么,在你门外遛开了。三妞儿!”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