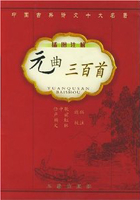妙仪吃了几次亏,再不敢抢嘴,遂只是默默坐着听,并不多话。反倒是昭娘姑姑来了兴致,问道:“哦,却不知这小丫鬟说了奴婢们些什么?”
“嗨,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能有什么见识,不过是鹦鹉学嘴,瞧了热闹回来说几句与我听罢了。我这园子里的丫鬟大多是些十来岁的小姑娘,爱热闹得很。因我病着,她们平日也不得出门,可一听说宫里来了两位教习姑姑,便忍不住和小姐妹换了值偷偷出去瞧一瞧热闹。据这小丫鬟说,远远看得并不真切,只觉得宫里来的两位姑姑威仪气派得很,一位观之十分温柔宽和,一位观之却十分威风霸道。我从前未见过两位姑姑,心里便默默描绘了两位的模样,谁知今儿个一见却大出意料之外。昭娘姑姑固然是温柔可亲,但妙仪姑姑怎么看,也离那小丫鬟说的‘十分威风霸道’差得很远,可见传言往往不尽真实啊。”
说罢,她掩唇又是一阵笑。她笑,昭娘和妙仪少不得也得陪着笑,只是个中心境却往往大不相同了。
妙仪的脸一阵青来一阵白,还得强作欢颜,那表情,真真是说不出来有多精彩绝伦。她心里已恨得暗暗咬牙,面色却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满来,蓦地起身道:“纪小姐,奴婢忽然觉得身子有些不适,想先行告退,还请纪小姐恩准。”
纪芷湮不由止住笑,满脸关切地望向面色难看的妙仪,懊恼道:“哎呀,怎么说得正高兴,妙仪姑姑便要走呢?难不成是芷湮方才说错了什么,倒教姑姑心中恼我了?”
妙仪勉强笑着,“纪小姐说的哪里话,几句玩笑话而已,奴婢怎会这样小气记仇?莫说纪小姐并无恶意,即便纪小姐真的要拿奴婢来取笑作乐,奴婢也是绝不敢有半句怨言的。只是这会儿身上的确有些不好,才不得不扫了纪小姐的兴。”
纪芷湮挽着妙仪的手将她重新按回座位,笑道:“既然知道是扫兴之事,那妙仪姑姑便走不得。”
“纪小姐,可奴婢身上……”
“我知道,姑姑身上不适么,这事好办。只怕两位姑姑还不知道吧,芷湮虽不才,于医术上却是颇有些心得的。莫说姑姑这样的小毛病,便是有些人已经死了,我要教他活过来,阎王爷也奈何不得。”
说完便如变戏法般,纪芷湮的指尖不知何时便多出了一根银针,又见她的手一抛一甩,便有两颗硕大的夜明珠挂在了两边铜铸的灯座上。珠光熠熠,立时照亮了整间屋子,也愈发显得她指尖的银针慑人。
她看向妙仪,脸上笑容灿烂,殷切道:“妙仪姑姑看着身子很是健壮,忽然间不适定然是来了我丞相府操劳太过的缘故,那我便更要用心治好姑姑了。妙仪姑姑,你且说说你哪里不适?不对,还是我亲自给你扎一针吧。”
眼看那银针离自己越来越近,妙仪彷佛是受了什么刺激般跳起来,抱着头蹲在地上大叫:“啊,不要,不要过来!我没事,我没事,我好了,不要扎我。”
其实妙仪的“病”,在场诸人无不心知肚明,只是看她这般装疯卖傻,便姑且陪着她玩下去罢了。想必妙仪也不曾料到,自己从未放在心上的这个纪家小姐,竟是这样厉害的人物,收拾起人来滴水不漏,半分痕迹也无。你吃了她的亏,也只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纪芷湮看也不看妙仪,只盯着自己指尖的银针喃喃自语:“咦,难不成我的医术越发长进了,这针都还没扎上,人竟自个儿好了?不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要么就是妙仪姑姑压根就没病,要么就是我的医术真的长进了,到底是哪一样呢?”
眼见得那渗人的银针又逼近自己,妙仪急得只差没哭出来了,大喊:“纪小姐,自然是小姐的医术又长进了。奴婢心服口服,多谢小姐医治之恩,多谢小姐。”
说完又是忙不迭地磕头叩拜,只求这小祖宗大发慈悲饶过自己。
此时此刻,昭娘也不由得有些同情起妙仪来了,素日在宫中那样霸道厉害的人物,宫女太监们见了一个个闻风丧胆,避之唯恐不及。谁知而今竟也有在人手底下栽跟头的时候,尤其,还是栽得这样毫无痕迹,毫无招架之力。说到底,谁也没成想这位小祖宗竟有这般能耐,谈笑间便能不动声色地把人给治了,一点错儿也寻不着。
昭娘忍不住道:“纪小姐,既然妙仪说她自个儿好了,那便是真的好了。您身子也不好,何苦为她这般操心劳力,快坐下歇会儿吧。”
妙仪听了这话也是忙不迭地点头,望向昭娘的眼中满是感激,倒透着十足的可怜劲。
纪芷湮睁着黑白分明的眸子望向妙仪,不放心道:“妙仪姑姑果真好了么?”
妙仪点头如捣蒜,“奴婢好了,奴婢当真好了。”
纪芷湮叹声气,彷佛是有些被妙仪的狼狈触动,亲自去扶了她起身坐下,“芷湮原是一番好意,想着和姑姑们多叙一会儿话,彼此间也好多亲近亲近些。尤其是妙仪姑姑,芷湮听闻前几日我病得沉重,爹爹明令不许人来探视,姑姑还不顾一切地三番四次求见,此心此意当真是教芷湮感动得紧。偏我今日见了姑姑也觉得投缘,这才舍不得姑姑早走,便留着多说了一会儿话。妙仪姑姑不会怪芷湮吧?”
她说这话时,目光澄净明亮,眼眶似红未红,倒透着几分真心实意。
妙仪便是心底真的怨恨,当面却也不敢说出来,她原是那等口蜜腹剑的人,遂亦挤出几滴泪来,惺惺作态道:“难得纪小姐待奴婢竟有这样的心,奴婢便是万死也难报小姐的情意。莫说多留我坐一会儿闲话,便是要奴婢为小姐赴汤蹈火,奴婢也是一百个愿意的。”
一旁有人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却是昭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