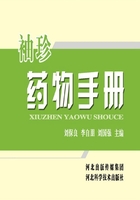如锦刚送了太医出去,从角门拐过来迎面就见玉华殿首领太监冯玉的徒弟小卓子正满脸喜气地往里跑,她不由正颜呼喝:“作死的东西,跑什么跑?不晓得太后娘娘今儿凤体违和,需要静养么?这般横冲直撞,还要不要命了?”
若换了别的小太监,被如锦这么一喝,定然是惊得噤若寒蝉。偏偏小卓子却依仗着他师父的名头,很是能在这些得脸的大宫女面前得巧卖乖,遂笑嘻嘻道:“如锦姐姐且听我说完再生气也不迟,那一位往这边来了。”
如锦平日里就很看不惯小卓子的做派,遂蹙眉问:“有话快说,卖什么关子?”
小卓子笑道:“还能是谁,当然是咱们万岁爷了。奴才方才远远瞧着龙辇往咱玉华殿的方向来了,千真万确。姐姐说,这难道不比太医开的那些个什么灵丹妙药管用多了?”
如锦面上亦露出几分喜色,笑骂一句:“小崽子,既知道,还愣着做什么?快些进去报信领赏吧。”
“哎,那奴才可去了。”
果然一听了小卓子的回报,正歪在贵妃榻上小憩的慕太后立时睁开眼来,娇艳的容颜上浮上几丝惊喜。她命人赏了小卓子东西,便起身用团扇拍了身侧的如玥一记,眼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便见如玥抿唇一笑,揶揄道:“知道知道,皇上也不是第一回来了,哪一次奴婢又不识趣了呢?只是今儿人来得巧,正好给太后吃一颗定心丸,可不知强过奴婢先前劝说那千遍万遍。奴婢便说了,凭它来上多少个纪氏王氏李氏,也不过是一时新鲜,当不得真,总越不过太后去。谁得比得太后这般,日日总教人惦记着来看一眼才安心。”
慕太后以扇掩面,眼中笑意如流霞绚烂,骂道:“你个死蹄子,仗着哀家疼你,尽浑说,如今越发说得起劲,也忒不像话了。还站着干什么,快出去将人迎进来啊。再不去,仔细哀家剥了你的皮。”
“了不得。朕才来,就听见这样厉害的话。总不是怨朕来迟,有人生气了吧?”
远远的便有男子爽朗的笑声传来,不是延陵澈,又是哪一个?
如玥抢先出去,绕过凤穿牡丹金立屏风笑盈盈行礼:“给皇上请安。”
延陵澈含笑喊她起来,便见她努嘴朝内,故意道:“皇上快进去哄哄吧,那一位刚发了脾气,说要剥了奴婢的皮呢。”
里头传来女子含羞带怯的声音,佯怒道:“如玥你个死丫头,若进来了看哀家如何惩治你。”
如玥别面轻笑一声,道:“那奴婢可怕得很,这会子只得出去避一避了。还劳皇上代为周全。”
延陵澈点头应了。
如玥轻轻拍掌,殿内的宫女便都垂头无声无息地离去,极有默契,可见这样的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延陵澈递了个眼色,苏喜便也识趣地退了出去,只在门外守着。
慕太后素喜奢华,先帝在时便十分受宠,又有一个家财雄厚的娘家,是以这些年没少着意添点,玉华殿内步步生华,雕金琢玉,十分耀目。
延陵澈信步入内,但闻层层罗帐后隐隐传来香浓的脂粉香气,眉间似有一瞬的褶痕,抬首进去时已是温柔似水的笑意,“今个儿又是怎么了?白白的和如玥生什么气?”
贵妃榻上的女子芙蓉如面柳如眉,半倚半起间,端的是风情妩媚,她娇嗔道:“她说什么你便信?你也不是不知道,那丫头素日嘴里从没个遮拦,十句话里通常有九句是唬人的。”
“这话不错。朕听着她方才的话里有一句便是千真万确的。”
“是哪一句?”
“就是日日总教人惦记着来看一眼才安心的那一句了。”
慕太后哎呀一声,羞得满脸红霞,仿若芳心初动的少女般用扇子掩住脸,声音柔媚得能滴出水来:“原来你早来了,还躲在一旁偷听我们说话,偏还学那丫头来打趣我,我便不依了。”
延陵澈轻声一笑,伸手覆在她的手背上,语调温柔:“看看,这又生气了。旁的人朕不敢保证,可在你跟前,朕从无一句虚话假话。”
慕太后两颊的红霞便一路烧到耳脖子去,许久才回转身来,目光幽幽含情,半怨半嗔地拨开他的手,“何必又拿这样的话来哄我?皇上眼下就要纳新人了,那纪小姐生得玉容花貌,不知比我这个老人强上多少。待接了她进来,到时皇上也便……也便渐渐把我抛诸脑后了。”
说完伏在椅把上哭作起来,呜咽声如泣如诉,玉肩耸动,好不可怜。
延陵澈叹一声气,伸手将她的身子给拌过来,又细细地擦了她脸上的眼泪鼻涕,“你向来是个聪明人,怎么今日却犯起糊涂来了?什么纪氏,什么玉容花貌,在朕眼中,远不及你万分之一。莫说一个纪氏,便是捧了全天下的妙龄女子都送到朕跟前来,朕心里眼里也只容得下你一个。何苦又去为了不相干的人来伤神流泪,实实不值。在这件事上,你倒不如如玥那丫头看得明白了。”
慕太后刚止住的泪水复涌了出来,目光复杂地望了他许久,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凄然道:“这话说得多好听啊。你说得恳切,我也几乎以为事实便是如此。可偏偏……偏偏我的心里那样清楚,它不是真的。或者说,我怕你我之间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延陵澈俊秀的脸上含着笑,沉静的眸中透着微微的柔光,彷佛是怜惜,无奈道:“吟霜,你今儿到底是怎么了?朕从前立了多少个皇后,也从未见你这般过。你心里明明清楚,不过是为了拉拢她父亲朕才应了这门婚事,况且这原是摄政王属意的人选,怎么听你的意思,反倒像是觉得朕和她之间有些什么似的。”
慕太后抬头,目光盈盈如一旺清泉,彷佛极认真又彷佛玩笑地问一句:“难道没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