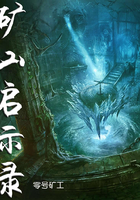莱森可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我的朋友,我敢保证他不是软弱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急性、坚硬而残酷的人。他好动不好静,丛林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的事。也许,那些不知所谓的城里人会觉得丛林里一定很刺激很浪漫,但事实恰恰相反。丛林是一个让人安静思考生命问题的地方。你能理解吗?法国人莱森是无法安静坐下来的。他才买下猩猩两天,就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百万富翁了。他设想自己在巴黎的公寓,四轮马车,赌场中的筹码,芭蕾女郎的媚笑。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想象,而想象的马力一旦过头,通常会驶向罪恶。莱森还有一个更糟的嗜好,那就是他的衣兜里总是揣着一个方方的酒瓶,他频频为自己的猩猩和自己将要在巴黎过上的美妙时光而干杯。他酒喝得有些过头。
那只猩猩很聪明,学东西很快。每次我和福伯格到莱森的营地,他总是把自己毛乎乎的学生牵出来向我们炫耀一番。福伯格不喜欢,我也一点儿不喜欢。我们告诉莱森自己的看法,他只是大声地嘲笑我们。
‘你们这两个傻瓜!’他叫道,‘你们这两个猴脑!你们等着瞧!皮尔?莱森教授和他训练有素的猩猩将每星期赚五千法郎!五千法郎!想一想吧!我会搂着巴黎名模的腰想着你们这两个在亚马逊受苦的傻瓜。’
他想过那种奢侈的生活有点儿想疯了,他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他经常看见自己和猩猩满欧洲大把捡钱,他想钱想疯了。我觉得那只猩猩也开始觉得他疯了。它会时不时地坐在莱森身边,托着腮纳闷儿为什么自己的主人这么兴奋。
这畜牲哪懂莱森的巴黎梦,它怎么会知道呢?它怎么会知道莱森已在头脑中为自己架了一只天梯,正在一点一点地爬上去吻仙女的脚跟。它只是一个畜牲,它不知道有人会每星期花四千马克看它装模作样地抽雪茄。哦,想想都让我恶心。
后来有一天,猩猩发了野性,有件事情它就是不肯学。我想那天莱森一定是又喝醉了,他一定是醉了。撒野的猩猩和醉酒的莱森,能有什么好事?皮尔?莱森后来告诉我,猩猩揉烂了雪茄打碎了道具,撒起野来。于是,他也撒起野来。他好像看到别墅、马车连同女人的腰都飞走了。他一口喝干了酒,甩掉方酒瓶,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黑漆漆的丛林安静下来,似乎也在倾听斯格瑞伯的故事。夜晚正微凉,生物学家的故事似一根魔鬼的手指,拨动着每个生灵的心弦。
“他一定是疯了。”生物学家继续道,“又疯又醉。亚马逊河刚好沿莱森的营地门口流过,许多丑陋、肮脏、凶残的鳄鱼整日都睡在河边的烂泥里。我讨厌鳄鱼,它们让我恶心。然而那个法国佬疯了,他认为猩猩需要好好教训一下。”
“然后怎么样?”我急切地问。整个夜晚仿佛都在听这个故事,关养动物的嘶鸣声已几不可闻。
“然后怎么样?”生物学家重复道,“皮尔?莱森想让猩猩知道不服从命令的代价。他把猩猩绑在河边的树干上——对,正挨着腐臭的烂泥塘。然后,皮尔自己坐在平台上,把来福枪横靠在大腿上。
猩猩在哀啼,莱森在笑。他后来告诉我说,猩猩一遍又一遍地哀啼,然后开始恐怖地尖叫。一块烂泥开始移动,把身体庞大的猩猩吓坏了。朋友,你见过鳄鱼的眼睛吗——冰冷的目光。那是凶残的鲨鱼才有的眼睛,没有别的生物会那么冷的眼睛。不,不对,鲨鱼也没有,鲨鱼的眼睛是凶狠战斗的眼睛。鳄鱼却不战斗,它要等到稳操胜算的时候才出击,她们是魔鬼。被皮尔?莱森绑在树上的猩猩吸引了泥中魔鬼的注意,猩猩愚蠢的哀啼正是向鳄鱼表明了自己正身处困境。
鳄鱼盯了猩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它觉得这也许是个陷阱,迟迟不发起攻击。莱森也在一旁观瞧。他要把猩猩调教成能在巴黎大把捞钱的聪明家伙。
鳄鱼甩掉头上的烂泥,以便能把四周看得更加清楚。猩猩尖叫着求莱森解救自己。它的尖叫一定凄厉哀婉无比。它在哀求,如果莱森马上来救自己,它一定会做任何莱森吩咐的事。但莱森只是笑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鳄鱼从泥中浮出身来,紧盯着浑身颤抖的猩猩。莱森后来还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情形。鳄鱼爬到岸边,眼中流出了几行眼泪,猩猩的眼中也流出了眼泪。残忍的眼泪与恐惧的眼泪。
鳄鱼冰冷的闪着死意的眼神彻底摧毁了猩猩的神经,猩猩瘫软在绳套里,用独有的哀啼向皮尔发出最后的呼救,它的声音已经绝望得破裂。鳄鱼因而更加充满信心,这个狡猾而残忍的家伙,它认为在这场与猩猩的比赛里自己已拿到了四张A,必胜无疑了。它决定发起攻击。
鳄鱼身体虽然笨重,但真正冲刺起来的速度却很惊人。它全速向猩猩冲去。皮尔?莱森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拿起了来福枪,将子弹射入了鳄鱼的右眼。鳄鱼翻了个身,惨嚎一声,飞快地钻回烂泥中。
你看这个皮尔?莱森,他简直就是个疯子。第二天,当我和福伯格又去他的营地时,他向我们大肆炫耀,笑得自鸣得意。猩猩可怜兮兮地围着他献殷勤,恐怕他再导演一次这样的恐怖剧。上帝,那个畜牲真的吓坏了,我敢打赌它梦中都会看见鳄鱼闪着死意的眼睛。每次莱森看它一眼,它就颤抖一阵,像婴儿一样啼哭。它被鳄鱼盯了三个小时,就算是正常的人,也会精神崩溃。
‘你们看,’莱森叫道,‘它再也不敢撒野了!我驯服了它!去!’他冲着猩猩叫喊,‘去把我的酒瓶拿来!’
猩猩去了没有呢?它当然去了。而且表现得仿佛这个任务生死攸关,一点儿不敢怠慢。莱森放声大笑,笑声好像都足以传到巴黎了。他还说鳄鱼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我下周先带它去新加坡,’莱森说,‘然后沿途演出,最后再去巴黎。每周五千法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看到皮尔?莱森教授和他驯养的猩猩!’
斯格瑞伯停了下来,轻轻吁了口气。一阵疾风吹来,巨大的树叶噼啪作响。阵风忽然消失无踪,周围又恢复之前的沉静。
“快说,”我兴奋地叫道,“告诉我,后来怎么样了?”
“四天之后,”斯格瑞伯平静地继续说道,“我又一次沿河而下来到莱森的营地外。我叫喊他的名字,却没有人回答。我以为他一定是到树林里去了,便决定自己先上去休息一会,喝上一杯。那天很闷热,亚马逊可绝不是个避暑的好地方。相反,它是个火炉。
你能想象死一样的沉寂吗?我有时会有这种预感,正如刚才赤练蛇逃走的那一刻。丛林中应有的蝉声似乎都已停止。哦!太奇怪了。每当我感觉到沉寂时我总是十分谨慎。我并非胆小,是因为我知道那种我无法感知而别的生物能感知的东西才最危险。
当我走向莱森的房子时,路上就感觉到这种沉寂,好像有一千只冰冷的虱子在抓着我的身体。我并没有幻想,在丛林里生活的人可以靠皮肤观察聆听,我的皮肤当时有些颤抖,我的判断不会错……它正在告诉我的大脑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我沿着小路,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我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但我知道我马上就会发现的。我在头脑中追随着那种奇异的感觉,我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找到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跳动,嘴唇发干。我想起了莱森对猩猩的暴行,想起他如何把猩猩绑在树干上,想起猩猩如何面对一身泥垢两眼凶光的鳄鱼。我好像看见猩猩又一次被捆在树上。完了,猩猩出事了。我脑中灵光一闪,好像挨了重重的一击。
三分钟后我渐渐平息下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平台前。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那个丑陋的猩猩正拖着莱森的来福枪,像人一样在痛哭。
‘莱森在哪儿?’我叫道,‘他在哪儿?’我为自己的问题疯狂地笑。我的皮肤,我的直觉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猩猩走过来,好像能听懂我的话。我的腿虚弱得像两根稻草。我并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但我在梦中却可重演每一个细节。
沉寂、猩猩的哭泣、皮肤的战栗告诉了我一切,那就是把太多的事情教给一个畜牲绝不是件好事。‘他在哪里?’我又喊道,‘告诉我他在哪里!’猩猩抹着它丑陋鼻子上的眼泪,伸出毛绒绒的手抓住我的手臂,开始拉我向泥岸边走去。
我感到阵阵恶心,那种气氛让我五脏翻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我当时就知道,我的大脑像拼魔方一样把零枝碎叶的细节拼在一起。我紧紧地抓着来福枪,浑身冷汗直淌。走近泥岸时,我四处搜寻着可以证实自己猜想的证据,缘来它就摆在那儿。在莱森绑过猩猩的树上,系着两只衣袖,衣袖里还有半只断臂,一条粗绳圈环在树根部,系得很紧——这就是我想要的证据。
事情对我来说再明显不过了。莱森肯定又喝醉了,醉得十分厉害,他的醉相激起了猩猩的恐怖回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出现在了这个畜牲简单的大脑中:让菜森也尝一尝在冰冷的眼神前发抖的滋味。它把莱森绑在自己被绑过的树上,学着他的样子拿着枪坐在一边的平台上,等待着那些冷冷的眼睛注意到莱森的困境。
莱森一定清醒过来,面对死亡的恐惧他一定大声呼救过,猩猩也学着他的样子故意不理不睬。事情太明显不过了——一定是这样。
莱森教了猩猩许多,唯独忘了教它如何装子弹。当鳄鱼发起攻击时,猩猩拼命扣动扳机,但毫无用处,太不幸了!猩猩只有坐在那里像人一样地哭泣,直到我赶来,可是已经太迟了。”
“那你后来做了什么?”我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做。”斯格瑞伯轻叹了一口气,“我知道皮尔?莱森对猩猩的所作所为,模仿本来就是灵长类动物最大的天性——而莱森正是想利用猩猩的这个特长去实现自己的法国梦的。命运?报应?造化……无论管它叫什么,自然界总是存在这种奇怪的法则,屡试不爽。后来我盯着猩猩,猩猩也盯着我惊恐地后退。他边退边哭边回头,它回头望了十几次,直至消失在了丛林里。”——这位有点儿胖的生物学家用手指了指黑漆漆的丛林——“那里有一只猩猩,头脑中永远存留着一场悲剧,无法抹去。”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