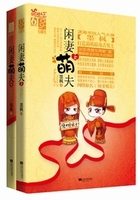背景材料:自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那一庄严的表决之后,历经十余年的移民工作伴着三峡工程建设的进度迅速展开。2003年,三峡工程将下闸蓄水、永久性航闸通航,并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因此国家要求2002年12月31日前完成135米淹没水位线以下的移民全部搬迁任务和库区清理工作。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库区又进行175米淹没水位线以下的移民工作。历时16年的百万移民堪称“世界级难题”,这一伟大北举震撼世界,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史上的特殊的“国家行动”。本书纪录的正是这场国家行动的全景画卷。
这是不久前我在三峡库区的所见所闻:
2002年6月6日清晨,在大江边的一个山村路口,王朝珍奶奶就要离开她居住了84年的水市村。她身边是成百上千人的送行队伍和喧天的锣鼓声,在无数遍叮咛祝福中夹杂着无数声离别的哭泣。
欢送的彩旗飘扬在猎猎晨风中,载人的汽车发动了隆隆作响的马达。全村人都要走了,但谁也没有第一个登车,所有的目光投向了王朝珍奶奶。
已当爷爷的长子过来想搀扶老母上车,不料老母轻轻将儿子的手一甩。
“妈,咱走吧,乡亲们都等着您哪,啊!”儿子有些着急。
老母不理会,一句话不说。转头寻觅了一下,找到了: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岁的重孙身上。
“好娃娃儿,来,给老宅居磕个头……”老人缓缓按下重孙,自己又颤颤巍巍地双膝跪地……
“妈——”儿子大哭一声,随之跪在后面,俯首贴地。
“奶奶——”
“祖奶奶——”
全村要走的人都跪了下来。紧接着是一片朝圣般的祈福声……
“奶奶,你迁移到的江苏,是我的家乡,那儿也有长江,比这里还美……”我忍不住也挤过去同乡亲们一起将王朝珍老奶奶搀扶起身,并从心底涌出这样一句话。
我看到老奶奶的眼里闪出一丝光亮,然后义无反顾地拉着重孙,头也不回地上了车,直到远远地离开那个青山绿水的江边小镇……影子渐渐变得模糊、模糊。
我发现那是由于我的眼泪。
7月9日,上午10时刚过,炙热的阳光便开始朝头顶泼洒。
又是大江边的一个小村,又是成百上千人的送行队伍和喧天的锣鼓声,又是无数遍的叮咛、祝福和无数声离别的哭泣。
“怎么办?总指挥,已经超过预定出发时间两个多小时了。再这样等下去会耽误整批移民搬迁任务的呀!”镇长急得团团转,已经不知第几次向担任外迁总指挥的副县长请示了。
总指挥双眉紧锁,只见他不停地在大树底下的那块石板上来回踱步,却不吱一声。终于,他再—次抬头……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在同一个地方、向同一个方向,他几乎抬过上千次头了。但总指挥必须继续抬头、继续抬头观察那棵大树枝杈上的动静……
那是农舍前的一棵近百年树龄的老槐,盘根错节。身后是柑橘满坡的山,前面是百米相望的大江。透过树干的枝杈,既可见逐浪翻滚的江流,又可见汽笛声声的舟船。
此时树杈上有个用塑料布搭盖的小棚子,那棚子里坐着一个老人,一个与老树同龄的老人。她叫什么名字,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就连她的儿子、儿媳也记不清,大伙儿只叫她“水娘”。
据说水娘出生的那一年长江发大水,江水一直淹到她家门口,大水一淹便是三七二十一天。水娘的母亲死得早,父亲和两个兄弟又被那场洪水吞噬了生命,最后只留下她和那棵槐树。
水娘和槐树从此一起饱经岁月的沧桑。是新中国给了她新的生命和新的家庭,还有满堂子孙。
有一天孙女告诉她,说政府要把家门口的这条大江修成大水库。
“咋修成水库?”水娘问。
“就是不让大江下游的人淹了。”
水娘点点头,明白了。
又有一天孙女告诉她,说我们要搬家了,搬到广东去,就是搬到大海的边边上。
“一定要搬?”
“一定要搬,政府说的。”
水娘再也不吱声了。
后来房子被拆了。孙女他们都临时住在亲戚家里,并且特意为“老祖宗”准备了一张席梦思床。
水娘执意不去。她对孙女说,她要再看一看大江。
可看不到呀!——屋前有了新的人家。
“把我抬到老槐树杈上。”老祖宗瓮声瓮气地说。
儿孙们一听乐坏了,连夸老祖宗雅兴不小,说行行,满足您老。
一大帮人好不容易将老人抬到老槐树杈上,不想老人越看大江越发痴呆,不是流泪就是喃喃自语着什么。一句话,怎么劝也没用,就是不下来。
这可急坏了家人,急坏了村上干部,也急坏了镇上县上的领导。移民计划争分夺秒,就像战场动员,说谁走就谁走,说哪时走就哪时走,不可延误,如同军令。
村干部千呼万唤不见效果后赶紧请来镇干部,镇干部口干舌燥仍见树上的老人家“岿然不动”,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搬来县领导。
指挥长面对已在老槐树上度过了四天三夜的老人家,还能说什么。“你们,包括我,有谁比得上水娘对故土的感情?对大江的感情?让她多看几眼吧!”指挥长含着眼泪对身边的干部和群众说。
“接住哟水娘,您渴了就喝口瓶子里的水,这是我特意从您家后面的山泉中灌的,甜着哩!”指挥长再一次向上递过一个小可乐瓶子。
码头上送行的船只,送行的锣鼓,还有送行的叮咛声和离别的哭泣声,都渐渐停下来,目光全都转向老槐树。
是风还是雨?老槐树的枝杈突然动了一下,树叶尖尖上掉下了水滴……
“我要下来——”是水娘在说话,随即见她双腿向下—伸。
“快快,赶紧接着!”指挥长急忙命令。
于是,老槐树下“哗”的一下簇拥了不知多少双手。
水娘安然落在众人的手臂之上。随后她又像一尊庄严的大佛,被前呼后拥地抬向远行的外迁船队上。那场面庄严而隆重,比得上当年皇上起驾之势。
送行渡轮笛声齐鸣,锣鼓敲得更响更脆。远行的船队徐徐启动,留下长长的一片白浪在翻卷……
我发现自己的眼里又是泪。
这是另一年4月的某一日。就在那个西陵峡中有名的兵书宝剑峡上的桂平村里,村民黄德发忧心忡忡地蹲在地上不吱声。
“走吧老黄,船都要开了你还在磨蹭啥子?”村干部过来催道。
黄德发哭丧着脸,低头道:“我一直还没敢给我娘说外迁的事呢!”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不跟她老人家说清楚呀?”村干部急了。
黄德发来火了,双脚用力踩地:“我咋不想跟她说清楚嘛!可你不是不知道咱这峡江一带自古就有‘六十不出门,七十不留宿’之说!我娘她从进咱黄家后就没离开过一回村子,现在她都88岁了,天天守着那口大红棺材哼着送终的小调,你让我怎么跟她说?说让她现在挪窝?告诉她死后不埋在长江边?我……我能出得了口嘛!”
村干部默然无言,只得叹气。
“发儿啊——”
“哟,是我娘在叫哪!”黄德发赶紧进屋。村干部也跟了进去。
“娘,你有啥吩咐?”
老母抬了下眼皮,不满地瞪了一眼儿子:“人家都搬了,就你落后!”
“哎哟娘你……你都知道了?”五十好几的黄德发“扑通”一下跪在老母亲跟前直请罪。
“起来吧,儿。”老母亲颤颤巍巍地从小木椅上站起身,慢慢地走到那口放在正屋中央的寿棺前,用手轻轻地擦了擦棺盖上的尘灰,又用手指头叩了几下木头,那寿棺立即发出几声清脆的音响。
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宽慰的笑意。
“知道这寿棺咋要大红色的?”她问儿子身后的村干部。
村干部点点头:“这是咱峡江人家的风俗。听说过去只有楚国的王公才用红寿棺,可因为我们这儿是屈原大夫的家乡,大家当年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夫子,所以用大红棺安葬了他。从此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和老人用大红寿棺便成了人们纪念屈原的一种风俗被传了下来。”
“你懂你懂。”老人挥挥手,然后对儿子说,“搬吧,带上我的这口大红寿棺!”说着,老人迈开小脚,一跛一拐地向外迁的队伍走去。
儿子黄德发恍然大悟,赶紧直起腰杆,满脸神气地朝村上的人喊道:“快来帮忙,抬我娘的宝贝疙瘩!”
“来啦来啦!”村上的男人们老的少的全都过来帮忙。阳光下,那口大红寿棺格外醒目地出现在外迁移民的队伍中间……
“奶奶小心!”
“奶奶走好!”
村上的女人们老的少的全都簇拥在88岁的谭启珍老人周围,不停地亲热呼唤着。
“走,孩子们,咱到新家去。”
“走,到新家去!”
又一队浩浩荡荡的外迁移民告别三峡,走得很远很远。队伍里的那口大红寿棺则在我眼前不停地摇晃着,直到再一次模糊。
我发现自己的眼里依旧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