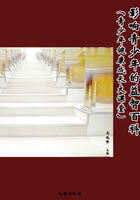摸黑走了一整晚,晨曦渐明,下一步要往哪去,她也认不清。青鸟突然叫了一声:“要走了!”
果儿一惊,“什么要走了?”是无恨吗?他擦觉到他们,所以要走?她不相信!
“那只银虫越来越远了!”
就是无恨也越来越远了,果儿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感觉,有点酸涩,有点难过,有点气愤,又有点担心。
当日头升到正中,两人一兽人到达青鸟所指之处时,只看到一地哀鸿,到处都是散落的女人,间着几个男人,全部都长着嘴嚎叫。
大部分女人穿着统一的侍者服饰,只有一件天蓝色覆着白纱的衣角从人堆中一堆破木头破布中漏出来,蓝衣白纱之上,沾染着点点血迹。
果儿没料到会看到这么一副盗匪过境的场景。她无法想象无恨会在这里——他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事?有没有受伤?是不是被人给抢走了?还是……种种猜测在脑子里翻滚,她担忧得展不开眉宇。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殷无恨的感情或许已经越过了那个模糊的界限。她害怕得心都痛了,拨开废木板。一个清秀俊美的女人露出来,颈上一道血口,鲜血汨汨流淌,染红了半个身子。
她闭着眼,脸上的神色格外平静,如果不是犹有余温的鲜血依旧鲜明,恐怕会误以为她只是陷在一场棋梦之中,在蓝天白云之下,平静地坐在林荫下,举着棋思考下一步,不时仰望一眼辽阔的天空。
果儿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很美,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脱俗淡雅,可是她死了。呼吸没了,脉搏停了,心跳也静了。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三人看过去,是位老婆婆,一身黑色长袍,两边腕上各有一圈簇金护腕,敛在宽大的袖中。满脸皱成橘皮,干枯的唇裂开一片死皮,干巴巴地翘着,一双已然被岁月蒙上红尘浊气的眼眸却直巴巴地望着果儿的方向,“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果儿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样一个老人家殷切而恐惧的问话,她是预料到了吧,可是又怀着那么一点希望,她真的不想成为抹灭那点光芒的人。她沉默着,不知道怎么开口。
青鸟往前一凑脑袋:“一个死人啊。”省了她的为难。
老人家一下子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蔫了。
果儿无力地一抚额,这只鸟!
明炎兮只在那女人身上看了一眼便移开视线,扫视周围,这些人,都没死,却不知被做是什么手脚,遍地哀声。
他走到最近的一个男人身边,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郎,一张小脸惨白惨白,已经叫得喉咙发哑。
明炎兮自是不懂医理,只是略识点皮毛。一把脉,当然脉不出什么东西来。
果儿眼角瞄到明炎兮的动作,便看向蔫搭搭,嘴里不知在念着什么的老太婆:“婆婆,你可通医理?这些人都是怎么了?”
老太婆茫然地抬头,视线不知落在何处,瞄一眼果儿,像勉强收回了一点心思似的,看向四周满地的伤员。踉踉跄跄地爬起来,走到一个女卫身边,搭上她的手腕,凝神,出神——一直没回神。果儿怀疑她是不是又魂飞天外去了?
“婆婆!”果儿大叫一声。老太婆一下像被惊醒似的抖了下,浑浊的目光看向果儿,一面收回手搭到自己手腕上。嘴里喃喃念着:“奇怪奇怪!奇也怪哉。”
果儿一头黑线,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奇怪啊?
老人家在人臂上摸索着,一直摇头,喃喃自语:“什么症状?什么症状?如此熟悉。”
熟悉乃就治啊!
明炎兮突然以掌为刃,剖开他手下男子的腹部——果儿尖叫:“明炎兮!你就是好奇东大陆男子怎么生孩子也不要这样把人家肚子剖开啊!啊啊啊——好恶心!”又是一声尖叫,果儿往后大跳一步,远离那被剖尸的男子。
一条条色泽鲜艳五彩斑斓的幼虫在男子腹部裂口处蠕动,血腥,恶心,恐怖。
果儿脸色发白,差点要吐出来,这是什么啊?
那边的老太婆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倾身一看,脸色大变:“食尸蛊?”
“食尸蛊?”这名字就很邪啊!
青鸟却是眼眸一亮:“食尸蛊!”那个兴奋劲。果儿怀疑地看去一眼,这一眼就看到青鸟化成迷你版,兴奋地扑腾着俩肉翅在人堆里飞来飞去——咬开人的肚子,吃虫。
看着那些五彩斑斓的虫在青鸟嘴边扭动,然后被它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下啜进嘴里,果儿顿时觉得有什么从胃里涌到喉咙口,梗着吐不出来,脸色一下憋得酱紫。
青鸟!不带这么恶心人的!
那老婆婆惊叫“青鸟!”
果儿一愣,这迷你版的青鸟也有人认得出来?还是说它的颜色太明显?果儿一手抚上下巴,认真地思考:或许,应该给青鸟染个色。
青鸟那边一径吃得欢快,果儿终于缓过神,大叫:“青鸟,你给小心点,别把人弄死了!”
青鸟闻言不满地回头看果儿一眼,动作却还是慢了下来。那老太婆更惊讶,而后叹了一声:“果然冥河后浪推前浪,人才都是少女邪。”
果儿一头黑线,长江后浪推前浪,被谁给篡改成冥河了?
“婆婆,你们这都是要去哪里啊?遇到什么变成这样了?”
老婆婆又一声叹:“孽啊!孽啊!”
孽?什么孽?她满头雾水,歪了头,疑惑地看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