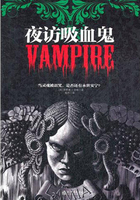邦德在星期三的大早上从死去的泰伦上校的床上醒过来。
他在上面睡觉的时间不是很长。昨天晚上,德拉克斯在他们两人回房间的路上没再说什么其他的话,仅仅是在楼梯口时向他道了声晚安。顺着铺有地毯的楼道邦德来到了亮着灯的一间房门前。他走进去之后,看见自己的东西在那间舒适的卧室里已整整齐齐地摆放好。房里的装饰同楼下没有什么区别,显得比较豪华。一些点心和一瓶矿泉水就在床边的茶几上放着。
除掉一副带皮套的望远镜和一个锁得紧紧的金属保险柜外,原主人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对于保险柜的机关邦德非常熟悉。他用力将保险柜推到墙边使它斜靠着墙,又把手伸到其底部,摸到了铁锁的按钮。假如按钮弹起的话就意味着锁上了。他稍稍朝上一用力,柜上所有的抽屉便被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他将保险柜小心翼翼放回到原处,心中暗自思量,怪不得泰伦上校在情报局里无法呆下去呢。
按比例缩绘的多佛尔海峡地区的地图及配套的设施放置在上面的抽屉里,另外,编号为1895的海军航海图也在其中。邦德把所有图都在床上摆放好,认真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发现有香烟灰迹就在那张航海图上的折叠处。
邦德伸手拿过一个存放在梳妆台上的方形的箱子。那是一个皮制的工具箱,。
他把皮箱上转锁的暗码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任何被偷开过的痕迹都没有发现。他把转锁上的密码转动开来,一直转到开的位置。工具箱里呈现在他面前的全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精密仪器。
他把指纹粉拿出来,小心翼翼地喷洒在那张航海图上,便立即有一片指纹显示出来。他用放大镜仔细照了照,得出的结论是,这应该是两个人所留下的指纹。他将其中两处最佳的指纹选出来,再拿出工具箱里带有闪光灯的莱卡照像机,将这两个不同的指纹分别拍摄下来。他把放大镜随后移动到图上粉末下端的两条细微的航线上。
这两条线是从海岸开始画起的,一直延伸到海里后,用一个“+ ”号标示出来。那标记画得非常小,而且看起来好像两条线的起点位置都是从邦德住的这幢房子开始的。
这两条线并非是用铅笔绘制的,而是很可能由于害怕被发现,就用铁笔尖轻轻勾画出来的。
有一个问号的痕迹在两线的交叉处,那地方距离悬崖约五十码,水深约有七十二英尺,使得这幢房子与南古德温灯船恰好形成正方位。
其他值得注意的线索从图上再也找不到。邦德看看表,距离凌晨一时还有20分钟。他听到有脚步声从远处的走廊上传过来,之后是关灯声。他匆匆站起身来,把大灯悄悄地关上,仅仅把床边罩着灯罩的台灯留下。
他听到德拉克斯的厚重的脚步声渐渐接近楼梯口,然后又是一声开关的喀嚓声。很快就没有任何声音了。那张多毛的脸在上面向下张望和倾听的表情邦德不难想象出来。没过多长时间,从外面传进来门轻轻开动和关闭的声音。邦德静默地等候着。在一声开窗声过后。整座房子不久又恢复了寂静。
邦德在五分钟后走到保险柜旁,将其他抽屉轻轻拉开,除了第二、三个是空的之外,在底层的抽屉里装了满满的卷宗,除此之外,一张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表也在里面,全部都是有关在这里的工作人员的调查材料。邦德把 “A ”卷抽出来,回到床上看起来。
所有的表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式:姓名、地址、出生年月、外貌、特征、大战时职业、战争中的履历、政治履历、现在的政治态度、犯罪记录、健康状况、家庭情况。对那些已成家的人其妻子与子女的情况都详细记录下来。所有档案中都附带照片,照片分别是正面、侧面像,同时还有双手指纹照。
邦德在两个小时内抽了十支烟才把所有档案全部读完。使他感觉有兴趣的有两点:第一,这五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清清白白的,任何政治纠葛与犯罪记录都没有,其生活作风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的。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下定决心但凡自己有机会,就一定到档案处去把这些人的原始档案再复查一下。第二点是,所有照片上的人全都未留胡子。无论德拉克斯怎样解释,在邦德看来这都是一个难解的问号。
从床上爬起来之后,邦德把那份航海图连同一份档案一起装进他的工具箱里,之后把剩下的东西再锁回原处。他把箱上的密码锁转动几下,再把锁好的皮箱塞进床下深处,也就是紧靠墙边的枕头的下方。之后他到浴室小声地漱口洗脸,再打开窗户。
夜空中的月光仍是那样皎洁。很可能在几个晚上之前,当一些奇怪的声音把泰伦惊醒,也许在他爬到屋顶张望时,由于被人发现,因此才突然遇难。想必那个晚上也是皓月当空。到底他看到了海上有什么?很有可能他是带着望远镜的。邦德想到这里就从窗前走开,拾起那桌上的望远镜。这是德国造的一架高倍望远镜,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缴获来的战利品。7 ×0 的数字在其顶部金属板上标示着,这就表明它夜间也能够照常使用。泰伦在那天晚上肯定是十分小心地走到房檐的那一头,举起望远镜向远处瞭望,估算着悬岩脚以及海上目标的距离,之后又估算着目标至南古德温灯船的距离。很可能他又顺着原路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邦德似乎能够看见了泰伦将房门轻轻地锁上,来到保险柜旁,把那张航海图取出来,轻轻地将方位线在上面标示出来。很可能他在将此图仔细研读后,才留下一个问号在旁边。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情况呢?这的确是让人太难以猜度了。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那并非是泰伦本应当看到的东西。他上房时所发出的声响已经有人听见了,而且认为那个目标他已经发现了,因此第二天早晨等他从他的房间离开时,那人就悄悄溜进房来,到处搜查,最终将航海图找到。可能没发现那张图上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然而在窗口一旁的那架高倍夜视望远镜则证明了那人的猜测。
这就已经足够将一切说明。所以,泰伦在那天晚上就丧命黄泉了了。
突然邦德将身子站直了,一连串的设想很快从脑子里闪过。巴尔兹把泰伦杀害了,然而他并非是那个听见响动的人。毋庸置疑那个人就是把指纹留在航海图上的人。
那个人一定就是那个溜须拍马的副官克雷布斯,图上的指纹就是他的!邦德比较图上和他档案中的指纹,足足花了一刻钟的时间。已经大致上能够确定这个结论。难道克雷布斯就是那个听见响动、干了后来所有这一切的人?且先不必提他看上去如何像一个天生的窥探者,他那双眼睛总是贼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很明显他的那些指纹是在泰伦看过之后才印到地图上面的,好几处都在泰伦的指纹之上面覆盖着。
但是,德拉克斯手下的克雷布斯如何会同这件事发生牵连呢?毕竟他是德拉克斯的心腹助手啊。然而,联想到西塞罗,那个大战中美国驻安卡拉大使看好的男仆,那不也是如此吗?那双伸进搭在椅背上格子裤口袋的手,大使的钥匙和保险箱,以及绝密文件。看上去所有这一切都极其相似。
打了一个冷颤后,邦德突然领悟到自己在窗前站的时间太长了,需要回到床上睡觉去了。
他在睡觉前将肩式手枪皮套拿出来,那东西就在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下边,邦德将布莱特手枪抽出来,塞在枕头下面。到底他是要防备什么人呢?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仅仅是凭直觉感到这儿非常危险,虽然很不清晰,并且只是在邦德潜的意识里绕来绕去,但这种紧张的气氛一直对都没有消除。实际上,他这种情绪紧张的感觉并非是庸人自扰,而是在过去的24小时中他心中积聚了一连串难以解答的疑点:德拉克斯的难解之谜,巴尔兹最后的那句的“万岁!”;那些人奇怪的小胡子;五十名一生清白的德国人;那张航海图;那个夜视望远镜;诡秘的克雷布斯等等。
得把这些可以的问题首先说给瓦兰斯,之后衡量一下是否克雷布斯具有犯罪的可能性,再把注意力最后转移到对“探月”号的防卫上。假如能够与那位布兰德小姐联络并交谈一次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将这两天的计划草草制定下来,心里暗想,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能再浪费了。
邦德把闹钟的闹铃定在七点上,这样可以方便明天一早按时醒来,他企图摆脱所有思绪准备入睡。明天他要赶快离开这里打电话给瓦兰斯。即便是他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也无所谓。把那与泰伦事件相关联的力量纳入他自己的轨迹之上就是他的目的,要让其余的人对他在这里的生活起居习惯起来。但是,有一点邦德已非常确信,泰伦的死肯定不是由于他爱上了加娜·布兰德。
闹钟极其准时地响了。他在七点整被叫醒了。他的嘴由于昨夜抽烟过多而感到干涩,脑子也不清醒。他勉强令自己下了床,先冲了个凉凉的冷水澡,又修了面,再用一把又尖又硬的牙刷漱了口。完成这些例行的事情之后,他穿上一件黑白相间的旧上衣,里面是海岛棉布的深蓝色衬衫,打着丝织的领带,然后手里提着那只方形的皮箱,轻手轻脚但又从容不迫地沿着过道向梯子尽头走去。
在房后他找到了停车房,很迅速地爬进自己的汽车,手一按在启动器上,本特利车上的大引擎便立马发动起来,慢慢地从混凝土坪上滑过。他把车停在树林边,空转着发动机,之后,他不停地观察着房顶,最后他已经能够断定,假如一个人站在屋顶上的话,他能够越过缓冲墙顶将不远处的悬岩及悬岩后面的大海看得清清楚楚。
“探月”号的圆顶盖四周没有任何生气。宽阔的混凝土路面在晨风中显得空空荡荡,一直延伸到迪尔方向,比较像是刚刚修好的飞机场跑道。那熨斗形状的缓冲墙以及坪面上的蜂房式圆盖,还有远处那立方体的点火处看起来在朝阳中显出阴郁之色。
海面上薄薄的轻雾预示着今天会是个不错的天气。南古德温灯船已隐约可见。那依稀可见的红色小船在同一个罗盘位置上永远被定格下来,和剧院舞台上的一只财宝船没有什么区别,在海风和波涛中摇摆,不存在船照、旅客、货物,在起点处它就已经永远抛下了锚,而这个起点也就成为了它最终的归宿。
晨雾中每隔30秒就会一阵嘟嘟的汽笛声响起。一对喇叭的声音,由高到低,声音悠长。一首汽笛歌,邦德暗自寻思,一点儿也不觉得好听,反而让人比较反感。
他脑子里反复思考着,七名船上的船员到底有没有发现或者听到泰伦在那张航海图上标出的那个标识呢?他飞快地驾车迅速通过层层岗哨。
他在到达多佛尔后,将车在皇家咖啡店旁停放下来,这是一家玲珑别致的餐馆。
这里的鱼以及煎蛋都可以算的上是店中的拿手菜。老板是母子俩人,意大利血统,他们如同对待老朋友一样对待邦德。他点了一份火腿、一份炒蛋以及咖啡,希望在半小时内他们能够准备好。吃完后他开车来到警察所,经由伦敦警察厅总机打电话给瓦兰斯。正在家中用早餐的瓦兰斯,仅仅只是听着,并未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于邦德还没同布兰德谈话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她是个非常机警的姑娘,”邦德说,“假如那个克雷布斯有什么秘密的话,她必定会觉察到。若是在星期天夜里泰伦听到了什么动静,很可能她也听到了,虽然我得承认她向来没有提起过这些。”
邦德对于瓦兰斯手下的这位得力助手究竟是怎样欢迎他的并没有提过一个字。“我打算今天上午好好和她谈一谈,”他说,“之后再把那张航海图以及莱卡像机胶片给你送过去。我先把它们交到探长的手里,再让他的巡逻兵给你带过去。对了,星期天泰伦是在什么地方给他的头儿打的电话?”
“我先查查,之后再告诉你。我会让议院请求南古德温以及海岸警卫队的帮助。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吗?”
“没有什么了。”这电话转线太多。假如对方是局长的话,也许他会再多说一点。然而邦德觉得,至于对瓦兰斯,似乎没有把工作人员的胡子及其感觉中的危险情形告诉他的必要。这些警察需要的证据,是铁的事实,而不是人的感觉。他们结案比破案要强得多。“所有情况就是这样,再见。”他把电话挂断。
再次回到那小餐馆把那可口的早餐吃完之后,邦德顿感精神振作起来。他将餐桌上的《快讯》和《泰晤士报》拿起来,随便翻阅了一下,发现有则报道是关于泰伦案调查的。
《快讯》还将那姑娘的一张特大画像登了出来。邦德看了觉得很好笑。很显然,所有资料全部都是由警方所提供的,肯定是由瓦兰斯所导演的一出戏。邦德打算无论布兰德是否愿意,都要想办法同她接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控制在手中。或许她心里也有很多的疑点,只是因为太过于模糊,所以才一直没有谈及。
邦德驾车没用多长时间就返回到那幢房子。穿过树林来到混凝土坪时刚好是九点钟。一声警报从房后的林中响了起来,一支由十二人组成的纵队整齐地跑步而出,向发射舱奔去。先由一个人按了门铃,门开后他们有秩序地消失在门中。
干掉德国佬还的确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邦德暗自思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