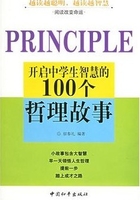邦德已经在五分钟后站在了高高的环绕着铁丝网的大门口,把部里给他发的通告证递给穿着制服的值班卫兵查看。
那位皇家空军中士看过邦德的之后有还给他,同时又向他行了个军礼,说:“先生,雨果爵士正在等您,就在前面树林中那栋最大的房子里。”他用手指着挨近悬崖边的一百码外的那片灯光。
邦德听见他给下一个哨卡打了个电话。他把汽车发动起来,顺着新铺设的柏油公路慢慢地向前驶去。在公路两边是广阔的田野。就连远处悬崖脚下传来的海涛声他都能够听见。近处的机器开动时所发出的轰鸣声在驶近那片树林时也传到了他的耳里。
邦德在第二道铁丝网前又被一名便衣拦住。一道带有五根铁栅的门就在铁丝网后,再往里面就到了树林。在那名便衣挥手表示允许他通过时,他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阵阵警犬的吠声。这就说明夜间有人在此巡逻。看起来一切安全措施都非常严密。邦德认为他没有必要为外部安全操心。
汽车在穿过树林之后,驶到了一大片较为宽阔的混凝土坪上。虽然他的两盏车灯射出了两束非常强烈的光线,但这片场地的边际他仍旧没有办法看到。在左面大约一百码外的树林边上矗立着一座大房子,里面灯光闪烁。房子外面是一堵约摸六英尺厚的围墙。差不多和房子一样高的围墙耸立在混凝土坪上。邦德把车速减慢,在圆顶房子前的山壁边上停下来。
他刚刚停稳了车子,房门便被打开了。身着白色夹克的一位男仆走出来,替邦德彬彬有礼地把车门拉开。
“晚上好,先生。请跟我来。”他的声音平平淡淡,方言口音很浓。邦德跟着他走进屋里,从一条宽敞的走廊穿过之后来到一扇门前。男仆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邦德在听到这特别耳熟的粗犷和那严重带有命令语气的声音时暗暗发笑。
德拉克斯在明亮、宽敞的客厅里背朝着一座空荡荡的壁炉站着。他身材魁梧,穿着一件天鹅绒质量的红色吸烟服,与他脸上的红胡子非常不相衬。除此之外,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三个人,是两男一女。
“啊,我亲爱的伙计。”德拉克斯扯着嗓子兴奋地喊道,并且大步迎了上来,热情地把邦德的手握住了。“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更没想到你居然会是一个为我部工作的可恶的间谍。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在和你打牌时我就会加倍小心的。那笔钱花光了没有?”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邦德带到了炉子边。
“还没有呢。”邦德笑着答道,“现在连钱影子都还没有见着呢。”
“那是当然。得等到星期六才能兑现。也可能恰好会赶上咱们小小的庆功会,怎么样?来,介绍认识一下。”他把邦德带到那个女人的面前,“这是布兰德小姐,是我的秘书。”
邦德注视着那双蓝汪汪的大眼睛。
“晚上好。”他友好地对她笑了笑。但是望着他的那双静静地眸子里并不带有一丝笑意。她在握手时也不带有半点热情。“你好。”她淡淡地回答。邦德感觉到似乎她的语气里带有几分敌意。
突然邦德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女人确实没挑错,简直就是一个劳埃丽娅·波恩松贝的翻版。能干、谨慎、忠诚、洁身自好。天哪,他私下里想,是个老手。
“这位是佛尔特博士,是我的得力助手。”那位年纪较大、面容清瘦、黑发下遮盖的眼睛略有愠色的男人好像根本就不曾看到邦德所伸出的手一样。他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仅仅只是稍稍地点了一下头。“是沃尔特,”他的薄嘴唇在黑色山羊胡子下翕动着,将德拉克斯的发音纠正了。
“这位应该说是我的……该怎么说呢,就算作是侍卫吧,你把他当作是我的副官也可以,他名叫威利·克雷布斯。”邦德与对方伸出来的汗涔涔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很高兴认识你。”随着这句讨好奉承的话说出口来,邦德看到了他那张苍白、病态的圆脸,那装出来的假笑还没等他来得及认真琢磨就已经一闪而逝了。邦德与对方的两眼直视着,他那双眼睛就像一对黑纽扣一样晃来晃去,闪躲着邦德的目光。
这两个人都穿着洁白的紧身衣,塑料拉链在袖口、脚脖子和臀部上安着。短平头,隐约能看见头皮。乍一看,他们的样子的确倒是很像天外来客,但是,凭借沃尔特博士那黝黑、散乱的髭须和山羊胡子,以及克雷布斯那绺苍白的小胡子,两个人看起来又很像是一幅讽刺漫画——一个疯子似的的科学家同一个年轻的耶稣门徒。
德拉克斯那过分热情、怪里怪气的模样和他那些态度冷漠的伙伴们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对于德拉克斯那野蛮的欢迎态度邦德并没有感到反感——至少使他这个刚刚到任的安全官不至于冷场。除此之外,德拉克斯表现出来的明确的既往不咎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刚刚上任的保镖头儿的信任,都让邦德感到非常欣慰。
德拉克斯确实是个不错的主人。他搓搓双手说,“喂,威利,替我们倒一杯你拿手的马提尼酒怎么样?不用说,博士是个例外,他是不沾烟酒的,”他对着邦德解释着,然后又对沃尔特说:“简直就像个死人。”他发出一阵简短的笑,“除了导弹之外,不会想别的,难道不是吗,我的朋友?”
博士毫无面情地站在他面前,“你就是喜欢说笑话。”
“好了,好了,”德拉克斯就像是在哄一个小孩子一样,“关于导弹尾舱的事过一会儿再讨论,除了你之外我们这儿可全都是烟酒之徒啊。咱们出色的博士不停地在操心,”他没完没了地解释着,“他就是喜欢不停地为一些事情殚精竭虑,这会儿是在为导弹尾舱操心,事实上,它们已经如同剃胡子刀片那般锋利,差不多可以不受任何风的阻力。但他猛然又觉得这些尾舱会熔化,认为空气的摩擦会磨光它们。不用说,什么事情都有很多的可能性。不过在3000 度以上的高温下它们已经被试验过,就如同我对他说过的,假如它们会熔化的话,那么整个导弹就也会跟着熔化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他说着,莞尔一笑。
克雷布斯走过来,手里端了一只银盘,有四只盛满马提尼酒的酒杯和一个打磨过的混合器在上面放着,马提尼酒的味道确实很好,邦德也这么说。
“你真好,”克雷布斯假装很满意地笑道,“雨果爵士一点也没说错。”
“把酒给他斟满,”德拉克斯说,“可能咱们的朋友非常希望洗个澡,然后八点钟咱们吃饭。”
一阵尖锐的哨声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响起,一队人整齐的跑步声接着从外边水泥场地上传来。
“这是晚上的第一次换岗。”德拉克斯解释说,“这幢房的后面就是营房。不用说现在肯定已经到了八点钟了。不管做什么在这里都需要跑步执行。”一丝洋洋自得的神情他眼睛里闪出,“准确而又迅速。即便科学家占了这里的多数,我们仍然使一切尽量都实现军事化。威利,你来照顾一下中校。让我们先走上步吧。亲爱的,现在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