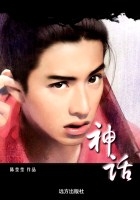在我猛然间发现自己对他潜藏的依赖和感情的时候,惊惶失措起来。我想起了曾经和夫君一起发过的誓,还有梅妃临死前怨恨的眼神,一个又一个的诅咒终于在今天都要实现,他们也许正在远处看我,而夫君,还在等我过去牵他的手。
皇上,让我走吧,我开口。要平息这场纷争,我只不过是个借口,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借口。请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赐玉环一死!我跪下请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可行的路,自幼便知女人本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漂亮女人。尽管她们中有许多人都很无辜,但仍是会被冠上“红颜祸水”之名,我自知自己也逃不了。
皇上很久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的看着我,感觉一下子老了很多。许久,他走过来拥住我,我想起了当年离开夫君时那场拥抱和亲吻,那样用力的,充满了绝望的气息。那时候的心,真如死水般沉寂。而今皇上的拥抱轻柔无力,他是真的,痛到了骨子里。我缓缓伸手拍他后背,那么就容臣妾,最后再为您舞一曲。
那天我着紫衣,如曾经山坡上的那片紫色花海样的随风起舞,院外的梨花洁白盛开,风一吹抖落一身一地。其实许多段爱情都无始无终,等到你要失去要离开时才恍然惊觉,它竟真的发生过,它一直默默的留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里,提醒你该痛的时候不如放声哭泣。
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转回身对着站在屋檐下的那个男人,皇上,其实我一直是爱你的。我将丝巾投到树枝上,自己飞身上去。
当一个女人肯将自己心底的感情全盘托出的时候,不是用情至深,就是已经结束。而我,只不过是在临走之前给自己一个交待,也好干干净净的去牵夫君的手。恍惚中,遥远的路之尽头,有人在向我招手。
一、我一直在寻找与我的鸳鸯谱相匹配的那个人,他该是能舞出空灵蔓妙的剑姿,轻柔优雅却招招致命。父亲临终前告诉我他叫剑泽。他说女儿,也许你一生的梦幻只不过是一个追寻,这是你的使命。
这个叫剑泽的男子一直出现在我的梦境里,穿着白色的衣衫纯净透明,他浅浅的笑着,恩慈,他轻声叫我。彼时我怀抱琵琶弹着那首鸳鸯谱,乐声悠扬动听穿过夕阳流水,丛林深处有谁舞剑的声音,身影忽隐忽现幻得幻失,与我的乐音正相匹配。可是我仍然看不清这个男子的身形,只留一片雪白的印迹和一缕银光闪烁。一切只是,自己的不甘心。
二、十五岁那年便初入江湖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辗转在不同的乐坊已三年有余,总会在固定的日子弹奏父亲谱成的鸳鸯谱,为这乐谱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他跟我说恩慈,找到会随着鸳鸯谱舞剑的男子,也许就能找到你的母亲,可以为爹爹报仇,你也就能衣食无忧的过一生。
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似乎这一切正是他心所向往的生活。可是在我的意识里没有母亲,没有其他男子,只有鸳鸯谱。我想我并不想衣食无忧的去过一生,飘泊的日子也是幸福。
和父亲在一起我们的确是辛苦的,没有积蓄朝不保夕,他总是整日的拨弄着他的那把琵琶,有时眼睛晶莹会有泪滴下来。每当这时我都会离他很远,怕他时不时的又发起疯来举起手里的东西胡乱砸人,他会痛苦的蹲在地上埋着头许久没有动静。恩慈。之后他叫我。我想吃东西。
我把荒原四周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找了个遍,后来只得翻过几座山去到别的地境。有时候回来父亲会心疼的看着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吃完饭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日子总是一成不变,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回来我看见他倒在血泊里,身边一个白色人影一晃闪过,他的胸口直直的刺了把剑,手里拽着他那把心爱的琵琶不瞑目。恩慈,他叫我,颤抖着交给我一个蓝色小本。这本是属于你的鸳鸯谱,终于还是还给了你。
天空乌云密布却怎么也不见暴风雨袭来,我拖着他去了屋子的后山,挖了个坑将他埋了进去。我看着他勉强闭上的眼睛,睫毛因为风的吹袭还在微微颤动。他是多么的不甘心,我明白,他从不曾提起的母亲是他多大的一块心病,他偶尔还会愣愣的看着我试图在我脸上找寻母亲的影子。可是能抛弃孩子的女子哪有资格当母亲,我不会认,即使有天相见,也会无言。
三、有很多人驻足聆听我弹的曲子,留下或惊叹或微笑的表情。我并不奇怪他们会有的赞誉,鸳鸯谱是我从小就熟练的曲子,这么些年加了自己的复杂情绪,如泣如诉缠绵悱恻,极能打动人心。可是一直没有人会随着这曲调起舞,大家只是给予欢呼和掌声,当自己在看戏。
这天乐坊的桂姐告诉我荣府的将军近日得胜回朝,家里人忙前忙后为他庆祝,决意由我们的乐班去为他弹奏几曲。其实这些本不是我所操心的事情,只是荣家老夫人点名要求我去,必须得弹鸳鸯谱。荣大将军长年在外老大不小,这次回来顺便相亲,家里人早准备了各色才女,只需我这乐师去助兴。
桂姐知道这曲子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她不敢随意答应。恩慈,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可怜你的美貌已快渐渐凋零,也许姐姐留不住你,何不遂了我的心愿再弹一次,也许有意外也说不定。
我点头,因为她的最后一句话。弹了近四年的曲子,我心灰意冷盼有奇迹发生,如果真有意外我愿五体投地叩谢苍天,父亲的在天之灵也许早已等得不耐烦去投胎转了世,苦的是,活着的人。
第一次看见荣将军是在门外的官道上,宴会还没开始荣府人声鼎沸,一刻钟后我感觉晕头转向,匆匆吃了些糕点便去门外透气。在河水中看着自己精心挑选的浅紫色衣裙衬着略显苍白的幽怨的脸,它们随风翻风在空气里,于是轻微笑了笑。每次出席任何一个场合都是由桂姐帮我选衣,今天竟是亲自动手,穿的是自己喜欢的衣服,也许这样也是幸福。
远处有人叫着“恩慈姑娘”在找我,我回头,身后站着一位身披战袍的男子,他亦在沉思。他身后很远的地方,荣府管家正焦急的看着我。那个男子回过神来,客气的招呼。
恩慈姑娘?听说你弹曲很好听?
我低头行礼。是大家太过夸奖。
想必已轮到你上场,我真是幸运正好能听到。
我一弯腰先他走了过去,走过老管家时隐隐听见他低声叫“少爷”才恍然明白,这位,即是荣将军。
我只见到过这个男子眉头紧锁的样子,那点点无助如孩童弄坏了自己的玩具般无奈,却又觉无足轻重。也许有些人在有些人的生命里能留下那么点印迹已算幸运,至少比随风飘散要好得多。
四、如我预料中的,这次弹奏真的发生了点什么,有人在我的曲子响起片刻后,随着乐调舞起了剑,虽然节奏上有些偏差,但整体来说还算吻合。这个人不是别人,即是荣大将军,荣泽。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凭着仅余的一点意识弹完了鸳鸯谱。我站起身来看着他,他对我微笑。
恩慈姑娘的曲子果然犹如天簌,我不请自到为姑娘舞剑,真是不自量力。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是这曲子本身,还是在他舞剑的过程中。我的整个脑子被欣喜包围着,心却不敢前进一步,就像前面是万丈深渊。
荣将军过奖,您会随着这曲子起舞,恩慈才是佩服万分。
我以为姑娘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人。
我呆愣原地。他淡淡笑着随风起舞的样子再次被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左思右想也想不出自己曾经梦到过的那个男子跟他有何关系,但是父亲说这个世上并没有第二个人能随着鸳鸯谱舞出那样的剑姿。乐谱和剑招是由两个恩爱夫妻同时创作出来的。我的母亲,虽然此后他们各分东西。
您确定,您就是我要找的人?我问得小心翼翼。
他再次微笑起来,一阵风吹过掠起他的衣衫,有那么一刻我感觉他的头顶充满阳光,所有的牵扯已快结束我这么久的坚持努力和前行的方向已然消失,这个人站在远处看我,我没有办法将他拉近到心里的某个角落,与我共享喜怒哀乐。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该是由你来确定的吧,不如姑娘再奏一曲看清楚些?
悠扬的乐曲再次传出,前方一个男子随着曲调挥舞着手中的剑风姿秀逸,不管多少年过去这个画面都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人与我如此的默契十足,在茫茫人海里遇到真的很不容易。
五、全京城都传开来我被荣大将军追的消息,桂姐时不时的问我还有什么不满意,要找的人也找到了人家还巴巴的要娶我过门,人间所有的幸运我都占尽了,要摆谱一天两天也就够了,难道还要一年两年不成。她说恩慈,必竟也是在外面抛过头露过脸的女人了,一般的寻常人家也许都很难看得上眼,尽管你只弹奏曲子别的什么也不曾做过,但是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闲言碎语一大箩筐,荣将军不嫌弃已经够福分,就别再迟疑了可好?
我淡笑不语。我总觉得事情来得太过容易,苦寻了四年未曾找到的人突然说出现就出现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算他真是我要找的人如此简单的相逢也未免让人起疑,我怎敢轻易的决定。
恩慈,你怀疑我?
我只是在想,爹爹说找到你就可以为他报仇,我们该如何为他报仇。
除了报仇你就不曾想过别的事情?
什么?
比如找回你母亲,然后与我成亲。
父仇不共戴天。
难道死了的人比活着的人还重要吗?恩慈!
他满脸无辜地看着我,我隐隐的感觉到他心里深藏的痛苦煎熬。可我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父亲只是执意的要我找到这个人,却不曾想他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否能如父亲所愿去做一些事情。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不容他人掌控分享。
那么,你该是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了?
不。他摇头。我不知道。
我手里还捧着他刚送来的新鲜百合,那些花怒放着娇艳欲滴,香味清新直抵人心。可是我的心底隐隐有些作痛,也许美好的事物都不容易拥有,也不容易长久。
六、我是无意间看到他的那柄剑的,闪着青色的耀眼光芒的剑刃在阳光下有些透明,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拿着它,剑柄上刻着一个字,鸯。
他在我面前喝多了酒如婴儿般瘫睡在桌上,偶尔有一两句梦呓,会叫我的名字。恩慈,不要走。恩慈,对不起。
这个男子在战场上定是叱咤风云无往不利的,他可以随意迎娶天下任何一个女子,即便是公主皇帝也一定会同意,但唯独,娶不得我,我不是他能娶的女子,他还不明白。
于是我选择离开,我选择在这一日阳光晴好春暖花开,走在归乡的路上,父亲的坟墓多日不曾打扫,我们的小茅屋只怕早瘫塌不知所踪。我身边的每一件事物都在作茧自缚走向不归路,没有人可以救赎。




![相女驭夫策[步步倾心]](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31/1949088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