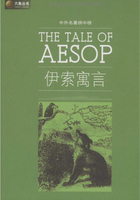武府,丫鬟男仆们在进进出出,给自家的男主人准备好行装,武云迪自己倒是悠闲的很,穿着一袭月白色长袍,一手抱住咿咿呀呀的儿子——已经取了名字,唤做武忆帆,一手拉住已经六岁的大女儿,低头和大女儿吩咐:“阿玛这次出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等会收拾了东西,你和弟弟就去你外祖母家住,知道吗?家里没有什么长辈,也只好放在你外祖母家了,若是有人闲言闲语,你要忍住,不要乱发脾气,我知道你的小姐性子,原本咱们家也不用低声下气,只是,哎,阿玛又要出去打仗,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外祖母家家大业大,说不定有几个猪油蒙了心的狗奴才想着仗势欺人,狗眼看人低,你先忍着,等到阿玛回来,再算总账。”
大姐儿眼眶里都是泪珠,却是强忍着不滚下来,点头回道,“阿玛我知道了,我绝对不发小姐脾气,老老实实呆在外祖母家里,有那些小人欺负我,我记心里就是。”
“很好。”武云迪亲了亲大姐儿的额头,长长得舒了一口气,“太后娘娘若是让你进宫,你就好好说话,回话的时候想好了再说,说慢些也无妨,但是不要骗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喜欢听真话,”武云迪摸了摸大姐儿的脑袋,“你是个要强的,和阿玛的性子是一样,若是有人欺负你,记住,你可是太后娘娘的外甥女,万岁爷的表妹,可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就算被人欺负了,也不能失了自己的体面。”父女两个正在窃窃私语,老王进来,神色古怪,“县君来了。”
冯婉贞龙卷风似的进了室内,大姐儿看到冯婉贞颇为喜悦,从炕上下来朝着冯婉贞行礼,“县君安好。”
冯婉贞摸了摸大姐儿的头,却是没有对她说话,“大帅,”冯婉贞对着抱着儿子的武云迪说道,“你又要出征了?”
老王连忙把大姐儿和武忆帆一同带了出去,又连忙关上房门,大姐儿有些不依,撅着嘴说道,“还有什么不能看的,县君喜欢阿玛,我是知道的,我也喜欢县君,她会教我小擒拿手。”
老王连忙让大姐儿别说话,悄悄的拉出院子,脸上却是眉开眼笑,“我的小姑奶奶,您给我小声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县君听到了,害臊了可不好。”
听到冯婉贞的询问,武云迪抚了抚衣服,“为将者,自然是要征战沙场,你这问题问的莫名其妙。”
“可是你才回来多久,朝中别的将军一样可以出征,你才没了福晋,小孩子还是这样小,忆哥儿还不会说话,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叫这一家子怎么办。”
“朝中武将虽多,能用的不多,可堪用的都要同去了,这次军机处已经有了令旨,务必全剿乱贼,不容西北再生事端,”武云迪站了起来,提起茶壶,给冯婉贞倒了一杯茶,“荣禄要去口外剿匪,更要筹办讲武堂事宜,走不开,且我在僧王麾下日久,说话方便些,”武云迪难得如此有耐心细细解释,“我常在京中,睹物思人,更是不好,你说的对,沉沦许久,再这样醉下去,整个人要废掉了,不如去西北走上一走,忆哥儿还小,我总要给他赚个出身才是。”
“那我和太后请旨,陪你同去。”冯婉贞说道。
“胡闹,你真以为你是花木兰,新疆远在千里,路途遥远,加上那白彦虎和阿古柏不是好相与的,昔日在永通桥如何惨烈你也是瞧见的,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和你父亲交代,太后也不会让你这样肆意妄为的。”
冯婉贞站在地上,眼中似乎就要流出泪来,武云迪看了冯婉贞一眼,长叹一声,站了起来,“我武云迪何德何能,能让你如此厚爱。”说完就拉住了冯婉贞的手。
冯婉贞的脸变得通红,“我原本就是山间的野丫头,那里谈得上这些,”说着话细不可闻,头也低了下来。
“你的心意我已经知晓,你且我此番出征回来,武云迪若侥幸不死,就向你父亲提亲,你在京师等我就是。”说完按了按冯婉贞的手,转身出去。
冯婉贞抬起头,看着武云迪的背影,嘴里喃喃自语,“放心吧,你的儿女我会去帮着照顾好的,你若是出事,”冯婉贞眼神转向坚定,“我自然也不会独活!”
同治六年六月初三,僧格林沁在丰台大营誓师出征,皇帝亲临丰台,为僧格林沁增添威势,旨意加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总督十二镇事务,兼任新疆总督;曾国荃为新疆巡抚,协办钦差大臣;武云迪加迪化将军,张树声加和田将军,王锦绣加吐鲁番将军,刘长佑加天山将军。
六月初九,交通部引进洋人工艺,设置兰州至京师电报,清流大哗,弹劾穆扬阿“以西夷之事乱我中华”,被太后以“事急从权”驳回,交通部又开设电报学堂,学习英国人电报技术,至此电报之事开始在中国推广。
同日,理藩院尚书庆海将文书发出,至苏禄国。西班牙大使对总理衙门抗议,恭亲王解释,“内藩之事,不用惊动友邦,若贵使有意见可向理藩院询问之。”西班牙大使和庆海抗议,庆海辩称,“苏禄乃是我国藩属,如今其国内局势不稳,影响南海往来船只贸易,水师驻跸福州,只是为了防范未然,且震慑海盗而已,并无和贵国交战之意,且理藩院已经行文给苏禄国王,****仁德为先,自然不会擅动刀兵,请贵国放心。”公使又问北洋水师具体行止,庆海又称,“此乃兵部之事,并非理藩院职责,贵使可问总理衙门。”
六月初十,北洋水师由水师提督彭玉麟率领舰队大小船只三十余艘,从威海卫出发,停驻上海休整一日,次日到达福州,左宗棠已经在福州等候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