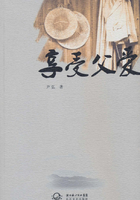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老娘,我记得我小时候挨过您很多打,您总是拿着棍子追得我满街跑,后来我长大了,要跟您反抗,您就改变了策略,整天板着脸对我唠叨。现在我终于明白,您那是恨铁不成钢。而我,如今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未能报答您的生养之恩,却又将小野这个负担甩给了您,我很惭愧,我除了跟您说感谢外,还要跟您说,总有一天,我会让您苦尽甘来,过上好日子!”
“二姐,我嫡嫡亲亲的姐!我们两个啊,肯定前辈子就有冤仇,所以这辈子老是冲突,一碰面就红眉毛、绿眼睛的谁也不让谁。你从小就横,样样都要占强,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你想人人都以你为中心,这可能吗?当然,你横也是因为你有能力,你不安于贫穷,要不是你横,这家人也不可能从此有吃有穿有事做,就连我也沾你的光,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你不愿看着我风餐露宿,沿街乞讨,总而言之我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独自照顾父母姐妹,感谢你,不计前嫌给我的宽容,甚至锲而不舍地仍在为我的将来操心,”林山深深给她鞠一躬,“谢谢了,二姐!”
一个个敬完后他踉踉跄跄地走回座位,一脸堆笑地看着杨梅,泼泼洒洒地往杨梅杯中倒酒。
杨梅嗔怒地一把抢了他的酒瓶,说:“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醉了。”
“哈,你还关心我。”
“我当然关心你。”
林山冷笑:“哼,关心我,老子去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从酒米缸里泡过来的,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天天烂醉如泥,那个时候你在哪里?老子守着你那句‘等我安顿好会回来接你们’的屁话,天天等啊盼啊,你在哪里?我跟儿子两个钱绝粮尽,无米下锅,儿子向你妈讨饭吃,你老子都不肯,还撵他下楼,追到我店里来一次次羞辱我,把所有债主都支到我那儿,你又在哪里?儿子一病不起,好几天无钱看病,我求助无门,四面楚歌,只有无可奈何地掉泪,守在他身边等奇迹出现,你又在哪里?你老子变本加厉地每天无事生非,对我跟小野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最终把我店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逼我们离开,我真想跟儿子就此一了百了,你又在哪里?哼!你在寻欢作乐!你在落井下石!你在大鱼大肉!你在放荡高兴!”
一家人被林山对杨梅又吼又叫、唾沫四溅数罪的材料惊得目瞪口呆。杨梅一直认罪地埋着头,她胆怯而怀有悔意地看着林山说:“我知道你很恨我,当初我不辞而别,以至于逼你离婚,确实没给你留一点儿余地,但,我是有苦衷的,我……”
“苦衷?哈,我明白,因为我没办法使你穿金戴银,百事无忧,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也要感谢你,嘻……感谢你使我山穷水尽、负债累累,呕啊——”顿时,林山喷了杨梅一身。
杨梅扶着酒醉的林山从出租车上下来,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屋,林山整个人软靠在沙发上,放眼四望这面积不宽的两室一厅,巡看件件陈旧的家具,不禁冷笑,他万万想不到杨梅带他回的这个地方竟是权裔少年时的家。
杨梅笑容可掬地一手端杯,一手捏着热毛巾走来,将杯子放在茶几上,说:“喝点浓茶吧。”不由分说,拿张毛巾体贴地给林山擦脸。林山顺从地由她摆布,奇异的目光一直盯着她。
杨梅看他一眼,说:“很奇怪,我学乖了是不是?”
林山感触地说:“的确,这些事以前都是我的专利,我们结婚七年了,你从未给我倒过一杯水,没递过一回毛巾,你甚至从未像今天这样心平气和听任我的吼叫而不出声。我每次喝醉酒你都骂我,把我推下床,让我在地上自己醒酒,还有很多次,你关我在外面,我就坐在门口,听夜深人静时四伏的虫鸣,望着漆黑的夜空模模糊糊入睡。一直以来我就像个任劳任怨的奴隶侍候你和你的家人,我想办法找路子挣钱,我是拼了命地想满足你的虚荣心,想努力置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可是你非但没有一丝感动,还釜底抽薪逼我上绝路!”
杨梅内疚地握着他的手,满心忏悔地望着他,说:“对不起老公,以前都怪我太任性了,拥有你这么好的人不知道珍惜,还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两年我独自在外面闯也经历了不少事,看了许多人情冷暖,我终于明白,这世界上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好!”
“可惜,这句话你说晚了。”
“我知道,但我想求你给我一次恕罪的机会,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可以把店扩大,自己管理,请人经营!以后我们还可以看情况多搞几家连锁店,甚至注册公司!”
“哼!”林山觉得好笑,说,“好大的口气,注册公司,乡下还有一屁股的烂账未还。”
“嗨。”杨梅不屑地说,“那点小钱,不值得担心,改天我就回去还了,你朋友信用社那些贷款,等下年到期我也还给他。”
林山理直气壮地看着她,说:“你该还。”
林山强调说:“你也没说过你要还。”
杨梅一脸天真地说:“我现在就说了,怎么样?”她抬腿骑坐在林山身上,一手拉一只他的耳朵,逗他道,“你敢把我怎么样。”
“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林山不温不火地伸手撇推开她的手,说:“不过,我们得把话挑明了说,账,还不还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之间没有额外的交易!”
“是,老公,谁叫我自己生在福中不知福,我接受你的考验,”杨梅伸手就朝林山两肋挠他的痒。林山大笑不止,在杨梅肆无忌惮的挑逗下林山忘了所有的怨恨,此时只有男人对女人的贪欲。
Chapter4
漫天烟花燃放,处处炫目璀璨。权裔站在自家楼前拐角处,望着毗邻冲天喷发的烟火,移目望着自家楼顶的寂静。想着去年和砚彧一起放爆竹的快乐。她好想儿子,望着自家漆黑的窗户,冷清而落寞,她感伤地返身而去。灯火璀璨,万物喜庆,权裔独揣心事,漫步在人来人往的欢声笑语中。看来这个家已经不欢迎她了,不知她的砚彧去了哪里过年,或许在医院陪他的爸爸。
权裔来到医院,走到病房门口她有些担忧婆婆会轰她走,便谨慎地藏在门边悄悄往里瞧。四张病床,只剩刘新廷一人。邹远惠正用心地往刘新廷口中送饭菜,并体贴的用纸巾擦擦他的嘴。刘新廷很难为情地抽出那只挂液体的手,说:“我自己来吧。”
“呃,别动,”邹远惠忙轻轻地将他的手送回被子中盖好,说,“小心弄到伤口。”
刘新廷感激地说:“谢谢你邹姐,你每天每顿都给我做好饭好菜,送来喂我,帮我照顾砚彧和母亲,还给我倒屎倒尿,我心里真是很过意不去。”
远惠含嗔带笑道:“过意不去就乖乖地养好伤,等你病好了,我也要你照顾照顾我,你会吗?”
“会,我洗衣做饭,端茶送水都没问题,你放心,只要以后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叫我,我决不推辞。”
远惠冲他笑笑,含羞看他一眼,夹个鱼丸送进他嘴中。看他吃得津津有味,心里很是满足地说:“这鱼丸好吃吗?”
“好吃,你做的什么菜都好吃,想不到你还做得一手好菜。”
“我才没那么能干呢,以前也是吃现成惯了,这回是为你逼上梁山,买了一本菜谱。”
新廷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顿了顿,扯开了话题说:“呃,砚彧今天晚上怎么没跟着你来?”
“还说呢,他就是在家里跟他奶奶闹,说要来医院,不去他姑妈家过年,要不是他哥哄他说,吃了饭带他上街去买烟花,可能八头牛都拉他不去。”
新廷霍然明白似的,说:“哦,怪不得几个病人都回家去了。”说着很是歉疚地看着远惠,“真对不起,我害你年都过不好,”一边忙又伸出手,说:“来,把碗给我,快回去吧,你叫陪伴进来就行了。”
远惠嗔怪地说:“上哪儿去叫,昨天他就跟我说了今天不来。”
“那你快喂我吃吧。”
“忙什么,”远惠惬意地看他一眼,又舀个鱼丸给他,温柔地望着他,说,“我今晚不走。”新廷惊异地看她一眼,忙躲开她的视线。
权裔怅然失落地离开,新廷也不需要她了,她的脸上有一丝酸涩的笑意。权裔一脸伤感地望着满天抖落的烟火,本应是家人热闹团聚的夜晚她却感到格外的阴冷凄凉,她的家在哪儿呢?此刻,她最想的人是她的砚彧,她最最可爱的儿子,在这样的夜晚,远惠独自一人陪伴新廷,那么尽心细致地照顾他,这意味着什么呢?权裔想自己是真的回不去了。望着漫天飞舞的烟花,她的心中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情绪,那是孤独而至的一种悲伤与苍凉,她开始怀疑这段感情是否得不偿失,是否如那天空正盛放的烟花,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转瞬即逝,只留下呛人的浓烟,让人患得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