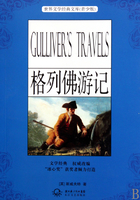他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过仍然微笑着。
“噢!”他说,“我在荒原上玩耍了一整天后回到家时,经常这样亲我妈妈。她站在门外的夕阳下,显得高兴又舒心。”
他们从花园这边跑到那边,发现了太多的奇迹,他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必须小声说话,不能大声喧闹。他指给她看在原本以为已经死掉的玫瑰枝上鼓出来的叶蕾,他指给她看从松软泥土里钻出来的千万点新鲜绿芽。他们热切地把小鼻子凑近地面,嗅着它温暖的春天的气息。他们挖土、拔草,满心欢喜地低声笑,直到玛丽小姐的头发跟迪肯的一样乱,脸颊跟他的一样红。
那天早晨,世上所有的快乐都出现在秘密花园里。在这些快乐中,有一种比其他的更快乐,因为它更神奇。只见一个东西轻盈地飞过墙、穿过树林、飞向一个角落。那是一只红胸脯的小鸟,嘴里挂着什么。迪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把手放在玛丽身上,就像突然发现自己在教堂里放声大笑一样。
“咱们甭动。”他用浓浓的约克郡口音悄悄地说,“咱们甭大声出气。我上次见到它时就知道它在求婚。这是本·威斯特夫的知更鸟,它正在搭窝。如果咱们不赶它,它会留下来的。”
他们轻轻地坐在草地上,纹丝不动。
“咱们绝对不能显得是在密切观察它。”迪肯说,“它要是发现咱们在干涉它,就会跟咱们永远翻脸。这段时间内它会很反常。它正在建立家庭。它比平时更害羞,更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它没时间到处串门、说闲话。咱们必须安静地坐着,努力地装成草或者树。等它习惯看见咱们时,我再对它叫一声,它就知道咱们不会妨碍它了。”
玛丽小姐一点儿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像迪肯那么明白,怎么才能努力地装成草或者树。他说到这么古怪的事情,就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似的,她感觉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她仔细地观察他几分钟,想看看他会不会静静地变绿、长出枝叶。可他只是站着,站得出奇地稳。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细小,能让她听得见真是很奇怪,可她确实听见了。
“这是春天的一部分,我是说筑巢。”他说,“我保证自打这世界一开始,每年都这样。它们有自己的思考和做事方式,人们最好不要干涉。你要是太好奇的话,在春天比其他任何季节都容易失去朋友。”
“要是咱们一直说它,我就忍不住看它,”玛丽尽量轻声地说,“咱们得说点儿别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要是咱们说些别的,它更高兴。”迪肯说,“你想告诉我什么?”
“呃——你知道柯林吗?”她悄悄地说。
他扭头去看她。
“关于他,你都知道些什么?”他问。
“我见过他。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跟他聊天。他想要我去。他说我让他忘掉了生病和死亡的事。”玛丽说。
迪肯圆脸上的惊奇消失了,他看起来是真的如释重负。
“我太高兴了。”他叫道,“我真的很高兴。这样我就舒服多了。我原来一点儿也不能提起他,可我又不喜欢藏着什么不说。”
“你也不喜欢藏着花园不说吗?”玛丽问。
“我永远也不会说出花园的事。”他回答道,“但我跟妈妈说:‘妈妈,我有一个秘密。它不是坏事,你知道的。不比藏着一个鸟窝更严重。你不介意吧,对吧?’”
玛丽总是愿意听到他妈妈的事。
“她说什么?”她问,一点儿也不担心。
迪肯憨憨地笑了。
“她的回答就跟平常一样,”他说,“她轻轻地揉揉我的头,笑着说:‘啊,孩子,你想保守多少秘密都可以。我已经认识你十二年了。’”
“你怎么知道柯林呢?”玛丽问。
“人人都知道克瑞文先生,也知道他有一个孩子像他一样,会变成驼背,人人都知道克瑞文先生不喜欢别人谈论这个孩子。人们都很同情克瑞文先生,因为克瑞文太太年轻又漂亮,他们彼此非常相爱。克瑞文太太每次去怀特镇的时候,都在我家歇歇脚。她不介意在我们小孩子面前跟妈妈聊天,因为她知道我们都值得信任。你是怎么发现他的?玛莎上次回家的时候可发愁了。她说你听见他发脾气就乱提问题,让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玛丽告诉他,那个夜晚,呜咽的狂风吵醒了她,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哭声给她引路,她举着蜡烛在黑黢黢的走廊里前进,最后她打开了那扇透出淡淡灯光的门,看见房间角落里的那张有四根支柱的雕花大床。当她描述那张象牙白色的小脸和那双长着浓密黑睫毛的奇怪大眼睛时,迪肯摇了摇头。
“跟他妈妈的眼睛一样,只是她的眼睛一直在笑着。他们说的。”他说,“他们说克瑞文先生没法在他醒着的时候看见他,因为他的眼睛跟他妈妈的太像了,可长在那张愁苦的小脸上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你认为他希望他死掉吗?”玛丽悄悄地问。
“不。不过他希望他从没出生过。我妈妈说,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最惨的事。没人想要的孩子很难成活。克瑞文先生,他可以给那个可怜的孩子花钱买任何东西,可他又宁愿彻底忘记他。因为他害怕有一天突然发现这孩子长成了驼背。”
“柯林自己也怕得要命,他都不愿意坐起来。”玛丽说,“他说他老是在想,要是感觉到自己背上有一个包鼓起来,他就会疯掉,他会尖叫着死掉。”
“噢!他不应该总是躺在那儿想这些事情。”迪肯说,“总是想这些事,哪个孩子也好不起来。”
狐狸躺在他身边的草地上,时不时地抬头让他拍拍自己。迪肯弯下腰,轻轻地抚摩它的脖子,沉思了几分钟。然后,他抬起头,环视花园。
“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说,“一切看上去都是灰色的。现在你往四处看看,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来。”
玛丽看了看,呼吸有点急促起来。
“天啊!”她叫道,“灰墙正在变呢。现在好像有一层绿雾盖住它了。简直像是一层绿色的面纱。”
“是的。”迪肯说,“它会越来越绿,直到灰色完全消失。你猜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肯定在想一件好事。”玛丽热切地说,“我相信是关于柯林的。”
“我在想,如果他能来这儿,就不会一直等着背上长包。他会一直等着玫瑰丛里的花苞冒出来,他还可能会健壮一些。”迪肯解释说,“我想,咱们能不能让他有心情到这儿来,坐着轮椅躺在树底下。”
“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都在想。”玛丽说,“我想他能不能保密,还想咱们能不能把他带到这儿来,不被人发现。我认为你也许可以帮他推轮椅。医生说他必须呼吸新鲜空气。如果他想让咱们带他出来,那就没人敢反对。他不愿意跟别人出去,也许他们会乐意他跟咱们出来。他可以命令仆人们离他远远的,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
迪肯一边挠船长的背,一边使劲思考着。
“我敢保证,这对他肯定有好处。”他说,“咱们没有觉得他不出生更好。咱们就是两个小孩,看着花园慢慢生长,他是另一个小孩,我们就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看春天。我敢保证这比医生的那些药方更强。”
“他在房间里躺的时间太长,他总是担心自己的背,把自己弄得怪怪的。”玛丽说,“他知道很多书上的东西,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老病着,根本没精力注意周围的东西,他讨厌出门、讨厌花园和园丁。不过他喜欢听关于这个花园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秘密。我没敢跟他说太多,不过他说他想看看它。”
“咱们总有一天会带他来这儿。”迪肯说,“我能帮他推轮椅。你注意没有,咱们坐在这儿的时候,知更鸟和它媳妇一直忙活着?看它,正站在那根树枝上,琢磨着把它嘴里叼着的细枝放哪儿合适。”
他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知更鸟扭头探询地看着他,口里还衔着它的细枝。迪肯像本?威斯特夫一样对它说话,不过迪肯的口气是一种善意的建议。
“你不管放到哪里都没问题,”他说,“你在钻出蛋壳前就知道怎么搭窝了。接着干吧,伙计。你没时间可浪费。”
“噢,我喜欢听你跟它说话!”玛丽说着,快乐地笑着,它、嘲笑它。它跳来跳去,好像每句话都听得懂。我知道它喜欢这样。本·威斯特夫说它特别自负,宁愿被人扔石头,也不愿别人忽视它。”
迪肯也笑了,接着说话。
“你知道我们不会打扰你。”他对知更鸟说,“我们自己跟野生动物差不多,我们也在搭窝。祝你好运。请别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知更鸟没有回答,因为它的嘴巴被占着。不过玛丽知道,当它带着细枝飞向自己的角落时,露珠一样明亮的眼睛黑黝黝的,意思是说它不会把他们的秘密告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