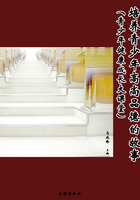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哎呀!”玛莎不安地说,“你以后不要去走廊里瞎逛、去偷听了。克瑞文先生一定会很生气,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没有偷听。”玛丽说,“我只是在等你——就听见了。听见三次呢。”
“我的天!是迈德洛克太太在摇铃。”玛莎说着,跑出了房间。
“这简直是人们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玛丽有些昏昏欲睡。她的头垂到旁边椅子的靠枕上。新鲜空气、挖土还有跳绳让她感觉很累,也很舒服。她睡着了。 士,对她撒谎,说你自己是密塞荒原上最漂亮的雄性知更鸟,随时准备打败其他的男士们。”
“噢!看它!”玛丽惊叫起来。
知更鸟显然心情不错,想要大胆地施展魅力。它跳得越来越近,越来越专注地看着本?威斯特夫。它飞到最近的红醋栗树上,歪着脑袋对他唱歌。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到我。”本说,他努力地皱着脸,玛丽可以肯定他正在尽量不露出高兴的样子,“你以为没人能超越你——你就是这么想的。”
知更鸟展开翅膀——玛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飞到本?威斯特夫的铁锹把上,站在铁锹把的顶端。老人的脸慢慢地变成另外一种表情。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都不敢呼吸——仿佛给他整个世界他也不会动一动,以免他的知更鸟突然飞走。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像耳语一样。
“好吧,我该死。”他说得那么轻柔,好像说的不是这句话,“你确实知道怎么收买人——你真的知道!你简直不像是人世间的鸟,你太聪明了。”
他纹丝不动地站着——几乎没有呼吸——直到知更鸟晃动一下翅膀,飞走了。他站在那儿,看着铁锹柄,好像被施了魔法。然后他又开始挖地,几分钟都没说话。
不过他时不时地咧嘴笑笑,所以玛丽不害怕跟他说话。
“你有自己的园子吗?”她问。
“没有。我是个单身汉,和马丁一起住在大门口。”
“如果你有个园子的话,”玛丽说,“你想种什么?”
“卷心菜、洋芋和洋葱。”
“可是,如果你想要的是花园呢,”玛丽坚持问,“你会种什么?”
“球根类的花,还有闻起来香甜的花——不过主要种玫瑰。”
玛丽的小脸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
“你喜欢玫瑰吗?”她问。
本?威斯特夫连根拔出一棵杂草,把它扔到一边,然后才回答她。
“嗯,是的,我喜欢。是一位年轻女士教我喜欢的。我是她的园丁。她在一个地方种有很多玫瑰,她非常爱它们,就像它们是孩子一样——或者说像知更鸟一样。我见过她弯下腰去亲它们。”他又拔出一棵杂草,对着它皱着眉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她现在在哪儿呢?”玛丽感兴趣地问。
“在天堂。”他回答说,又把铁锹深深地插进土里,“牧师是这样说的。”
“那些玫瑰呢?”玛丽又问,她更加感兴趣。
“它们自己待着。”
玛丽变得非常激动。
“它们死了吗?如果没人照看,玫瑰会死吗?”她冒险问道。
“嗯,我喜欢它们——我喜欢她——她喜欢它们。”本·威斯特夫不太情愿地承认,“每年我都去一两次,修剪一下,给它们松松土。它们到处乱长。不过它们都种在肥土里,所以有些活下来了。”
“当它们没有叶子、看起来又灰又黄又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们是死是活呢?”玛丽问。
“等到春天——等到太阳照着它们,雨水又淋着它们,然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看——怎么看?”玛丽喊了出来,忘记自己要谨慎。
“沿着枝条看,如果你看见这儿或那儿鼓起一个个褐色的小包,等春雨下过之后你瞧瞧会发生什么。”他突然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她急切的脸,“你为什么突然对玫瑰这么感兴趣呢?”他问。
玛丽小姐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她简直不敢回答。
“我——我想玩——我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园。”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什么事情可做。我什么也没有——也没人和我玩。”
“嗯,”本·威斯特夫盯着她,慢慢地说,“这是真的。你什么都没有。”
他说话的语调很奇怪,让玛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为自己感到难过。她以前从没为自己难过过,她只是觉得累、老想发脾气,因为她是那么讨厌周围的人和事。可现在世界好像正在改变,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如果没人发现秘密花园的事,她一定会永远快乐下去。
她又跟他一起待了十几分钟,大胆地提了许多问题。他倒是全都怪怪地嘟囔着回答了。他看起来没有真的生气,也没有拿起铁锹走开。她正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了些关于玫瑰的事,这让她想起他说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些玫瑰。
“你现在还去看那些玫瑰吗?”她问。
“今年还没去呢。风湿让我的关节僵硬得不行。”
他正嘟嘟囔囔地说着,突然地对玛丽发起火来。她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你听着!”他大声地说,“别问这么多。你是我碰到的问题最多的娃娃。走开,自己玩去。今天我不想再说话了。”
他的语气非常严厉,玛丽知道再待下去也没用。她慢慢地沿着小路跳着跳绳,琢磨他是怎么回事。她对自己说,很奇怪,这又是一个她喜欢的人,虽然他爱发脾气。她喜欢老本·威斯特夫。是的,她确实喜欢他。她总是想办法让他跟自己说话。而且她开始相信,他知道世界上所有关于花草的事情。
秘密花园外面,有一条月桂树篱笆围着的小路。小路的尽头是一道小门,小门通往院子里的一片树林。她想她可以沿着这条小路跳到树林里去,看看那儿有没有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她一路上跳得很开心,来到门前时她推开门走了进去,因为她听见一声低低的、特别的哨声,她想看看这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她停下来一看,简直无法呼吸。一个男孩背靠着树坐在树下,正在吹一支粗糙的木笛。他大概有十二岁,模样很好笑。他看上去很干净,鼻子翘翘的,脸蛋红得像罂粟花,玛丽小姐从没见过哪个男孩子的脸上长着这么圆、这么蓝的眼睛。在他靠着的那棵树上,有一只棕色的松鼠挂在树干上,看着他;附近灌木丛背后,有一只公野鸡正优雅地伸着脖子探头观看;离他很近的地方,有两只兔子直直地坐着,吸着小鼻子——它们好像都被他吸引过来,听他的笛子发出奇怪的低声呼唤。
他看见玛丽的时候,伸出手,用几乎跟他的笛声一样低的声音对她说话。
“你别动。”他说,“会吓着它们的。”
玛丽一动不动。他停止吹笛,从地上站起身。他的动作慢极了,看起来就像根本没动一样。可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这时,松鼠跳回它的树枝,野鸡缩回它的脑袋,兔子四肢着地,跳走了,不过它们好像都没受到惊吓。
“我是迪肯。”那个男孩说,“我知道你是玛丽小姐。”
这时玛丽才意识到,她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迪肯。还有谁能吸引兔子和野鸡呢,就像印度当地人吸引蛇一样?他的嘴巴宽宽的、红红的、弯弯的,他的微笑铺了满脸。
“我慢慢地站起来,”他解释说,“因为如果你动作很快的话,就会吓着它们。有野生动物在旁边的时候,动作要慢,说话声音要低。”
他跟她说话的方式不像是从没见过面的,而像是跟她很熟一样。玛丽不大了解男孩子,她跟他说话的时候有点僵硬,因为她觉得有点害羞。
“你收到玛莎的信了吗?”她问。
他点了点头。他长着红褐色鬈曲的头发。
“所以我就来了。”
他弯下腰捡起什么东西,那是他吹笛时放在身旁的。
“我带来了园艺工具。这儿有一把小铲子、一个小耙子、一支小叉子还有一个小锄头。嗬,这些都很好用。还有一把泥刀。我买下其他花籽的时候,店里的女人还送了一包白罂粟籽和一包蓝色飞燕草籽。
“你能给我看看那些花籽吗?”玛丽说。
她真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说话。他说话又快又顺畅,听起来好像他喜欢她,而且一点儿也不担心她不喜欢自己,尽管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荒原上的男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长着一张可笑的脸,还有一个乱蓬蓬的红褐色脑袋。当她离他更近一点儿的时候,她发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混合着欧石楠花、青草和树叶的清新气息,仿佛他就是这些植物做成的。她非常喜欢这种气味。当她看着他那张长着红色两颊和蓝色圆眼睛的滑稽面孔的时候,她忘记了害羞。
“咱们坐在这根木头上看吧。”她说。
他们坐下来。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包得很粗糙的小牛皮纸袋。她解开绳子,发现里面有很多包得更整齐的小袋子,每个小袋子上都有一个花的图案。
“有很多木犀花和罂粟花。”他说,“木犀花最香,随便你撒到哪儿它都能长。罂粟也是这样,你只要对它们吹声口哨,它们就能开花。它们是最好的花。”
他停下来,飞快地扭过头去,他深红的脸庞高兴得直发光。
“那个正在叫咱们的知更鸟在哪儿?”她问。
鸟鸣声来自密密的冬青树丛,冬青树上猩红的浆果鲜亮。玛丽知道那是谁。
“它真的在叫咱们吗?”她问。
“是啊,”迪肯说,好像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它在叫它的一个朋友。像是在说,‘我在这儿呢,看我呀。我想跟你说说话。’它就在灌木丛里。它是谁?”
“它是本·威斯特夫的,不过我想它也认识我。”玛丽回答说。
“是的,它认识你。”迪肯的声音又低沉下去,“而且它喜欢你,把你当自己人。它一会儿就会告诉我关于你的所有事情。”
他用玛丽刚见过的那种动作慢慢地移到离灌木丛很近的地方,发出一种类似知更鸟鸣叫的声音。知更鸟认真地听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像回答问题一样开口回应。
“哈,它是你的朋友。”迪肯咯咯笑了。
“你觉得它是吗?”玛丽心情急迫,大声叫道。她太想知道答案了,“你觉得它真的喜欢我吗?”
“如果它不喜欢你的话,就不会离你这么近。”迪肯回答,“鸟儿很挑人。知更鸟鄙视别人的时候比人类还厉害。你看,它在讨好你。它在说:‘你没看见有一个家伙吗?’”
看起来这一定是真的。它正在灌木丛中跳着,侧着身子移动,歪着脑袋歌唱。
“你能听懂每一只鸟说的话吗?”玛丽说。
迪肯笑开了,似乎满脸只剩下宽宽的、红红的、弯弯的嘴巴。他挠挠乱蓬蓬的头发。
“我想我能听懂,它们也觉得我能听懂。”他说,“我在荒原上跟它们一起待了很长时间。我看着它们破壳孵出来、羽毛慢慢丰满、学会飞、开始唱歌,我觉得自己成了它们中的一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只鸟,或是狐狸,或是兔子,要不就是松鼠,也有可能是一只甲壳虫,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他笑了,回到木头上坐下,又开始说花籽的事。他告诉她它们开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告诉她怎么种、怎么照顾、怎么浇水施肥。
“你瞧,”他突然转身看着她说,“我可以亲自帮你种。花园在哪儿呢?”
玛丽瘦小的手放在大腿上,紧紧地握在一起。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整整一分钟她什么都没说。她从没想到这一点。她觉得很痛苦,感觉自己的脸红一阵又白一阵。
“你有一小片花园,是不?”迪肯说。
她的脸真的是红一阵又白一阵,迪肯看见了。她还是一言不发,这让迪肯开始有点弄不明白了。
“他们不给你一点儿吗?”他问,“你还没有花园吗?”
她的手攥得更紧了。她把眼睛转向他。
“我对男孩子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慢慢地说,“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替我保密呢?这是一个大秘密。如果被人发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我会死掉的!”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情绪很激动。
迪肯更疑惑了,又用手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不过他友善地回答她。
“我一向都能保守秘密。”他说,“要是我不对其他孩子保密,保守小狐狸、鸟窝、小动物的洞的秘密,那荒原上就一点儿都不安全。相信我,我能保守秘密。”
玛丽小姐没打算伸手抓住他的衣袖,可她确实这么做了。
“我偷了一个花园,”她说得很快,“它本来不是我的。它是别人的。谁也不要它,谁也不管它,甚至没人进去过。很可能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死掉了。我也不知道。”
她开始焦躁起来,感觉像以前一样想乱发脾气。
“我不管,我不管!没人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我在乎它,他们不在乎!他们让它死掉,把它锁起来了。”她激动地说完,用手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可怜的小玛丽。
迪肯好奇的蓝眼睛越来越圆。
“啊——呀!”他慢慢地发出感叹,既表示惊讶又表示同情。
“我没事可干,”玛丽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是自己找到它、自己进去的。我其实就像知更鸟一样。他们不会把它从知更鸟手上夺走。”
“它在哪儿?”迪肯压低声音说。
玛丽小姐立刻从木头上跳起来。她知道自己叛逆、固执的脾气又爆发了。她才不管呢。她傲慢专横,摆出一副在印度时的派头,又愤怒又悲伤。
“跟我来,我带你去看。”她说。
她带着他绕过月桂小径,来到两边长着厚厚常春藤的走道。迪肯跟着她,脸上带着奇怪的、几乎是怜悯的表情。他感觉自己正被带着去看陌生鸟儿的鸟巢,必须轻手轻脚。她走到墙边掀开垂着的常春藤时,他吓了一跳。那儿竟然有扇门。玛丽把它慢慢地推开,他们一起走了进去。然后玛丽就站在那儿,挑衅般地挥着手。
“就是这儿。”她说,“这是一个秘密花园。我是这世界上唯一想让它活着的人。”
迪肯环视四周,看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噢!”他几乎耳语般地说,“这是一个奇特的、美妙的地方。简直像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