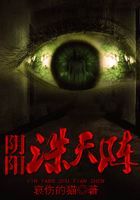看着丫鬟焦急而明亮的眼睛,盗墓的过程在潮生脑子里一桢桢回放。那些细枝末节被串联起来,而最后蓝漓那眼里一闪而过的狠绝令潮生一个惊醒,豁然明了。
潮生没再多说,夺门而出朝着西郊楼景浩的墓飞奔而去。希望,一切还可以来得及。
原来,楼景浩与蓝漓是互相深爱的情侣,却不想家族之间的阻隔,令两人无未来可言。于是,两人策划了这一场假死的私奔计划。绿如意有拘魂之效,只要七日之内魂魄得以归体,死去之人就可复活。于是由楼景浩持着绿如意死去,在由蓝漓盗出绿如意,让楼景浩复活。并且,是借他人之体。这样,便可做到天衣无缝,不会引人怀疑。而蓝漓那一出大闹送葬队伍,恐怕也是为了消除楼蓝两家对二人的怀疑。
他们之间的情事,也只怕两家早有风闻。不得已,才逼迫两人走上绝路。
却不想,在那墓室里竟遇见那样多困难的阻档。最后一个不惜血本的禁咒,更是令蓝漓绝望。她不想,他竟如此不惜代价组织她。曾经的誓言,都成了虚妄。于是,她选择玉石俱焚。
不过,打破蓝漓最后希望的,便是那枚悬挂在机关绳上的扣子。那是她赠与他的定情信物,他贴身藏着。若离他身之日,便是两人恩断情绝之时。
当潮生赶到主室时,看到蓝漓扑在楼景浩的尸身上。一只手已被歌破,血缓缓地滴落在绿如意上。绿如意散发的幽幽绿光,渐渐盛浓。而蓝漓呢喃着:“景浩,既然如此,那我们便永远地待在这绿如意里,不得超生。无论如何,我都不要与你分离。”
潮生赶紧上前取开绿如意,并强制地将蓝漓拉起。蓝漓挣扎着,嘶吼着。潮生一个耳光扇过去,令她暂时安静下来。潮生轻轻执起她的手,为她包扎,并柔声道:“这,并不是真相。”
蓝漓恍然地看着眼前表情忽然柔软如水的男子,“而且,你也应该知道的。”一句话,隐忍已久的眼泪睁睁流了下来。最后,低声压抑的哭声成为放肆的大哭。那些积蓄在心里的苦痛,被全数引燃。
“其实,一开始是是提出让自己死去,楼景浩却不肯,执意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假死’之人。而之后,墓室里那些机关全然不是你们当初设计的模样,那时你就已生疑。而当遇见最后那个血童葬时,你已完全肯定了楼景浩根本没有复活同你私奔的打算。于是,你以为他背叛了你。”潮生说到这里,顿了顿,而蓝漓眼里的痛苦越发深浓,“但你终不甘心,调查后却发现原来楼景浩早已被下诅咒,即便复活过来,也是活不长久的。”
话至此,已让蓝漓接近崩溃:“是我害了他呀。我不想,我并不想的。”
“不,即便他未被诅咒,亦是活不过来的。”
“什么?”这一句话,宛若响雷,惊破清空。蓝漓看着潮生忽然悲戚的神光,疑问脱口而出。
“其实,你早已知道,你并非白慕云亲生。你是……”潮生的话,勾起了蓝漓遥远的回忆。离世的母亲。冷漠的父亲。同族人的排斥与嘲笑。手足厌恶的眼神以及自己虚弱模糊的存在感。那样尴尬的境地,才使得她如此孤注一掷地想抓住这份感情,即便毁天灭地。
蓝家乃女权家族,每代当家皆是女性,且是一脉相承,旁系根本无染指的机会。而北方术法世家白则是入赘蓝家,同蓝家族长诞下下一代女族长。这个传统,已世袭几百年。而蓝漓的母亲则是上一代的继承人蓝嫣,父亲则是白慕云。而蓝嫣却在诞下蓝漓后就离奇离世。
“而要释放被拘禁在绿如意里的生魂,只有纯粹是蓝白两家的血才可做到。而你,是不可能的。所以,楼景浩才如此坚持要他‘假死’,才如此处心积虑设下那些机关来阻挠你。他只是想,你好好活下去。那血童并未出手伤害,便是最好证据啊。你怎么会不懂?”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他是知道,你有着倔强极端的个性吧。而且,他或许是真的想,给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梦。”
这一层深埋的真相,让蓝漓惊痛得无法言语。楼景浩的爱如此厚重难抵,她又怎么不明白。她知道,他如此为她着想。她只是恨,她无法如此交付于他。她恨的不是他,她悔的不是他。她责怪的,终究是这样一个无能的自己。
沉默片刻后,蓝漓整理狼狈不堪的泪痕,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光彩:“先生,你是否,可以最后帮我一把。帮我和景浩,完成一次冥婚。”
“你,决定了?”
“恩。这尴尬的位置继续下去亦是痛苦。那个家,从来不曾有我的所在。倒不如,就这样随他去。这次,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先生,是否就成全我这一次。”蓝漓露出虚弱的笑。眼神里的几乎奢望的乞求,令潮生的心疼痛难抑。最后,他还是艰难地颔首应允下来。
那绿如意,在昏暗里漫溢出幽幽荧光。
晨光熹微。当第一屡光染白天边阴翳的云层时,冥婚也终于完成。
当飘浮于绿如意上两个执手的魂灵最终在荧光里散去时,一张白色丝绢也飘落在地。潮生缓步过去,拾了起来。当上面娟秀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时,潮生浑身一震,那隐忍多年的清泪也终于潸然而下。
面对着渐渐散去的黑暗,潮生呢喃着:“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的结局呢?但至少,比我好吧。”
没有回答。似乎只有轻风里徐语低吟,吹去唇边的苦笑。
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第一次邂逅小孩,结果事后她告诉我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是他学长,他却爱叫我大叔,这让我很郁闷。但每次她叫得字正腔圆,我就忍俊不禁,于是由着她叫得开心。
那时放学已经很久了,学校里的人基本上已经走得清光。因为是值日,所以我耽搁了很久才提着书包懒散悠闲地从学校里踱步出来。经过学校第三个转角处的小巷时,一阵争执的声音让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本来也无事可急,索性看看热闹。但我忽然听到有个倔强纤细的女声叫出了我的名字。小巷幽暗,我看不清人的面目,只知道有几个男的把一个女的团团围住。这样的戏码倒是常见,只是那女的为何要无缘提起我的名字。
“你们这群混蛋知不知道苏离惜是我哥哥。”这句话明显收到了预期的震慑效果,周围的几个人都愣了一下。但他们的智商似乎也不愚,“你说是就是呀?又没证据。”明显底气不足的话语连尾音都变成涟漪状。
“证据这不是来了么?”一行人见是我,拔腿就跑。我是怪物么?怎么见我就跑?我又开始无聊得郁闷起来。苏离惜明明是一个很文雅具有底蕴的名字,偏偏落在了我这样一个暴戾臭屁的流氓身上。每次我打架,妈妈先就是如是感叹一番,接着直接挥我一拳,“臭小子,你给我繁华似锦地去死吧!”有这样以暴制暴的母亲,我想不以拳头出名都难。
那群人落慌而逃,狭仄的空间里就只剩我和小孩大眼瞪小眼。小孩眉目生得清秀,身材娇小,着装也粉红配着湛蓝。如果不说话,倒也是可爱的。偏偏一双眼倔强到底,直直地望着我愣是半天不说话。加之刚才的行为,这样的女孩子还是少惹为妙。于是我撇撇嘴,准备转身离开。
“喂。那位大叔。你不认识我了呀?”一句话差点把我呛死。大叔?我看上去再怎么蹉跎也不至于轮上当她大叔吧。我转过头再次奇怪地把她盯住。这模样,似乎是有点熟悉,但我确实想不起来。
我这人在记忆方面很是迟钝,经常对不感兴趣或不喜欢的人或东西都记不住。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依旧不能记得我老师和我同学的脸和名字。每次别人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总是一脸茫然地问,你是谁呀?而且对于那些经常来找我复仇的人我也不知道究竟他们是为了什么,只知道早解决早完事。所以对于第二次见面的她能有熟悉的印象已实属不易了。
小孩见我丝毫没有记起的反应,脸微微一红,转身就走了。这表情倒是满可爱的,我喜欢。
“喂,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好歹也让我认识下你呀!”小孩根本不理我,很快身影就溶进了苍茫暮色中。既然不知道名字,于是我决定叫她小孩儿。谁让他叫我大叔呢?
现在我才发现记住人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我就这样记住了笑孩那张倔强清秀的脸。第一次,我觉得这个学校也不是那么陌生。
有了记忆之后,剩下的就是加强记忆。我现在就经常有意无意地出现小孩的实现范围内。如果人太多或者隔得远我也会拼命地挤过去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她错身而过。在此期间,我观察到了她很多。早晨大概会在起点半左右到达学校。教室在三楼左侧第二个拐角处。喜欢独自一个人。爱吃冰淇淋爱喝鲜橙多。总是在那个叫什么郭品超还有杀生丸(为此我还专门到网上去折腾了半天)的海报面前驻足很久。爱穿粉色蓝底的上衣和宽松的牛仔裤。面部表情单一,只有在看到清湛蓝天时会微微展颜或看见我时微微蹙眉,其余都是一马平川,而这两个表情再我看来都有趣可爱。在我有意无意地与她碰面多次后,她终于斜着眼问我:“这位大叔,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可不喜欢老男人。”我?对她有意思?我?老男人?这犀利尖锐的小孩,又差点把我给呛死。于是我对着她嬉皮笑脸:“没有,我就是想多看看外星人长什么模样?”说完扬长而去。我可以想象,她肯定在后面气得想跳脚。一想到她生气的样子,我就想笑。这小孩,有意思。我的情绪开始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仿佛是那种缓慢的化学效应,转变得不声不响。
小孩的样子最近越来越频繁地在我脑子里晃悠,而想见到她的冲动也越来越多。最后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想我是喜欢上这个让我深深记住的小孩了。如果让老妈知道,她肯定会语重心长地说:“你啊!别耽误了一个好姑娘。”于是我更加沮丧起来。是不是坏学生都不应该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我第一次,有了对自己的怀疑。
倒是小孩,自从那次跟我说了话之后就变得跟我熟络起来。经常在放课的课间跑来找我陪他去小卖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那天课间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从门外越人而来:“哎。那位大苏大叔,陪我去趟小卖部吧。”我转过头看见小孩站在门外,于是我忽然地就对她笑了,还是笑得特别傻气那种。用小孩的形容就上,我那表情稍不注意就可以用丑字来形容。
我在同学的侧目和窃窃私语中走出了教室。陪小孩去小卖部的路途中,我们接受了不少奇怪目光的洗礼,仿佛我俩走在一起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管他那么多,我高兴就好。我也的确很高兴,和小骇走在一起总觉得有种略微的幸福感。于是我不自觉地就把脸的方向往她那边偏,结果得到她一副“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表情。我立马转过头,寒蝉若噤。想不到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竟被一个丫头盯得大气不敢出。但我一点也不生气。